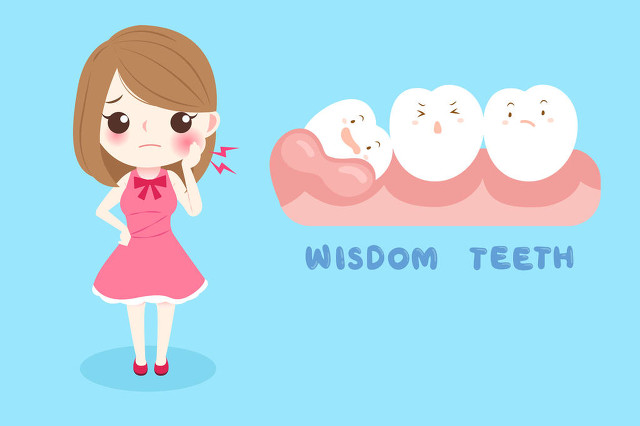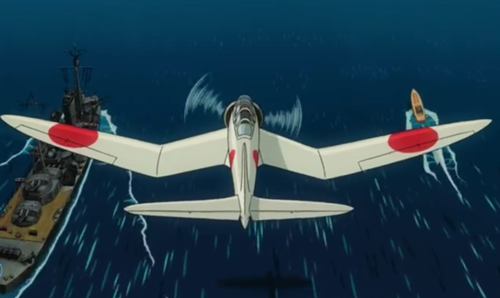關注李小龍的人,一定不會忘記他在電影中飛身爆踢兩塊牌匾的精彩場景。這部電影,叫《精武門》,1972年上映;那兩塊牌匾是“東亞病夫”和“犬與華人不得入”。
電影是一門藝術,任何藝術表達,只有撥動觀眾的心弦,方能激起情感共鳴,從而形成巨浪效應。而最廣泛、最自然、最深沉的情感,莫過於“愛國”。梁啓超曾說:
 李小龍
李小龍“大抵愛國之義,本為人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
是啊,愛國,在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那裡,首先是一種情感,然後才是一種主義。在這片土地上,在這個國度里,出生、成長直至死去,留下了全部記憶,怎會輕易割捨?
即便遭遇不公甚至是迫害,真正愛國的人,可能會選擇暫時逃離,但一定不會選擇叛國。
曾幾何時,陳獨秀寫道:
“八國聯軍打中國時,為什麼不乾脆滅了中國,留下這么個爛攤子,讓人受苦。”
曾幾何時,胡適寫道: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這國如何愛得……你跑罷,莫要同我們一起死!回來!你莫忘記:你老子臨死時,只指望快快亡國。”
但是,他們終究從絕望中走了出來,毅然決然地回國,向黑暗勢力發起挑戰,用看似單薄的力量,打造一片新天空。
至於那些走不出來的,有的自殺以殉志,有的則踏上漢奸的不歸路。一旦邁出滑向深淵的那一步,就會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哪怕,在內心深處,仍是愛國的。
李小龍的電影,總是高揚著“民族精神”的旗幟,通過凌厲霸道的武術,讓國人壓抑許久的屈辱甚至是自卑情緒得到宣洩。
最近成為現象級電影的《戰狼2》,又何嘗不是如此?刷過兩遍之後,給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末尾那句:“那他媽是以前”。
一句話,道盡了百年屈辱;一句話,宣示了民族復興!
以李小龍的武術修為,如果放到今天,很難想像《精武門》會有多少票房。
不過,人們似乎更願意沉浸在澎湃的情緒里,而不太會去思考那兩塊牌匾的真偽。誠然,電影嘛,何必較真?
但是,一切以歷史為主題的藝術表達,都勢必勾起人們對過往的記憶,勢必會重塑人們頭腦中的歷史場景。
然則,這兩塊牌匾,或者說這兩句長期壓在中國人頭上的話語,究竟是怎么來的呢?
 李小龍
李小龍【東亞病夫】
就現有史料而言,最早使用“病人”來描繪中國的,是1876年1月4日發表在《申報》上的一篇文章,文中稱:中國“如土耳其國,早已素稱病人”。那時,距離國門洞開已30餘年,西方對中國的實情早已了如指掌。
真正撕下中國“天朝”面具的,則是清人視為蕞爾小邦的島夷——日本。除李鴻章、袁世凱等人外,天天嚷著要恪守“大本大原”的士大夫們,絕不會料到戰爭的結局竟如此殘酷。
1896年,英國《倫敦學校歲報》對此戰發表評論稱:
“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患其虛實也。”
[註:被西方視為病人的四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波斯、中國、摩洛哥]
顯而易見,無論是“病人”,還是“病夫”,西方藉以指代的是整體意義上的中國,甚至更傾向於清政府,而非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
甲午戰爭尤其是庚子事變之後,“東方病夫”迅速成為流行詞,報紙上的評論可謂俯拾即是。茲略舉幾例。
1901年《國民報》載《東方病人》:“西人謂東方有病人焉,中國是也;西人謂東方有死人焉,中國是也。”
1903年《萬國公報》載《東方病夫之伴侶》:“在遠東之二病夫,曰中國,曰高麗。”
1903年陳天華撰《警世鐘》:“恥呀!恥呀!恥呀!外國人不罵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
1904年孫中山撰《支那問題真解》:“支那久有‘東方病夫’之稱。”
期間,也曾出現“遠東病夫”、“華夏病夫”、“東方病人”之類的概念。至於現在大家所熟悉的“東亞病夫”一詞,則來源於曾樸。
他撰寫小說《孽海花》使用的筆名,正是——“東亞病夫”。
翻閱當時報紙雜誌可知,在“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改革成功之前,“東方病夫”與“東亞病夫”在中國知識界的使用頻率不相上下,甚至前者的見報率更高。
因為,通常意義上的“東方病夫”,同時包含中國與土耳其。未曾想,凱末爾這個牛人,愣是將土耳其頭上的“病夫”帽子給摘掉了。
中國知識界只好有意淡化這一辭彙,更多採用“東亞病夫”來專門描繪中國,以喚醒沉睡的國人。
在傳播過程中,“病夫”的含義也慢慢發生轉變,不再泛指抽象的中國,而是針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乃至身體力量,並成功為尚武精神的復甦提供了重要理論支點。
 如果李小龍重生,再度爆踢“東亞病夫”牌匾,會有多少票房?
如果李小龍重生,再度爆踢“東亞病夫”牌匾,會有多少票房?1903年,梁啓超撰寫《論尚武》一文,大聲疾呼:
“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癱瘓,已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內向而魚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惡根,一雪不武之積恥,20世紀競爭之場,寧復有支那人種立足之地哉?”
註:關於尚武精神的論述,敬請參閱拙文《梁啓超: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
【犬與華人不得入】
1994年,上海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薛理勇發表《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一文,首次對這一木牌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直至今日,學界仍有爭論。
誠然,寫有“犬與華人不得入”的木牌至今未能找到實物,也沒有相關照片,甚至在當時的大型報紙《申報》都無法看到報導。
但是,有一條很關鍵的證據,來自周作人的《公園之感情》:
“上午乘車,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經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游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字,哀我華人與犬為伍,園之四周皆鐵柵,環而窺者甚多,無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與友人同行,又能具體到木牌字數,應能排除故意作偽嫌疑。
除私人日記外,當時租界工部局的檔案也可以互相印證。檔案中明確記載了公園園規,內容如下:
一、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
二、小孩之坐車應在旁邊小路上推行;
三、禁止採花捉鳥巢以及損害花草樹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庸婦等理應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
四、不準入奏樂之處;
五、除西人之庸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
六、小孩無西人同伴則不準入內花園。
據此,我們可以進行合理推測。即使這塊木牌真的沒有掛出來過,國人也會很自然地將公園六條規定簡化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加以傳播。
因為,其他幾條跟自己沒有半毛錢關係,而犬與華人兩條所產生的恥辱感卻撲面而來。這樣的簡化或者符號化,自然不能說它偏離了歷史事實!
《上海租界的黑幕》一書在談到此事時就曾寫道:
“過去有一個時期,公共租界小公園之揭示牌上,標舉規則多餘,其第一條說,‘此園專供外人之用’。另有一條,‘此園不準犬類入內’。簡單說起來,就是華人與犬,不得入內。”
後來,有不少中國人穿上西裝,假扮成日本人入園,而公園方面對此也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取默認政策。1912年,租界董事會會議有一條這樣的記錄:
“在允許穿西裝的華人進入公園問題上,出現了一些爭論,但董事會認為與日人混淆的情況並不多見,因此現行規則應予保留。”
直到1928年,中國人的抗爭終於迎來了勝利,關於“允許華人進入公園和公共場地”的提議終於在納銳人年會中獲得通過。
至此,中國人可以自由出入租界內的任何一所公園。
詩人黃莽曾在《懷念李小龍》中寫到:
梨園子弟詠青春,
跨海猶平拳道真。
一掃病夫龍骨傲,
唱他萬遍警來人。
時光易逝,中國已向世界宣布進入“新時代”,民族復興之夢指日可待。
此時此刻,還有多少人記得李小龍?
李小龍 東亞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