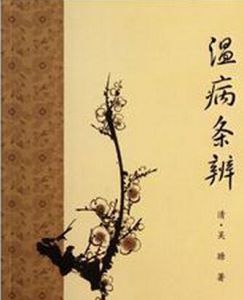原文
 溫病條辨序
溫病條辨序蓋自叔和而下,大約皆以傷寒之法療六氣之疴,御風以締,指鹿為馬,迨試而輒困,亦知其術之疏也。因而沿習故方,略變藥味,沖和、解肌諸湯紛然著錄。至陶氏之書出,遂居然以杜撰之傷寒治天下之六氣,不獨仲景之書所未言者不能發明,並仲景已定之書盡遭竄易。世俗樂其淺近,相與宗之,而生民之禍亟矣。又有吳又可者,著《瘟疫論》,其方本治一時之時疫,而世誤以治常候之溫熱。最後若方中行、喻:嘉言諸子,雖列溫病於傷寒之外,而治法則終未離乎傷寒之中。惟金源劉河間守真氏者,獨知熱病,超出諸家,所著六書,分三焦論治,而不墨守六經,庶幾幽室一燈,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論簡而未暢,其方時亦雜而不精承其後者又不能闡明其意,裨補其疏c而下士聞道若張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於是其學不明,其說不行。而世之俗醫遇溫熱之病,無不首先‘發表,雜以消導,繼則峻投攻下,或妄用溫補,輕者以重,重者以死u倖免則自謂己功,致死則不言己過,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父以授子,師以傳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夜嗥,二千餘年,略同—轍,可勝慨哉!
我朝治洽學明,名賢輩出,鹹知溯原《靈》、《素》,問道長沙。自吳人葉天士氏《溫病論》、《溫病續論》出,然後當名辨物。好學之士鹹知向方,而貪常習故之流猶且各是師說,惡聞至論。其粗工則又略知疏節,未達精旨,施之於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吳子,懷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學不厭,研理務精,抗志以希古人,虛心而師百氏。病斯世之貿貿也,述先賢之格言,攄生平之心得,窮源竟委,作為是書。然猶未敢自信,且懼世之未信之也,藏諸笥者久之。予謂學者之心固無自信時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無應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豈待整冠束髮?況乎心理無異,大道不孤,是書一出,子云其人必當旦暮遇之,且將有闡明其意,裨補其疏,使夭札之民鹹登仁壽者。此天下後世之幸,亦吳子之幸也。若夫<折楊皇苓>,聽然而笑,《陽春白雪》,和僅數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當世,豈不善乎?吳子以為然,遂相與評騭而授之梓。
嘉慶十有七年壯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謹序。
譯文
過去淳于公說:“人們擔憂的問題,是擔憂疾病多;醫生們擔憂的問題,是擔憂治病的方法少。”疾病多但是治病的方法少,沒有超過溫病的了。什麼原因呢?六氣當中,君火、相火不用說了,風、濕和燥沒有不同時具有溫,只是寒同溫相反,然而被寒邪傷害的人必定患熱證。天下的病哪有比溫病更多的病呢?記載和論述方劑的書從張仲景開始。張仲景的書專門論述傷寒,這只是六氣當中的一氣啊。其中有同時說到風的,也有同時說到溫的,可是講的風,是寒中的風,講的溫,是寒中的溫,因為他的書本來論述傷寒啊。其餘五氣,一概沒有涉及,因此後代不傳了。即使這樣,但是創作的人叫做聖人,闡述的人叫做賢明的人,學習的人如果徹底推求他們的文章,通曉他們的文義,變化它們,奉行它們,用它們治療六氣造成的疾病是可以的,用它們治療內傷也是行的。無奈社會上缺少善於觸類旁通的有才識的醫生,—般人認為缺漏可恥,不能舉—反三,只求按照圖樣尋找好馬般地就傷寒而論傷寒。
從王叔和以以下,大約都用治傷寒的方法療六氣造成的疾病,這好比用細葛布擋風,指鹿為馬,到治療時立即失敗,也知道他們的醫術粗疏了。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就仍舊襲用原來的方劑,稍微改變藥味,沖和、解肌等方劑就紛紛地編錄到陶華的《傷寒六書》出現,於是竟然用臆造的治傷寒的方法療六氣造成的所有疾病,不僅僅對張仲景沒有講到的內容未能創發新的義理,就連張仲景已寫定的書也都遭到了竄改。社會上的普通人喜歡《傷寒六書》內容淺近,共同尊崇它,人民的禍害就頻繁了。又有一個名叫吳又可的,編著《瘟疫論》,其中的方劑本來是治療—個時期發生的時疫病的,但是社會上的人錯誤地用它治療每年一定季節出現的溫熱病門最後像方中行、喻嘉言諸醫家,雖然把溫病排列在傷寒之外,但是治療方法則最終沒有離開傷寒之中。只有金朝劉完素先生特別通曉熱病,超出各家,編著的《河間六書》分上中下三焦論述治療,而不墨守六經,近似暗室一燈,中流一柱。可惜他為人敦厚而缺乏辭采,他的論述簡略而不通達,他的方劑有時也駁雜而不純粹。繼承他的人又不能闡明其中的含義,彌補其中的疏漏。像張景岳這一流學習醫道的下等醫生,正在責怪他而且詆毀他。於是他的學術不能顯明,他的主張不能推行。社會上的平庸醫生遇到溫熱病,就沒有不首先發汗解表,用消積導滯法攙雜,接著就猛用攻下法或者亂用溫補法,輕病因為這個緣故而加重,重病因為這個緣故而死亡。如果僥倖不死就吹噓是自己的功勞,造成死亡便閉口不說是自己的過失,即使病人也只知道重病難以挽救,卻不了解藥物殺人。父親把這一套方法傳給兒子,老師把這一套方法授與學生,整個社會同一風氣,牢不可破。肺腑不能說話,冤鬼深夜號哭,兩千多年,大略相同,令人感慨不已!
我朝政治和協,學術昌明,著名的醫家一批批地出現,都知道從《靈樞》、《素問》探求醫學的本源,向張仲景的著作求教。自從蘇州人葉天士先生《溫病論》、《溫病續論》出現,然後依照溫病的名稱求取溫病的內容。喜愛學習的醫生都知道趨向正道,但是貪求常規的醫生仍舊各自認為老師的學說正確,厭惡聽取高明的理論。那些技術不高明的醫生又只稍微了解—些粗淺的內容,不能明白精闢的含義,在醫療實踐中運用它,很少能取得滿意的療效。我的朋友吳鞠通先生懷有救世的抱負,具有超人的智慧,酷愛學習,從不滿足,研究醫理力求精深,立下高尚志向,仰慕古代名醫,虛懷若谷,效法各家。他擔憂這·個社會對溫病蒙昧不清,於是傳述前代醫家的可為法式的語言,抒發平生的心得,窮盡溫病的源流,·寫成這部書。但是仍舊不敢自信,同時顧慮社會上的人也不相信這部書,因此在書箱裡收藏的時間很久。我認為學者的心本來沒有自信的時候,可是因為天下有非常多種溫病,卻竟然沒有對付、溫病的方法,幸運地獲得了這個方法,就應當趕快拿出來使它公開,比如拯救被水淹、被火燒的人,難道還等待整理帽子束結頭髮嗎?況且人們的心理沒有不同,高明的醫學理論不會與世隔絕,這部書一旦出現,揚子云那樣內行的人必定很快遇到,並且將有闡明其中的主旨,彌補其十的疏漏,使遭受瘟疫的人都有登上長壽境域的可能。這是天下後代的幸運,也是吳先生的願望啊。《折楊皇菩》這類通俗的歌曲,人們都能領會,張嘴而笑,《陽春白雪》這類高雅的歌曲,能跟著唱和的卻只有幾個人,從古如此。了解我或者責備我,完全聽憑當代的社會輿論,難道不好嗎?吳先生認為我的話正確,於是共同討論評定後交付刊印。
嘉慶十七年八月月半後,同鄉愚弟汪廷珍恭敬地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