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是在1957年3月10日,當時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正在北京召開,不久後就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
毛澤東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上主要講了3個問題:1、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對上海《文匯報》上開展的電影問題討論做出了評價;3、對具體辦報和新聞做了解讀。
這篇談話收 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86頁,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全文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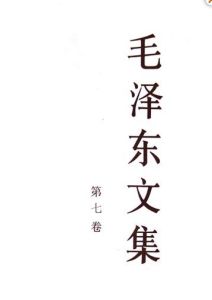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你們說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低,在社會主義社會辦報心中無數。現在心中無數,慢慢就會有數。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打游擊戰,打以前,我們就連想也沒有想過,後來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著頭皮打下去。當然,打仗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對於新出現的問題,誰人心中有數呢?我也心中無數。就拿韓戰來說吧,打美帝國主義就和打日本帝國主義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無數的,打了一兩仗,心中有數了。
現在我們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像過去搞階級鬥爭(當然也夾雜一些階級鬥爭),心中無數是很自然的。無數並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談社會主義的書出了那么多,教人們怎樣去具體地搞社會主義的書,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還沒有;也有些書把社會主義社會的東西什麼都寫出來,但那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有些事情還沒有出現,雖然可以預料到,卻不等於能夠具體地提出解決的方針和辦法。
說到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這是普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好好地學。當然,學是要自願的。聽說有些文學家十分不喜歡馬克思主義這個東西,說有了它,小說就不好寫了。我看這也是“條件反射”。什麼東西都是舊的習慣了新的就鑽不進去,因為舊的把新的壓住了。說學了馬克思主義,小說不好寫,大概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跟他們的舊思想有牴觸,所以寫不出東西來。
在知識分子當中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學他十年八年,馬克思主義學得多了,就會把舊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也要形成風氣,沒有風氣是不會學得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特點是否定一切,教條主義則把凡有懷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上學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觀察問題和了解問題。當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難。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沒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有關係。我們要用十年八年的時間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拋棄形上學的思想方法。那樣,我們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這次對電影的批評很有益,但是電影局開門不夠,他們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傾向,人家一批評,又把門關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數批評文章提出的問題,對於改革我們的電影是很有益的。現在的電影,我就不喜歡看,當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評凡是合乎事實的,電影局必須接受,否則電影工作不能改進。你們報上發表的文章,第一個時期批評的多,第二個時期肯定的多,現在可以組織文章把它們統一起來,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評。電影局不理是不對的。這次爭論暴露了問題對電影局和寫文章的人都有益處。
你們的報紙搞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青年不愛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條件反射”。一種東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愛看。
民眾來信可以登一些出來,試試看。政府和有關的業務部門有不同意見,報館可以和他們研究商量一下,在報上加以解釋,再看結果如何。一點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樣業務部門會犯官僚主義,不去改進工作。
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馬克思主義是按客觀情況辦事的,客觀情況就包括客觀效果。民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民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確的領導,有不正確的領導。正確的領導按客觀情況辦事,符合實際,民眾歡迎;不正確的領導,不按客觀情況辦事,脫離實際,脫離民眾。使編報的人感到不自由,編出來的報紙民眾不愛看,這個領導一定是教條主義的領導。我們要反對教條主義。我們過去用整風方式搞了好幾年,批判了教條主義,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報紙有一些專業化也好,好像《大公報》那樣,開放自由市場的時候,我就愛看它,因為它登這一類的東西多,又登得快。但是,太過於專業化,有時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興趣就少。搞專業的人也要看專業之外的東西。
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總比資本主義的報紙好。香港的一些報紙雖然沒有我們說的思想性,但也沒有什麼意思,說的話不真實,好誇大,傳播毒素。我們的報紙毒少,對人民有益。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裡。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
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寫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後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著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餘孽”,說他不行,但魯迅還是寫。現在經濟方面的雜文也可以寫。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
新華社的新聞受不受歡迎?聽說你們那裡有人提出通訊社的訊息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在階級消滅之前,不管通訊社或報紙的新聞,都有階級性。資產階級所說的“新聞自由”是騙人的,完全客觀的報導是沒有的。美國的通訊社和報紙,現在也報導一下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態出來給人看看,因為經濟危機壓迫著它。
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民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反對官僚主義也是這樣。“三反”的時候,有許多部長就是中央給他們端了梯子接下樓來的。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該接受教訓。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學、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
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歷史也很短,全國性辦報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有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其中的共產黨員不過是一個小指頭。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半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至於具體的科學技術,比如地質學,共產黨是不懂的。但是國民黨也不懂。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個地質人才,我們解放七年造就了一萬多。這種行政領導的狀況,在現在的過渡時期,只好這樣,將來是要改變的。
現在要爭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來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有個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們一下子貫通。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貫通的。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出版,只是馬克思主義體系形成的開始,還不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完成。要求知識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馬克思主義,這個要求是不現實的。說懂得馬克思主義,其實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也不多。作為專家是要讀多一點的,我們沒有那么多工夫,讀少一點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現在很多幹部沒有讀書的習慣,把剩餘的精力放到打撲克、看戲、跳舞上面去。大家不應該把時間浪費掉。
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新聞的快慢問題也是這樣。有的訊息,我們就不是快登慢登的問題,而是乾脆不登。比如土改新聞就是這樣,我們在報上不宣傳,免得傳播一些不成熟的、錯誤的經驗。前年年底,北京幾天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本來對這樣的訊息就要好好考慮,後來一廣播,各地不顧本身具體條件,一下子都幹起來,就很被動。
對人民內部問題進行批評,鋒芒也可以尖銳。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上辟一個專欄,當專欄作家。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
關於百家爭鳴問題,完全學術性的,在報上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至於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別一下情況。但是劃範圍也有困難,因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們說的節育和晚婚的宣傳,報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為要修改婚姻法,趕快去結婚。這樣,報紙也難辦。在舊社會,報紙上的東西老百姓看了等於不看,現在報上一登可不同了。如果發現宣傳上產生一些不良後果,可以寫文章來解釋說明,但是我們報上的文章往往不及時。至於範圍怎樣劃法,各報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其要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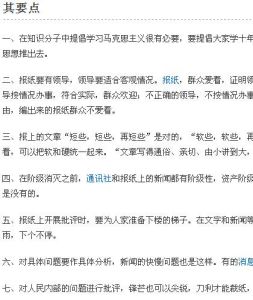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一、在知識分子中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很有必要,要提倡大家學十年八年,形成風氣,馬克思主義學多了,就會把舊思想推出去。
二、報紙要有領導,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報紙,民眾愛看,證明領導的好;民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高明。正確的領導按情況辦事,符合實際,民眾歡迎;不正確的領導,不按情況辦事,脫離實際,脫離民眾,使編報的人感到不自由,編出來的報紙民眾不愛看。
三、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
四、在階級消滅之前,通訊社和報紙上的新聞都有階級性,資產階級所說的“新聞自由”是騙人的,完全客觀的報導是沒有的。
五、報紙上開展批評時,要為人家準備下樓的梯子。在文字和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就是下毛毛細雨,下個不停。
六、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新聞的快慢問題也是這樣。有的訊息,我們就不是快登慢登的問題,而是乾脆不登。
七、對人民內部的問題進行批評,鋒芒也可以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尖銳的程度是幫人而不是傷人。
八、關於百家爭鳴。完全學術性的問題,在報上爭來爭去,對社會生活不會有影響;政策性的問題,就要分別一下情況。否則,有的問題報上文章一多,就會給社會生活帶來不良後果。
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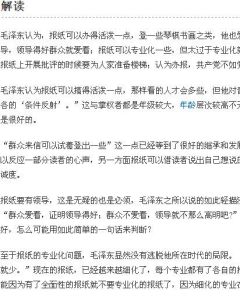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毛澤東認為,報紙可以辦得活潑一點,登一些琴棋書畫之類,他也愛看;民眾來信可以試著登出一些;報紙要有領導,領導得好民眾就愛看;報紙可以專業化一些,但太過於專業化就容易枯燥;社會主義的報紙總比資本主義的好;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認為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
毛澤東認為報紙可以搞得活潑一點,那樣看的人才會多些,但他對青年似乎是不屑的,“青年不愛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條件反射’。”這與掌權者都是年級較大,年齡層次較高不無原因。時至今日,看黨報機關報的青年也確實還是很好的。
“民眾來信可以試著登出一些”這一點已經等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展,現在的許多報紙都有類似的版塊。一方面這可以反應一部分讀者的心聲,另一方面報紙可以借讀者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也可以藉機拉攏讀者,培養讀者對報紙的忠誠度。
報紙要有領導,這是無疑的也是必須,毛澤東之所以說的如此輕描淡寫,是因為他相信這個道理大家都是很明白的。“民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民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么高明吧?”這明顯就有調侃的味道在裡邊了,領導得好與不好,怎么可能用如此簡單的一句話來判斷?
至於報紙的專業化問題,毛澤東顯然沒有逃脫他所在時代的局限。“太過於專業化,有時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興趣就少。”現在的報紙,已經越來越細化了,每個專業都有了各自的報紙,全面化的報紙要有專業化的報紙也要有,不能因為有了全面性的報紙就不要專業化的報紙了,因為細化的專業在市場經濟下才具有別人所不具有競爭力。
至於社會主義的報紙總比資本主義好,這一條就不用解釋和反駁了。需要澄清的一個誤會是,毛澤東並不認為魯迅在1957年還活著的話,不是蹲監獄就是閉口不言了。“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由此可以看得出,毛澤東對魯迅還是懷有很深的敬意的。
“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民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這話聽上去特溫情,其實卻是養虎為患,逼人跳樓總比等民眾把那座樓拆了的好。當然,毛澤東並沒有做的這么溫情,只是那時的出發點已經變了。
認為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這顯然是毛澤東的自謙之詞,你都領導了法號司令了,現在你卻說你不如黨外人士,當然黨外人士明白,共產黨是不可能讓賢的,所以接下來毛澤東就說了,“現在要爭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來學習馬克思主義”,這樣黨外人士自然也就是黨內了。
接來下毛澤東談了對於新聞的一些看法:新聞的快慢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人民內部問題進行批評鋒芒也可以尖銳;完全學術性的問題在報上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
“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新聞的快慢問題也是這樣。有的訊息,我們就不是快登慢登的問題,而是乾脆不登。”作為黨的喉舌,在這裡就得到了具體的體現,說話是因為說的話能產生好的影響。
比較有意思的是,毛澤東“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這和評論員文章、特邀評論員文章、本報評論員文章、社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有時候因為那些話是特地的人說的,就變得微言大義舉足輕重了。總體來說,現在的報紙也還是很好的貫徹了這一點的。
毛澤東認為完全學術性的問題,在報上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至於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別一下情況。這個說法也是相當明智的,只是到底怎樣的問題是學術性的問題、怎樣的問題又是政策性的問題、而這些又是由誰來定義,毛澤東就沒有說明了。
相關考證
關於毛羅對話“如果魯迅活著會怎樣”的真實性考證
1957年,羅稷南問毛澤東,如果魯迅活著會怎樣?回答的大意是:要么坐在監獄裡繼續寫,要么不作聲。有以下證據支持這個毛羅對話的真實性——
魯迅之子周海嬰的《魯迅與我70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1年9月第1版。書中第370-371頁寫道:1957年,“此時正值‘反右’”,毛澤東去上海小住,找一些同鄉聊聊。“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構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會怎么樣?”毛澤東對此“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周海嬰說,是一位“親聆羅老先生講述的朋友告訴我這件事的”。
上述這個“朋友”,叫賀聖謨,曾任寧波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2001年11月2日《寧波教育報》和同月6日《寧波晚報》發表了賀聖謨的一篇文章《“孤證”提供人的補正》。文中糾正了周海嬰在一些細節敘述上的錯誤,但並不否認他對周海嬰所說毛羅對話內容的真實性。他重述了羅稷南對他說的話:“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請一些人座談。會上我問毛主席,要是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毛主席回答說,無非是兩種可能,要么是進了班房,要么是顧全大局,不說話。”
電影演員趙丹的夫人黃宗英在2002年第12期《炎黃春秋》上撰文《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敘述了她所記得的毛澤東的回答:“‘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
黃宗英提供了更多的細節:一、毛羅對話時間是1957年7月7日;二、發生毛羅對話的坐談會的照片,在1957年7月11日的《光明日報》和1957年7月9日的《解放日報》上登載,並在2001年中國電影資料館為慶祝黨的誕辰80周年攝影圖片展覽上展出;三、與會各界人士共36人;四、當時的上海市領導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也參加了座談。
羅稷南還向侄子陳焜講述過毛羅對話的內容。2002年第3期《北京觀察》上登載了陳焜致周海嬰的一封信,說——“1960年,我從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養病住了幾個月,聽伯父講過那次接見的情況。他說,毛主席進來坐定以後,有人遞了一張在座人士的名單給他。毛主席看了名單,就挑了伯父第一個和他談話。他們先談了一段他們以前在瑞金相見的事,毛主席又謝謝伯父翻譯了《馬克思傳》,說他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後來毛主席問伯父有沒有什麼問題,伯父想了一下就問,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毛主席沒有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後才說,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他大概不是關在牢里,就是不說話了。”
但有很多人對毛羅對話的真實性持否定態度,主要證據是收在《毛澤東文集》第7卷中的那篇《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文中明確提到,“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毛澤東的回答中有這樣的話:“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的日期是1957年3月10日,於是,持否認態度的人就說,是一些人把毛澤東3月10日關於“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說的話,篡改後移到7月7日去了。
比方說,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陳晉就竭力否認毛羅對話的真實性。他在《百年潮》2002年9月號上發表了《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一文,提出:“正是在3月10日召集的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會上,毛澤東直率地談起了‘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
然而,正是陳晉這篇文章,於不經意間披露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他在引用毛澤東談“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那一大段話後說了這樣的話——
“這段話,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新華社聯合編選、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不過,在這篇座談記錄稿上,並沒有記載‘魯迅活著會怎樣’這樣的話題。”
也就是說,根據《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的原始記錄,毛澤東1957年3月10日根本就沒有回答過“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問題,現在我們看到的毛澤東的回答,是26年之後整理成正式文稿時加上去的。
毛澤東的講話在以後正式發表時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需要而進行修改和補充,這是常有的事。
因此,認為,毛澤東在1957年3月10日並沒有回答過“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在同年7月7日毛羅對話中回答的。後來公開發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時,重新編寫了毛羅對話,並迴避了魯迅可能“關在牢里”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