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人淡如菊》講述的是在英國留學的喬景仰英籍中年教授納梵的學識和人品,深深地愛上了他。畢業後,喬回到香港。由於思念日甚,喬無心工作,重返英國後,成為納梵的情婦。納梵卻無法承受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巨大壓力,喬母將女兒許配給留學生陳家明。由於家明的勸戒,喬對往事略有所悟,在無奈與憂傷中,黯然回到香港。感情這樣東西,無法解釋,也只好推給前世,明明沒有道理可喻的感情,偏偏這么多……
作者簡介
 亦舒
亦舒她美麗而豪爽,“有著追求理想的翅膀”,因之她的小說充滿幻想色彩——虛無飄渺,卻又執著而不肯放棄。她更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與觸覺,有擅於將平凡的字眼變成奇句的才華,她的寫作正如她的人,麻利、潑辣,而又快又多,但即使換上十個筆名,讀者也不難一下子從作品中把她辨認出來。
至今,亦舒的作品已結集出版的有七十種,代表作是《玫瑰的故事》、《喜寶》、《朝花夕拾》等。
書摘
我跟羅蓮說:“比爾·納梵是最好的教授,他從來不當我們是孩子。”她笑,“可惜他講的是熱力散播。”
我說:“那沒有關係,我可以選他那科。”
她說:“他那科很難,他出的題目也很難,我最怕的,他一說到宇宙線紫外線,我的頭都昏了,你想想,一個原子,有幾層外殼?”
我笑,“第一層叫K層……”
羅蓮說:“好了好了,別背書了,你也是的,這么窮凶極惡地念書,但是你算好學生,同學也喜歡你。”
我說:“我對基本的常識有興趣。你想想,原子有什麼不好?我喜歡。”
“納梵下半年教你吧?”
“唔,聖誕之後,他還是教我們的。我不是不喜歡高克先生,他的化學與生物都合理得很,我還是等納梵。”
我們一路走回家,五點鐘,下微雨,一地的落葉,行人大半是學生了,馬路中央塞車。天氣相當冷,我嘴裡呵白氣,穿著斗篷,既防雨又保暖,羅蓮撐著傘,遮著我。
回家要走十五分鐘。
羅蓮說:“你真很厲害,去年一上化學課就哭,倒叫高克老師向你道歉,什麼意思?結果三個理科老師嚇得團團轉,B小姐叫我教你,高克叫我盯住你,納梵說:‘叫她別怕,慢慢地學。’真了不起,誰不交學費?你那種情形,真肉麻,真可怕!”
我笑笑。
她比我高一級,常常老氣橫秋地教訓我。去年三個教授趕著她來照顧我,她就不服氣,跑來見到我,就冷笑說:“我以為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卻不過是個瘦子,擠一擠便可以塞進汽油箱裡去。”後來她對我很好,一直照顧我,有難題也指點我,過了一年,我們索性搬到一起住,相處極好,一起上學放學,別有樂處。教授叫她找我,認識我,只因為全校只有我們兩個是中國人,現在卻成了好朋友。
到了家裡,暖烘烘的,我們坐在一起做功課,晚飯早在學校飯堂吃過了。
她沖了兩杯咖啡出來,我一路翻書,一路說:“納梵先生的樣子不漂亮,但是真……真特別,一見難忘。”
羅蓮說:“你一整天提他,大概是有點毛病了。”
我說:“什麼毛病呢?我又不會愛上他。”
“愛上他是沒有用的,他又有妻子又有孩子,人這么好,你想想去,別提他了。”
我看了羅蓮一眼。
我是不會愛上納梵先生的,又不是寫小說。
不過他是一個好教授。
去年在飯堂見到他,我就欽佩他,忽然之間問他:“你是博士嗎?”
他笑了,他說:“我只是碩士。”
我居然還有膽子問:“為什麼你不是博士?”天下有我這種人,非逼教授做博士不可。
他說:“讀博士只管那極小極小的範圍,我不大喜歡,我讀了好幾個碩士,我現在還在讀書。”
我睜大了眼睛,“是嗎?”
羅蓮在我身邊使眼色,我才不問了。
後來羅蓮說:“他總是個教授,你怎么老問那種莫名其妙的事?”
我才怕起來,以後看見他,遠遠地笑一笑,然後躲得人影都沒有。一年來我讀那幾門理科,不遺餘力,別人都是讀過的,只有我一竅不通,什麼都得背上半天,整天就是躲在屋子裡念念念。
結果還考得頂不錯。五道題目,我答了兩道納梵先生的,他的“紅外線對人類貢獻”與“原子結構基本講”。大概是答得不錯的。
後來羅蓮看見他,第一件事是問他:“喬陳考得好嗎?”
納梵先生說:“很好呢!這孩子,以前嚇成那樣子。”
B小姐也問:“另外那箇中國女孩子好嗎?”
教會計的戴維斯先生因為在香港打過幾年仗,很喜歡中國人,新開學,他也去問羅蓮:“喬陳好嗎?有沒有見她?”
羅蓮翻翻白眼,“當然見過,她現在與我同住。”
回來羅蓮大發牢騷。
她說:“我也是中國人,為什麼他們不問問我怎么了?嘿!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眉開眼笑,“我遲鈍,沒有他們我不行,而且我聽話。”
“真受不了。”羅蓮說。
我默默地做著功課。
我喜歡去上課,這就夠了。
第二天羅蓮遲放學,我一個人走回家,才出校門,就見到納梵先生迎面而來,他六呎一時高,捲髮,濃眉,實實在在不算漂亮,可是他的臉上有一種懾人的神情。我遲疑了一下子,笑一笑,低頭走了。
臉上莫名其妙地紅了起來。
納梵老師手臂下夾著一堆書,從圖書館裡回來?他是這樣的大方、和藹、有教養、學問好、心情好,風度翩翩,穿著那么舊式的西裝,普通的皮鞋,一點不打扮,那種姿態,卻是驚人的好。
難怪人家說:最危險是讓丈夫去教女子大學。念大學那種年紀,多數是無法無天的,不危險也變危險了。一年來大半學生都找到了對象,只除了我,我沒有男朋友,也沒有愛人。
羅蓮有一個男朋友,是奧地利人,她是很起勁的,天天一封信,還說聖誕要去看雪。我覺得歐洲人不過如此,想免費游東方,不如娶一個東方太太,或是嫁一個東方來的丈夫。歐洲這么冷,去享受一下熱帶的溫馨,有什麼不好?在這裡讀書的學生,家裡都不會太差,他們也就是看中這一點。依我看來,中國女孩子除非長得特別美,否則不必與外國人混,得不到什麼好處。
外國人也有好的,像納梵先生,我想他的人格是毫無問題的。我喜歡科學家。
他這個學期頭一個月沒有教我們,過了聖誕才教。
學期開始的時候,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台上,獨獨他不在,我就到處問:“納梵先生在不在?”
他們都叫我放心,納梵先生快要做副校長了,走不了的。
但是這么多的老師,我反而與他最不熟。
在飯堂里休息著,他來買咖啡喝,排隊排在眾學生當中,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他微微地笑著,他穩重得像一座山一樣,他是這么可靠,任何女人看了他,都想:嫁給他必然是不用再擔心任何事了。
同學說:“你看,那是你的納梵先生。”
我笑一笑。
他們的意思是,那是你心愛的教授。
我們這間學校小,所有的學生加在一起,不超過一千,每個人都認識彼此,這是小大學的好處。而每個教授都認識我。
他們問我:“你去年回家了嗎?”又問,“今年回不回去?”我總是老實地有一說一,有二說二。
我不大懂得他們的幽默,動不動就大驚失色,信以為真,他們倒是很欣賞這種天真,我自己真懊惱這種遲鈍,直到今年,那種呆瓜勁兒才改掉了一點,然而還是惹笑。
老師們很曉得我這個人。他們要找我,就到圖書館,我好歹坐在那裡,無論看什麼書都行,我都坐在那裡。
去年學生罷課,只有我一個人上學。老師看見我,心花怒放。
我坐在圖書館里讀筆記。
高克先生來了,看見我,趨向前來,握著手,眉開眼笑:“啊,喬,你多么乖,坐在暖氣邊,在溫習嗎,不冷嗎?”
我笑。發神經了,他把我當三歲小孩子了?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匪夷所思。
有時候納梵老師也來看報紙,或是印講義,他總是在忙,我在一層層書架子後面看著他。心裏面很定,縱使有什麼事,大概可以找他幫忙。
他去年一直說:“你知道我在哪裡,有難題請來找我。”
他不叫我“喬”,不叫我的名字。別的教授一天到晚叫著我。他也不點名,不過凡是他的課,教室總是滿的,他不把我們當孩子。
新近規定,凡學生上課次數少過百分之七十五者,不準參加考試。
他不管,他覺得學生該有自律能力,點名沒有用,點得再凶,那些逃學學生還是逃學去了。
但是去年我沒有找過他。他把什麼都講得這么明白,還有什麼好問的?
納梵教授跟學生說話的時候,老是側著臉,開頭我不大明白這個姿態,後來才曉得他右耳是聾的。讀大學的時候,他玩美式足球,被同伴一腳踢在頭上,昏在草地上,進了醫院,出來的時候,一隻耳朵就聾了。
羅蓮嘆道:“真了不起,連缺憾美都有了。”
我聽得津津有味。他畢業於諾丁大學,羅賓漢出沒的地方。雖然也是科學家,但他沒有那種MIT、CIT的高深莫測,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有那種深人民間的高貴氣息,我喜歡他。
羅蓮已念到最後一年,笑話自然多。
她對我說:“你曉得考萊小姐?每星期四她都有課,但是大家星期三玩得七葷八素,星期四哪裡起得了床?一班十四個人只到了四個,她等了一刻鐘,不見第五個人影,就衝下去報告校長,哪曉得一走,就來了六個,氣得她什麼似的!哈哈哈。”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笑,這真有點殘忍。據羅蓮說,在外國生活,不殘忍是不行的。我倒不覺得,至少我沒有那樣,我也活得很好。
羅蓮說:“你是例外,你一皺眉,老師同學就相讓於你,不知道為什麼。”
我倒還沒有為誰皺過眉,只記得去年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就哭,哭得不亦樂乎。今年擠來擠去,擠不出什麼眼淚來了,天大的事,推在明天再說,功課再多,一樣樣慢慢做還是可以的,只是實在多了,做起來未免辛苦。周末非但沒有休息,反而變本加厲地忙,晚上做到二三點才睡。第二天一早又撐起來,不敢貪睡。那種熬法也不用說了,不過心裡還是很快活,也說不清楚是為什麼。
有時候問羅蓮:“你猜升了第三年,我吃得消嗎?這么多的功課。”
“人家是人,你也是人,”她說,“怎么做不了?最多他們花一小時,我們花兩個鐘頭也就是了,一般是老師教出來的。”
她這個人信心真足,走步路都好起勁啊,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我走路卻始終無聲無息,腳步好輕的,不知道是什麼習慣。
過了聖誕,納梵先生終於出現了,大家都很高興。讀理科的人總比較講道理,我老有一種感覺,文科是不能讀的,越讀越不通,越讀越小氣,好的沒有,壞的都齊了,結果變成自高自大、極端自私的一個人。我們還沒有念完書,不能算數,但是看看那些學成的人,也就有點分數。亦不能讀藝術,學藝術的人都有一種毛病,不管阿狗阿貓都先以藝術家姿態出現,結果大部分做了現世的活招牌。
當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個個像納梵先生,他是例外中的例外。念文學藝術的,也不見得人人差勁,不過我們運氣好,正巧碰到一個好老師。
一星期有他兩節課,每節只一小時,一共上十一個星期。他常常遲到十分鐘,方便大家去喝杯茶,大家感激他。上課時草草在黑板上描幾幅圖,簡單地解釋幾句,就很明白——如果我明白,那誰都明白,誰還比我更鈍呢?怕沒有了。
有時候不明白,我舉手發問。
同學都笑我,說我這么大了,還像小學生,次次發問都舉手,我一舉手,他們就嚷:“喬陳又要告狀了!”
納梵先生微笑說:“不必舉手。”
我漲紅著臉分辯:“如果不舉手,不給老師準備,就插嘴,那有什麼好?”
納梵先生還沒答,眾同學又笑說“好啦好啦!教授變了老師,大學變了書館,咱們都成了小孩,也不必投票選舉,回家乾脆抱著叫媽媽。”
他們只是開玩笑,我知道我很規矩,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師重道,哪像他們這般無法無天?一時改不過來。
我漲紅了臉,訕訕地過了好幾堂課。
有一天在圖書館,我與納梵先生撞個正著,我稱呼他一聲:“納梵先生。”
他站住,微笑問:“什麼事?”
我說:“沒事啊,我叫你一聲。”
他詫異地問:“為什麼?”
我答:“理應如此啊。”
他說:“你家那邊的老師是怎么樣的?”
“他們?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但凡課文說得明白,已算盡責了。”
我說:“階級分得好明白,否則,學生恐怕倒霉,這是中學,大學不得而知,看來也絕不民主。”
“你覺得哪種制度好?”他極有興趣。
“我不知道,”我老實地說,“這裡的學生太放肆了,我覺得。我讀的中學是很好的,老師也待我客氣,只是幾個英籍老太太很作威作福。”
“我代她們致歉。”納梵先生笑說,“只是你別太拘謹,有什麼想說的,不要猶疑。”
我點點頭。
我跟他說話,老是有點口吃。
羅蓮說:“他好做你爹了,你幾歲?”
“二十歲了。”
“可不是?他起碼三十八。”羅蓮說,“看上去倒是很年輕的樣子。”
“也不算特別年輕,”我說,“只不過頭髮未白而已,不過他一向不老氣橫秋。”
“你不是真看上他了吧?”
“哪裡啊!別開這種玩笑,我是很尊重老師的。”我說,“人人都說他好。”
“很多教授都很好,你怎么不提他們?”
“我也提呀!”
“你這個人,將來人家都要討厭你的,一副模範生的樣子,決不遲到早退,颳風落雨,一向不缺課,見了教授,‘是老師是老師’,真受不了。”
我白她一眼。
我可沒有她形容的那么肉麻。
她胡謅的。
星期二,照例有實驗,我並不太喜歡做化學實驗,瓶瓶罐罐,麻煩得很。大家穿上了白上衣,拿了講義,照著煮了這個又煮那個,我的手腳不十分靈敏,常常最慢,弄得一頭大汗。
我把煤氣火點著,煮著蒸發器里的化學顏料,納梵先生走過來,問我:“好嗎?”
我說:“煤氣有點聲音,是不是?”
他側耳聽了聽,“嗯,是,熄了它,我替你調整調整。”
我遲疑了一下,聽他的話,關了煤氣。
納梵走回去幾步,向一個女同學借來打火機,點一下,沒點著。
我探過去看,他再點火,我只聞到一股煤氣味,跟著只是輕輕的一聲爆炸,我眼前一熱,一陣刺痛,退後已經來不及了,我蹲了下來,只聽見同學的驚呼聲,我一急,一手遮著眼睛,一手去抓人,只抓到一隻手,便緊緊地捏著不放。
實驗室里亂成一片。
納梵先生大叫:“去打電話,叫救護車!快,快!”
我馬上想:完了,我一定是瞎了。
眼睛上的痛一增加,我就支持不住了,失去了知覺。
醒來的時候,我還是看不見東西。我躺著,身子好像在車上,一定是救護車。有人在替我洗眼睛,我還是覺得痛,並且害怕。
但是我沒有吭聲,如果真瞎了,鬼叫也沒有用。然而怕還是怕的,我伸手出去摸,摸到的卻是女護士冷冰凍的制服。我忽然哭了。
天啊!如果一輩子都這么摸來摸去,怎么辦?
我不知道有沒有眼淚流出來,但是我聽見一個聲音說:“別怕,我們就到醫院了。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抓住了他的手。
“說給我聽,你感覺如何?”
我想要說話,但是太害怕了,什麼也說不出來,只緊抓著他的手。
護士說:“不是很厲害,她不想說話,就別跟她說。”
……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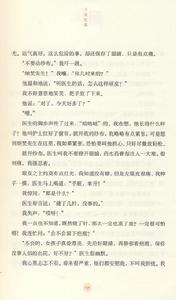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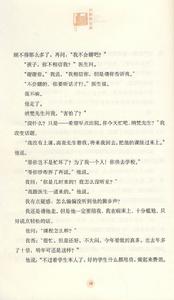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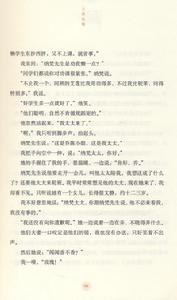
網友書評
一
剛剛看完亦舒的《人淡如菊》,陷入深深的糾結中。
我每次看完她的小說都會糾結一會。
有點像國中時看安妮寶貝的感覺。不過我覺得安妮的前期文字是濃郁的狠,而師太的是淡淡的冷。
濃郁的狠猶有竟時,所以安妮後來成熟了,圓潤了,平靜了。
而淡淡的冷就不好說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心智的成熟,要么就更加包容,要么就一副看破紅塵的樣子反而更落得一股一針見血的犀利。
師太的書太多了,也不好評價,但至少我看的幾本,都是這樣的感覺,冷冷的,但是不會叫你撕心裂肺的疼痛,只是在你心上輕輕劃開一道口子,叫你看見真相的疼,然後無奈的輕嘆。
二
《人淡如菊》因為喜歡這個名字,所以便買了。
是講師生戀的,中國女子和英國教授。
師太筆下的女子至少我看過的裡面,都是又漂亮又獨立,說話做事成熟又保有幾分直爽的可愛。
而男子或者成熟睿智或者風度翩翩或者人財俱佳,但就是給人一種無能的感覺,沒有能力和勇氣去保護自己愛的人。
太理智太瞻前顧後反而喪失了最佳的行動力。
不知道師太塑造這樣的人物時是不是自己也經常陷入YY狀態,應該也是一個標準女性主義者吧OML。。。
即使內容是涉及這樣一種愛戀,筆調也是淡淡的,沒有驚心動魄,但是你能感受到那種不同常情的愛戀所帶來的刺激和歡愉。
只是,曾經費盡心機的想要在一起,曾經以為這輩子都只會愛這樣一個她尊敬她迷戀她無法忘懷的“老師”,卻終敵不過彼此的差異和時間的考驗。
就是累了,所以最後女子離開了。
三
第一次拜讀亦舒的作品,是因為這個書名,如此清淡,如此優雅,人淡如菊?是寫人性的淡薄,還是寫人生的清涼,幾分疑惑,幾分激動。封面設計也非常簡潔,白底,一枝鍍銀花,很乾淨。第一印象很美。
讀了幾頁之後,知道這是一個愛情故事,我本身不太喜歡讀愛情故事的,總感覺愛情很不理智,而且電視電影的看多了,被那些花花綠綠、各種各樣的愛情故事麻木了,一個故事看來是震動的,兩個故事看來是感動的,三個,四個多了以後就沒有感覺了,千篇一律講得一個東西。我是本著這個書面看完的。亦舒的文筆真如這個名字,清雅,沒有太多華麗的詞藻,把一個故事用很平淡的語氣就敘述完了,讓人很容易的接受了。這種風格很好,而且還不乏一些幽默的筆調,很適合像我這樣宜於安靜的人看。
故事是以第一人稱來寫的,講在英國留學的喬崇拜已有家室的教授納梵先生的學識和人品,深深地愛上了他。畢業後,喬回到香港。由於思念日甚,喬無心工作,重返英國成為納梵的情婦。納梵卻無法承受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巨大壓力,曲曲折折之後,發生很多故事之後,喜歡喬的彼得,還有同是中國人的家明……之後喬母親讓女兒與家明訂婚。由於家明的幫助和勸戒,喬開始意識到自己該怎么做,在無奈與憂傷中,黯然回到香港與家明結婚。
故事不能說不動人,不能說不曲折,只是感覺看了如此多的電影電視,也就覺得這個故事多少普通了一些。但我時時還是被喬牽著,跟著故事走了下來。
怎么說呢,故事的寫作風格我喜歡,正如這書名,淡淡的感覺,很美好,故事也可以,有曲折有人之常情,只是只是……總之對愛情故事感動不起來。
不過,我覺得此書的一大亮點,對喬心理的點滴變化乃至成長過程,刻畫得非常逼真,有點年輕人的味道和衝動。
如果要看愛情故事,這書肯定調不起你們的味口啦,不過要欣賞淡淡的文字,自己在一間小屋裡看這本書確實不錯的。呵呵。
亦舒的作品集
| 亦舒的作品以情節取勝,故事往往跌宕起伏,環環相扣,結局受歐·亨利的影響,常常出乎意料,富有傳奇色彩。在語言形式上,亦舒小說都是以一、兩句話為一個段落:跳躍性大,節奏感強,這各香港惜時如金的緊張生活很吻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