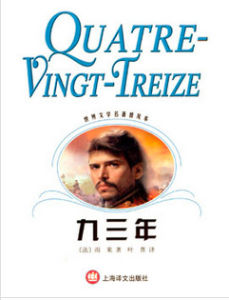內容簡介
故事發生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急風暴雨時代,發生在共和國誕生不滿一歲、革命與封建復辟勢力生死搏鬥的1793年。5月,巴黎國民軍的一個“紅帽子聯隊烈樹林裡搜尋時,發現了在飢餓中的農婦佛萊莎和她的三個孩子,並收留了他們。6月1日傍晚,大霧之中,從英國”在布列塔尼的索德一個海島起航了一隻偽裝成商船的軍艦,船上有逃亡的法國保王黨軍人,還載著一個農民打扮的重要人物朗特納克侯爵,他戴著皇后在塔堡監獄繡的百合花統帥綬帶,被秘密派到旺代發動十萬盲目忠於國王的農民軍叛亂,迎接英國人登入,企圖一舉把法蘭西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
軍艦起航前,共和國方面已得到情報,並通知巡邏艦俘獲此船,將朗特納克送上斷頭台。不料這一軍艦由於途中一尊發射二十四磅重炮彈的大炮滑脫,船員無法控制,終於迷失航向,誤觸暗礁,滑脫的炮身又撞漏了船,撞壞了一半以上的大炮,船身不斷下沉,炮手又因玩忽職守而被槍決。在這危急的當口,法國巡邏艦艦隊又出現在面前,無論是迎戰還是後退,結局只有一個,那就是必然毀滅。為了完成以旺岱為基地摧毀新生的共和國,使王室、貴族的反革命勢力起而復生的使命,艦長派一名勇敢的水手阿爾馬羅用小舢板護送侯爵逃生。
朗特納克侯爵在布列塔尼一個海灣登入,在小山頂的碑石上發現了通緝他的告示,署名的海岸遠征軍司令正是他的繼承人,他的侄孫郭文子爵,他內心升起無比痛恨的火焰,決意與這一家族的叛逆勢不兩立。上岸次日,他便找到報復的機會,在山下村子裡,他正好與剛剛占領這村子的七千旺岱軍隊相遇。在他的命令下,這幫反革命匪徒把戰鬥中俘獲的巴黎聯隊士兵全部槍斃,包括那個被聯隊收留的母親,把村子燒光,把三個孩子帶走。
在巴黎,英勇的市民興高采烈地慶祝革命的勝利。在一家小酒店裡,革命的領袖羅伯斯庇爾、丹東、馬拉正共同商量解除共和國巨大潛在危機的辦法,為了消滅威脅革命的旺岱叛軍,國民公會委派西穆爾登為海岸遠征軍司令部政治委員,並由他們三人正式簽署了公安委員會的正式委任令。他們說,西穆爾登有全權去監視那個司令官,因為這個年輕的貴族雖然很有軍事才能,又很勇敢堅強,已經打敗了年老的朗德納克,但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寬恕、待人慈悲,他釋放俘虜,認為強者對弱者有保護的責任,他不願殺死已經趴在地上的人,總之他有半顆柔弱的心。但革命對反革命是絕不能寬大的,尤其對那個頑固的反革命侯爵;同時革命對那些寬恕反革命的人也絕不能容忍。
當西穆爾登聽到司令官的名字是郭文子爵時,頓時臉色蒼白。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世界上唯一的親人。西穆爾登以前是個教士,他有一顆純潔高尚然而憂鬱的心,他善於思考、博學多才,雖然科學毀滅了他的信仰,他卻一直守著教士的戒律,孤身一人。他曾把全部愛情傾注在一個孩子身上,那是他年輕時在布列塔尼的郭文家族當家庭教師時的郭文子爵。這是一個無父無母、由叔祖父朗特納克侯爵撫養的孩子,他把自己的知識、信仰、意識、道德、理想、人民的靈魂都灌輸給這個貴族子弟。一次郭文重病,他日夜守護在床邊,挽救了孩子微弱的生命。孩子長大成人,當了上尉出發到軍營去了,他們再也沒見過面,只能相互思念。
西穆爾登憎恨諾言,憎恨專制政體,憎恨神權,他曾幻想共和,終於成為一個冷酷、堅定的革命者。西穆爾登日夜兼程趕到旺岱時,正遇上共和軍與叛軍的廝殺,他用自己的身體又一次拯救了郭文的生命。他凝視著久別重逢的親人,淌著血的臉上閃耀著快樂的光芒,郭文叫著“恩師”跪在他的身旁。
西穆爾登看到昔日的孩子已經變成勇猛的戰士、一個屢建戰功的指揮官、革命的柱石和英雄。他夢想他將會成為舉世聞名的軍事領袖,披著光閃閃的鎧甲,前額閃著正義和理性的光芒,好像看到自己的靈魂化成偉大,但幸福的面容上隨即掠過一層陰影。
儘管朗特納克也是個軍事領袖,並且更殘酷、更狡猾、更瘋狂,但在搏鬥中,總是代表正義與革命的郭文占上風。最後,不但陰謀未能得逞,還被打得走投無路,幾乎全軍覆沒,只剩下十八個人退守到富耶爾森林角上他們家族的一個廢棄的舊碉堡里,那是一座基牆厚達十五尺的圓形高塔,出口是個牆洞。高塔與高地由一座石橋相連,橋墩上有一座三層城堡,他們把三個孩子帶入其中作為人質,下層堆滿乾柴、柏油,第三層置放乾草。而從橋上進入城堡的厚鐵門的鑰匙放在侯爵口袋裡。一根硫磺引線從鐵門下拉入高塔,這樣使得共和軍無法從橋上進攻高塔。勇敢的共和軍先鋒隊在郭文的指揮下從牆洞向高塔中的敵人發起勇猛進攻,“紅帽子聯隊”曹長巧妙地從炮眼爬進碉堡,里外夾攻,敵人大敗,只剩下侯爵幾個人從壁上一個能轉動的石頭暗門逃跑了。
但是負責斷後的一個敵人臨死前點燃了引線,橋頭的小城堡大火騰空而起,被乞丐救活的佛萊莎在火光中從窗戶看見了房中酣睡的她的三個孩子,大呼救命,這喊聲驚住了已經脫險的侯爵。共和軍打不開鐵門,又沒有梯子,正為救不出孩子而焦急萬分。這時候,侯爵出現了,他手裡拿著鑰匙走向鐵門。之後,他的白髮在火光中閃現,從樓里豎下一架梯子,把三個孩子一個個送下來。然後他束手就擒,被押在地牢里。
西穆爾登連夜召開軍事法庭會議,定於次日處侯爵絞刑。然而侯爵用自己的自由換取三個孩子的生命的舉動引起了郭文劇烈的思想鬥爭。郭文認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是上帝賦予他的責任,他決然放走了侯爵,自己留在地牢中。為了這一寬恕,西穆爾登按革命法律判處郭文以絞刑,施刑的前夜,他來到地牢中與他的孩子一同進餐告別,內心充滿痛苦。天色微明,當郭文被執行絞刑的同時,一聲槍響,西穆爾登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作品目錄
第一部
在海上
第一卷索德雷樹林
第二卷克萊莫爾號軍艦
第三卷阿爾馬洛
第四卷泰爾馬克
第二部
在巴黎
第一卷西穆爾丹
第二卷孔雀街的小酒館
第三卷國民公會
第三部
在旺代
第一卷旺代
第二卷三個孩子
第三卷聖馬托羅繆的屠殺
第四卷母親
第五卷INDAEMONEDEUS
第六卷勝利之後的鬥爭
第七卷封建與革命
創作背景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一八六二年雨果還在根西島流亡時就開始
為醞釀中的這部小說蒐集材料,他閱讀了大量有關書籍,作了充分準備,十年後動筆寫作,花了六個月的時間一氣呵成,於一八七四年二月出版。
九三年指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七九三年這個充滿急風暴雨的年代,也是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展開生死搏鬥的年代。這年年初,新生的共和國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國內外反革命勢力聯合進行瘋狂的反撲;國外,英國夥同普魯士、奧地利、西班牙等國組成反法同盟,從東、南、北三面進攻法國;國內,保王勢力在旺代發動叛亂,威脅巴黎,企圖裡應外合,把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復辟封建王朝。革命政權採取果斷措施,大力平定旺代叛亂,嚴厲鎮壓反革命,造成了法國歷史上著名的“恐怖時代”,使共和國轉危為安,為法國革命的徹底勝利奠定了基礎。[4]
點評鑑賞
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展開的生死搏鬥的正確描寫是這本小說的基本價值所在。雨果以深邃的社會歷史眼光和磅礴雄偉的氣魄,用如椽的巨筆,描繪了一幅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真實生動的歷史畫卷。小說以旺代叛亂與平定叛亂的鬥爭為背景,以三個孩子的命運為線索,描寫了革命與反革命、共和與保王兩黨之間那場血與火的慘烈嚴酷的內戰,再現了新舊兩種制度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殊死較量,揭露了保王勢力的兇殘沒落,歌頌了以國民公會為代表的新生革命政權,同時也表現了作者一貫的人道主義思想。
《九三年》的中心情節是圍繞著郭萬、西穆爾丹、朗德納克三個主要人物來構思的。雨果為他們安排了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們分別是兩個敵對陣營的首領,卻又有著不解之緣。叛軍首領朗德納克是鎮壓叛亂的共和軍司令官郭萬的叔祖,而共和軍中公安委員會的特派員西穆爾丹卻曾經擔任過郭萬的家庭教師,一直把郭萬視為自己的“精神之子”。這樣巧妙的構思,不僅加強了矛盾衝突的戲劇性,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法國大革命的深度。
雨果通過驚心動魄的戲劇性場景描寫,細緻感人地刻畫出人物內心的衝突與升華,給人以強烈的情感衝擊和心靈震盪。雨果的小說善於運用對照原則,在人物衝突、性格衝突、觀念衝突、情節衝突中揭示人物心靈深處的真象,從而展現出人性的弱點與偉大。在《九三年》中,朗德納克、郭文、西穆爾登是三個對照中的人物,他們不同的價值觀念形成了對照,通過這種對照的衝突與映襯,雨果表達了他對人性的最終分析: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九三年》是雨果的寫作藝術達到爐火純青地步的產物。它的篇幅雖然不像雨果的其他幾部長篇小說那么大,但結構卻頗為完善,情節發展也很緊湊,很少有什麼枝蔓繁冗之處,充分顯示出雨果晚年圓熟的藝術技巧。小說的第一第二部為全書確定了背景和框架,給此後的故事發展作好鋪墊。在第三部中,三個主要人物終於在拉圖爾格的攻防戰中正面相遇,此後節奏明顯加快,情節起伏跌宕,一步步導向那撼動人心的結局。《九三年》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雨果一生思想的概括和總結,也是作者藝術形式最為完美成功的作品之一。
雨果的小說
《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這是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他在《笑面人》 (一八六九)的序中說過,他還要寫兩部續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前者始終沒有寫成,後者寫於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這時,雨果已經流亡歸來;他在拉芒什海峽的澤西島和蓋爾內西島度過了漫長的十九年,始終採取與倒行逆施的拿破崙三世誓不兩立的態度,直到第二帝國崩潰,他才凱鏇般返回巴黎。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對普法戰爭的悲慘戰禍和巴黎公社社員的浴血鬥爭,眼前的現實給他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再一次激發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他回顧歷史,法國大革命的史實給了他啟發,他有心通過大革命時期旺代地區保王黨人的叛亂,闡發自己的思想。這個念頭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經出現,如今寫作時機成熟了。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天主會給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敵人稱之為龐大得出奇的巨大計畫嗎?我年邁了一點,不能移動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聳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這樣一座大山!”顯而易見,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輕易不肯動筆,因而醞釀的時間有十多年之久。雨果在寫作之前閱讀了儘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歷史背景的工作。關於大革命時期布列塔尼地區的叛亂,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憶錄》(一八0三-一八0七),杜什曼·德斯波的《關於朱安黨叛亂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從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語、服裝和生活方式的細節,還有各個事件。關於救國委員會的活動,他參閱了加拉、戈伊埃、蘭蓋、賽納爾等人的回憶錄。關於國民公會,他參閱了《日通報》彙編。他研讀了米什萊、路易·布朗、梯也爾、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國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條書籤,上寫:“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關鍵局勢。”這一天成為小說的出發點。他還使用過拉馬丁的《吉倫特黨史》,阿梅爾的《羅伯斯比爾史》和他的朋友克拉爾蒂著述的《最後幾個山嶽黨人史實》,另外,賽巴斯蒂安·梅爾西埃的《新巴黎》給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國生活和堡壘建築的寶貴材料。雨果並沒有讓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駕馭這些材料,創作出一部生動而緊張的歷史小說。應該說,雨果對法國大革命並不陌生,他生於一八0二年,父親是拿破崙手下的一個將軍,而母親持有保王黨觀點。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經歷了大革命的變遷。對於這場人類歷史上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過這時雨果早已改變了早年的保王派觀點,他從四十年代末開始已成為共和派,他是以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這場革命的。雨果不想寫作一部通俗的歷史小說,他不滿足於描寫法國大革命的一般進程,而是想總結出某些歷史經驗。《九三年》這部歷史小說的切入角度是獨具慧眼的。雨果選取了大革命鬥爭最激烈的年代作為小說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處於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賓派取代了吉倫特黨,登上了歷史舞台;面對著得到國外反法聯盟支持的保王黨發動的叛亂,以及蠢蠢欲動的各種敵人,雅各賓黨實行革命的專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鎮壓敢於反抗的敵對分子;派出共和軍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亂,終於使共和國轉危為安,鞏固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在小說中指出:“九三年是歐洲對法蘭西的戰爭,又是法蘭西對巴黎的戰爭。革命怎樣呢?那是法蘭西戰勝歐洲,巴黎戰勝法蘭西。這就是九三年這個恐怖的時刻之所以偉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紀的其餘時刻更偉大。”他又說:“九三年是一個緊張的年頭。風暴在這時期達到了最猛烈最壯觀的程度。”以這一年發生的事件來描寫大革命,確實能充分反映人類歷史中最徹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
雨果尊重歷史,如實地展現了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殘酷性,描寫出這場鬥爭激烈而壯偉的場面。在小說中,保王黨叛軍平均每天槍殺三十個藍軍,縱火焚燒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燒死在家裡。他們的領袖提出“殺掉,燒掉,絕不饒恕”。保王主義在一些落後地區,如布列塔尼擁有廣泛的基礎,農民盲目地跟著領主走。他們愚昧無知,例如農婦米歇爾·弗萊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國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為貴族賣命,斷送了性命;乞丐泰爾馬什明知政府懸賞六萬法郎,捉拿叛軍首領朗特納克,卻把他隱藏起來,幫助他逃走。農民的落後是貴族發動叛亂的基礎,小說真實地反映了這種社會狀況。面對貴族殘忍的燒殺,共和軍以牙還牙;絕不寬大敵人。在雅各賓派內部,三巨頭--羅伯斯比爾、丹東、馬拉,雖然政見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採取強有力的手段。他們選中主張“恐怖必須用恐怖來還擊”的西穆爾丹為特派代表,頒布用極刑來對待放走敵人的嚴厲法令。因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來對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確評價了雅各賓黨專政時期實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國民公會喻為釀酒桶,桶里“雖然沸騰著恐怖,也醞釀著進步”。國民公會宣布了信仰自由,認為貧窮應受尊敬,殘疾應受尊敬,母親和兒童也應受尊敬;盲人和聾啞人成為受國家監護的人;譴責販賣黑奴的罪惡行為;廢除了奴隸制度;頒布了義務教育制;創立了工藝陳列館和博物院;統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創辦了電報、老年人救濟院、醫院;創建了氣象局、研究院。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燦爛的思想光芒,造福於人民。大革命所進行的乃是啟蒙思想家的理想,是以先進的資產階級文明代替愚昧落後的封建體制。至今,上述各項措施繼續起著良好作用,並普及到世界各國。
對法國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階級生死搏鬥的正確描寫,是這部小說的基本價值所在。雨果捍衛法國大革命,包括雅各賓派一系列正確政策的立場,鮮明地表現了他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現出真知灼見。《九三年》以雄渾的筆觸真實地再現了十八世紀末的法國歷史面貌,是描繪法國大革命的一部史詩。不過,對於雅各賓派的所作所為,雨果並沒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賓派為什麼會失敗?人們有各種各樣的看法,雨果也進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來,儘管一方面是刀光劍影,以暴力對付暴力,但另一方面,應有仁慈,要以人道對人道或非人道。他認為,雅各賓派濫殺無辜,沒有實行人道主義政策,以致垮台。這一沉思表現在小說結尾。人們歷來對這個結尾爭論不休,難以得出結論,小說的魅力卻很大程度來自於此。從藝術上看,《九三年》的結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時寫得扣人心弦。叛軍首領、布列塔尼親王朗特納克被圍困在圖爾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為人質的三個小孩來交換,請藍軍司令官戈萬放了他,戈萬斷然拒絕。可是朗特納克得到別人幫助,從地道逃了出來。突然他聽到三個孩子的母親痛苦的喊聲:三個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沒了。朗特納克毅然折回來,冒著危險,救出三個小孩,他自己則落到共和軍手裡。戈萬震驚於朗特納克捨己救人的人道主義精神,思想激烈鬥爭,認為應以人道對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納克。特派代表西穆爾丹是戈萬小時的老師,他不顧廣大共和軍戰士的哀求,堅決執行“任何軍事領袖如果放走一名捕獲的叛軍便要處以死刑”的法令,鐵面無情地主張送戈萬上斷頭台。就在戈萬人頭落地的一剎那,他也開槍自殺。
西穆爾丹、戈萬和朗特納克是小說中的三個主要人物,他們之間的糾葛從政治觀點的敵對,轉化而為是否實施人道主義的衝突。雨果認為:“慈悲心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殘餘,一切人心裡都有,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納克的情況就是這樣,“那個母親的喊聲喚醒他內心的過時的慈悲心,”“他已經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來。在造成罪行之後,他又自動破壞了那罪行。”對此,戈萬在沉思時發現,“一個英雄從這個惡魔身上跳了出來”,朗特納克不再是殺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惡魔,這個拿著屠刀的人變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贖回了種種野蠻行為,救了自己的靈魂,變成無罪的人。
小說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像異峰突起,使矛盾達到白熱化。如何處置與評價朗特納克和戈萬的行為,構成了人物之間的衝突,也引起讀者不同的看法。毫無疑義,與其說是戈萬在沉思,不如說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納克是個一般的保王黨人或一般的叛軍指揮官,他捨身去救三個處在大火包圍中的小孩,那么這還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費解的是,朗特納克是個異常冷酷的人,他出現時曾經毫不憐憫地槍殺藍軍中隨軍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個尚不懂事的孩子,作為向共和軍要挾的人質,也正是他要放火燒死他們,準備同歸於盡。在此時的朗特納克心裡,或者說作者心裡,人道主義已經超越了某些關於階級、革命、社會等宏大敘事,而只是作為一種人皆有之的對不懂事的孩子的憐憫的表達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雨果是把人道主義放到一個非常高的位置上的。有某些人認為這裡情節突兀,不符合常理。但事實上,這只是不符合關於革命和暴力的常理;實際上,如果不把朗特納剋死死地按在“封建者”“革命的反對者”這一角色下的話,這種情節不但不突兀,而且是非常感人,也很好地體現了作者對人道主義的態度的。
至於戈萬,他的行動倒是描寫得有根有據的。雨果早有交代,說他在打仗時很堅強,可是過後很軟弱;他待人慈悲為懷,寬恕敵人,保護修女,營救貴族的妻女,釋放俘虜,給教士自由。他的寬大不是無原則的,他曾對西穆爾丹說,他赦免了戰敗後被俘獲的三百個農民,因為這些農民是無知的,但他不會赦免朗特納克,因為朗特納克罪大惡極,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罷。法蘭西才是他的兄長,而朗特納克是祖國的叛徒。他和朗特納克誓不兩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與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稱。例如,他認為路易十六是一隻被投到獅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衛是很自然的,雖然他一有可能便會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斷頭台來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護人頭。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在打仗的時候,我們必須做我們的敵人的敵人,勝利以後,我們就要做他們的兄弟。”這些話為他後來的行動按下了伏筆,雖然是雨果的觀點,但與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萬的行動同雨果對雅各賓派的看法有關,雨果對雅各賓黨的恐怖政治是頗有微詞的。在他的筆下,雅各賓黨三巨頭狂熱多於理智,只知鎮壓,不懂仁政,語言充滿火藥味,渾身散發出平民的粗俗氣息。他們所執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條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時也包含著弊病。戈萬認為對舊世界是要開刀的,然而外科醫生需要冷靜,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共和國不需要一個“怕人的外表”。從這種觀點出發,戈萬放走朗特納克是順理成章的。應該說,雨果在小說里發表的見解既非全對,亦非全錯。對於保王黨人的武裝叛亂和殘忍屠殺平民的行為,革命政權只有以眼還眼,這樣才能保存自身。但也無可諱言,雅各賓黨矯枉過正,存在濫殺現象,這就是為什麼雅各賓黨的專政維持不了多久,連羅伯斯比爾也上了斷頭台的原因。據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考證,一七九四年,當局嫌斷頭機行刑太慢,便輔之以炮轟、集體槍斃、沉船,一次就處死幾百人。因此,雨果提出勝利後應實施寬大政策,是針對革命政權的極端政策而發的,具有合理、正確的因素。但戈萬之所以放走朗特納克,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敵人也能實行人道主義,共和軍就不能實行人道主義嗎?這裡,雨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的觀點集中表現為這句話:“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雨果將革命和人道主義割裂開來是錯誤的。革命與人道主義可以統一,而且應該統一起來。就拿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這是對罪惡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會制度;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比起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關係。貴族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要前進一大步。然而,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終勝利的緊急關頭,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寬大無邊的、絕對的人道主義,否則就是對人民實行不人道。以朗特納克來說,就算他果真救出三個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對於革命的一方來說,完全可以根據他的情況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決,而不一定非要處以極刑。當然,共和軍不會這樣處理。但是,放走了他,後果會怎樣呢?他必然與革命政府為敵,再次糾集叛軍,攻打共和軍,屠殺無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從效果來說,戈萬放走朗特納克的行動,對人民來說,是不符合人道原則的。以上分析說明,無論雅各賓黨,還是雨果本人,都未能處理好革命與人道的關係問題。西穆爾丹是作為戈萬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雖然他也是一個革命者。小說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儘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愛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個病人喉部的膿瘡,可他決“不會給國王幹這件事”。他認識到革命的敵人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沒有人看見他流過眼淚,他自認為不會犯錯誤,別人無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雖然崇高,“可是這種崇高和人是隔絕的,是在懸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親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圍被懸崖峭壁包圍著。”他忠於雅各賓黨的信條和各項恐怖政策,他向委任於他的國民公會保證:“假如那委託給我的共和黨領袖走錯了一步,我也要判處他死刑。”他屢次警告戈萬:“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仁慈可能成為賣國的一種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實。在判處戈萬死刑之後,他再一次同戈萬交鋒。戈萬縱橫捭闔,暢談他的理想,西穆爾丹無言以對,敗退下來。他承認戈萬的話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觀點,內心處於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著像箭一樣的盲目的準確性,只對準目標一直飛去。在革命中沒有什麼比直線更可怕的了。西穆爾丹一往直前,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親手處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兒子”和學生、他的戰友,最後在痛苦與惶惑中開槍自盡。通過他的悲劇,雨果批判了只講暴力,不講人道,只知盲目執行,不會靈活處置的革命者。西穆爾丹是有代表意義的、相當真實的一個形象。
作為浪漫派的領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雨果的一個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將無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繪得如同有生命的物體一樣神奇、動人心魄、令人驚嘆。小說開篇對戰艦上大炮的描寫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艘名為巨劍號的軍艦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彈的大炮從炮座上滑脫了,它變成了一頭怪物,它在艦上滾來滾去,鏇轉,衝撞,擊破,殺害,殲滅,又像握城錘在任性地撞擊城牆:“這是物質獲得了自由,也可以說這是永恆的奴隸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一切仿佛是隱藏在我們所謂無生命的物體裡的那種惡性突然爆發了出來;它那樣子像是發了脾氣,正在進行一種古怪的神秘的報復;再也沒有比這種無生物的憤怒更無情的了。這個瘋狂的龐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靈巧,斧子的堅硬,波浪的突然,閃電的迅速,墳墓的痴聾。它重一萬磅,卻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彈跳起來。……暴風可以停止,颱風會吹過去,斷掉的桅可以換一根,一個漏洞可以堵上,火災可以撲滅;可是對這隻龐大的青銅獸怎么辦呢?”這門大炮完全解除了軍艦的戰鬥力。雨果豐富的想像力將這個場面描繪得令人嘆為觀止。就是在這樣一個悲壯的場面中,朗特納克出現了,顯出他的嚴厲、冷峻和剛毅。這個陰慘慘的、色彩神秘的開場給小說定下了悲劇的調子。雨果就以這樣的筆法,營造出殘酷的、命運捉摸不定的氣氛,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認為這種浪漫手法同樣能達到真實,他在小說中說:‘歷史有真實性,傳奇也有真實性。傳奇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傳奇的真實是在虛構中去反映現實。”浪漫手法與寫實手法是殊途同歸。
眾所周知,雨果是運用對照手法的大師。他在《克倫威爾·序》中曾經指出:“醜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後,美與惡共存,光明與黑暗相伴。”這條準則始終指導著雨果的創作。《九三
 《九三年》
《九三年》雨果的小說技巧在《九三年》中達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說情節的進展異常緊湊,看不到多少閒筆和題外話,不像《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那樣,常常出現大段的議論或枝蔓的情節。作者的議論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是更高明的手法。從結構上說,小說環環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個小孩的遭遇為核心,以三個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鋒為衝突,寫得緊張而動人心弦。這部小說雖然篇幅不大,卻堪與卷帙浩繁的歷史小說相媲美,成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書摘
書摘:
在茂林深處有一片小小的林中空地,它呈圓形,是燒樹根的木炭窯留下的。在它邊上,有一個由樹枝形成的房間式洞穴,它半開著,像一個放床的凹室。那裡有一個女人,她坐在苔蘚上,正給一個嬰兒餵奶,膝頭上是另外兩個滿頭金髮的孩子,他們在熟睡。
這就是陷阱。
“你在這裡乾什麼?”女販喊道。
女人抬起頭。
女販又憤怒地說:
“你瘋了,呆在這裡!”
接著又說:
“你差一點就沒命了!”
她又對士兵們說:
“這是個女人。”
“當然,我們看見了!”一位士兵說。
女販繼續說:
“來林子裡送死!怎么幹這種蠢事!”
女人嚇壞了,驚惶失措,呆若水雞,像是在做夢。她看看四周,看著那些長槍、馬刀、刺刀和兇狠的面孔。
兩個孩子醒了,哭叫起來。
“我餓了。”一個孩子說。
“我害怕。”另一個孩子說。
最小的孩子繼續吃奶。
女販對她說:
“你最乖。”
母親嚇得說不出話來。
中士朝她喊道:
“你別怕,我們是紅色無檐帽營。”
女人全身顫抖不已。她瞧著中士,那是一張粗糙的臉,只看得見眉毛、髭鬚和火炭般的兩隻眼睛。
“就是從前的紅十字營。”女販說。
中士接著問道:
“你是誰,太太?”
女人驚恐萬狀地打量他。她瘦削、年輕、蒼白,衣衫襤褸,戴著布列塔尼農婦粗大的披肩風帽,脖子上繫著一床毛毯,像雌性動物一樣毫不在意地露出赤裸的乳房。她既沒有穿襪子也沒有穿鞋,兩隻腳在流血。
“這是個窮人。”中士說。
女販用粗聲粗氣、但仍不失女性溫柔的口吻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女人喃喃說了幾個字,幾乎聽不清;
“米歇爾·弗萊夏。”
這時,女販用粗大的手撫摸嬰兒的小腦袋,問道:
“小傢伙多大了?”
母親沒有聽懂。女販又說:
“我問你她多大了?”
“呵!”母親說,“一歲半。”
“夠大了,”女販說,“她不該再吃奶,應該斷奶了。我們給她喝湯。”
母親開始放心了。睡醒的那兩個孩子好奇甚於恐懼,正在欣賞羽飾。
“呵!”母親說,“他們真餓壞了。”
接著又說:
“我沒有奶了。”
“我們會給他們東西哈,”中士大聲說,“也給你。不過還有一件事。你是什麼政治觀點?”
女人瞧著中士,沒有回答。
“你聽見我的問題了嗎?”
女人結結巴巴地說:
“我很年輕就被送進修道院,但我給了婚,我不是修女。修女們教我說法語。村子被人放火燒了,我們急急忙忙逃了出來,我連鞋也來不及穿。”
“我是問你的政治觀點。”
“我不知道。”
中士又說:
“現在常有女奸細。女奸細是要槍斃的。來,你說吧,你不是波希米亞人吧。你的祖國在哪裡?”
她仍舊瞧著他,仿佛聽不懂。中土重複說:
“你的祖國在哪裡?”
“我不知道。”她說。
“怎么,你不知道哪裡是你的老家?”
“呵,老家,我知道。”
“那好,哪裡是你的老家?”
女人回答說:
“西斯夸尼亞莊園,在阿澤教區。”
這回中士吃驚了。他沉思片刻,問道:
“你是說……”
“西斯夸尼亞。”
“那可不是祖國。”
“那是我老家。”
女人想了一下又說: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法國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那又怎樣呢?”
“這不是同一個地方。”
“可這是同一個祖國呀!”中士喊叫了起來。
女人又說:
“我從西斯夸尼亞來。”
“西斯夸尼亞就西斯夸尼亞吧。你家裡人是在那裡嗎?”
“是的。
“他們做什麼?”
“他們全死了。我沒有親人了。”
中士是個愛說話的人,又繼續審問:
“見鬼,你總有親戚吧,至少從前有。你是誰?說話呀。”
女人聽著,目瞪口呆,這句“至少從前有”不像是人的語言,而像是動物的吼叫。
女販感到自己應該介入了。她又撫摸吃奶的孩子的頭,用手拍拍另外兩個孩子的臉頰。
“吃奶的女孩叫什麼名字?”她問道,“這是個女孩吧。”
母親回答說:“若爾熱特。”
“老大呢?這淘氣鬼是男孩吧?”
“勒內-讓。”
“小的呢,他也是男孩吧,臉頰鼓鼓的。”
“胖阿蘭。”母親說。
“這些孩子多好哇,”女販說,“都已經像大人了。”
中士繼續問:
“你說吧,太太,你有家嗎?”
“有過。”
“在哪裡?”
“在阿澤。”
“你為什麼不呆在家裡?”
“家被燒掉了。”
“誰幹的?”
“不知道。是戰爭。”
“你從哪裡來?”
“從那裡。”
“你去哪裡?”
“不知道。”
“說正題吧,你是誰?”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誰?”
“我們是逃難的人。”
“你是哪一派?”
“不知道。”
“是藍黨還是白黨①?你和誰站在一起?”
--------
①藍黨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派,白黨是保皇派。
“和我的孩子們。”
沉默。女販說:
“我沒有生過孩子,沒有時間生孩子。”
中土又問道:
“那你的父母呢?聽我說,太太,告訴我們你父母是什麼人。我叫拉杜,我是中士,我是從謝爾什米迪街來的,我父母原先在那裡,我可以談我的父母。你談談你的父母吧。他們原先是什麼人?”
“他們姓弗萊夏,就這些。”
“是呀,弗萊夏是弗萊夏,拉杜是拉杜,可總有個職業吧。你父母的職業是什麼?原先是乾什麼的?現在乾什麼?你的這些弗萊夏,他們弗萊夏些什麼呢?”
“他們種地。我父親是殘廢,不能做工。他挨過老爺--他的老爺,我們的老爺--的棍子,這還算老爺開恩,因為父親偷了一隻兔子,這夠死罪,老爺發善心,讓手下人只打了我父親一百根,從那時就落下了殘疾。”
“還有呢?”
“我爺爺是胡格諾派,被本堂神甫送去服苦役。那時我很小。”(第一章)
維克多·雨果作品
|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2.26~1885.5.22),法國浪漫主義作家,人道主義的代表人物,19世紀前期積極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代表作家,法國文學史上卓越的資產階級民主作家,被人們稱為“法蘭西的莎士比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