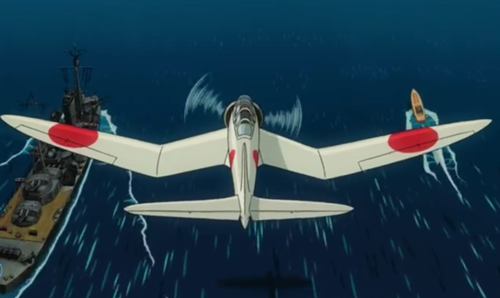陳寅恪先生在談論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時提出曹魏統治者出身為“寒族”,與此相對應的即為“豪族”。不過,陳寅恪先生提出的“豪族”,著重討論的是信仰儒家的大士族。
在我個人看來,東漢末年“豪族”的範圍很廣,除了以儒家思想為信條的主流“豪族”,還存在幾類非主流“豪族”。而“豪族”之“豪”,亦非僅僅體現在政治、文化上,還體現在人力和財力上。
東漢末年豪族的構成
1
東漢末年的豪族大抵有以下幾類:
第一是擁有政治聲望的大士族,這也是東漢末年豪族的主流。典型的有:弘農楊氏、汝南袁氏。
《三國志 袁紹傳》載:“(袁紹)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可見,這一類豪族世代為官,在政治上掌握了重要資源。此外,他們也都服膺儒教,在文化上擁有重要地位,以此形成了“樹恩四世,門世故吏篃於天下”的政治勢力。
 四世三公的袁紹
四世三公的袁紹同時,這種門生故吏網路在諸侯紛爭時也能夠起到強大的政治壓力,《三國志 滿寵傳》載:“(官渡之戰)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大士族在外戚和宦官兩敗俱傷之後,逐步開始占據政治的主導權、掌握文化的話語權,成為東漢末年重要的政治力量。
第二是依靠強大人力的大宗族。與大士族相比,大宗族的範圍不如大士族廣,往往只是限於某個地區。
此外,大宗族普遍為地方豪族,他們多是憑藉地緣血緣(如李典:“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等)或地方豪俠之氣聚集(如李通:“以俠聞於江、汝之間…眾多歸之”),這類豪族在政治權勢和文化水平上不如大士族。
與大士族相同的是,大宗族也擁有大量的人力資源;然而與大士族門生故吏的政治網路不同,大宗族的人力資源優勢在於能夠直接投入使用,形成強大的人力武裝。
如《三國志 許褚傳》載:“(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這些武裝不僅能夠自衛,也能夠起到對征伐起到幫助作用,如《三國志 李典傳》載:“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谷帛供軍”、“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原徙詣魏郡”,這樣的人力資源優勢是大士族所不具有的。
 畫家劉曉陸繪製的許褚
畫家劉曉陸繪製的許褚第三是憑藉大量財富的大商人。
與大士族的政治資本、大宗族的人力資源不同,大商人成為豪族憑藉的是財富的積累,但是在中國古代重本抑末的環境下,單純靠積累物質財富是難以維繫商人永久安定的,尤其是在東漢末年天下板蕩的時代,大商人的財產乃至生命安全都時刻受到威脅。於此,大商人會通過豢養僮客、組織武裝以保障自身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如《三國志 麋竺傳》除了記載:“(麋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還提到了“自竺至照(麋竺孫),皆便弓馬,善射御雲”,點明商人出身的麋家也有一定的武備。
 東海巨富糜竺
東海巨富糜竺從上述的歸納可以看出,東漢末年的豪族大體能夠分為大士族、大宗族和大商人,而他們之所以成為豪族,仰仗也各不相同。大士族擁有的是政治權勢和文化地位,大宗族依靠的是可直接使用的人力資源,大商人憑藉的是巨額財富以及財富所帶來的附屬品。
從時代的背景看,上這三種豪族又能夠劃分為兩種,即主流豪族和非主流豪族。
由於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又在血緣政治、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下,大士族在豪族中擁有絕對優勢;而大宗族多是地方豪帥,在政治權勢、文化水準上遠不如大士族;大商人沒有大宗族血緣紐帶,又需要通過花費錢財來組織自己的武備,其實力又不如大宗族。
因此,雖然東漢末年出現了多元的豪族構成,但無論是地位還是主流程度,都呈現大士族>大宗族>大商人的局面。
袁紹、曹操、劉備早期依靠的豪族
2
東漢末年,各路諸侯的創業基本都需要依靠豪族的支持,豪族能夠給諸侯們帶來政治上的聲望、人力上的幫助以及財力上的支援。我們亦可通過觀察幾位諸侯的創業經歷,來體會豪族在東漢末年政治局勢以及戰爭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看袁紹。
袁紹的創業具有先天優勢,因為其本身屬於主流豪族,即擁有政治聲望的大士族。故而,袁紹在創業初期順風順水,不僅因為出身名門而當上了討伐董卓盟軍的盟主;在接收富饒的冀州時,原冀州牧韓馥亦因“袁氏故吏”身份對袁紹心生畏懼,故而拱手獻出冀州。
 被袁紹威望壓垮的韓馥
被袁紹威望壓垮的韓馥雖然袁紹具有先天優勢,但是袁紹最終沒有取得成功,這說明了大士族的優勢失靈。大士族的優勢為何會失靈,在我看來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是大士族自身的問題。
從政治上看,大士族擁有政治特權,隨著勢力擴張,往往容易濫用特權、驕縱枉法,從而失去人心。
從文化上看,大士族受到的儒家教義限制多,往往束縛住了手腳。史載:袁紹“繁禮多儀”、“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這並非是袁紹個人的問題,推而廣之,在儒家一系列繁文縟節的規制下,大士族都容易陷入實際作用不大的框框條條,從而降低做事的效率。
第二則是東漢末年特殊的社會背景。
在東漢末年天下動盪的時代,伴隨著帶有宗教色彩的黃巾起義和帶有軍人政府性質的董卓之亂,天下人對正統的儒家統治思想產生了懷疑,也由是大士族的政治權勢和文化地位也隨之受到了動搖,再加上前述所說大士族的自身問題暴露,使得大士族豪族的優勢趨於失靈。
但是這種失靈只是一時的,在時局恢復穩定後,大士族的優勢又容易重新突顯。
其次是曹操。
曹操雖然在政治出身上弱於袁紹,但曹操亦非絕對的寒族。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在我看來,曹操至少亦屬於豪族中的大宗族。
從另一個方面看,譙沛武人集團的構成也符合大宗族豪族的概念,諸如曹氏、夏侯氏宗族中,曹仁“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鏇淮、泗之間…”,曹洪曾有“家兵千餘人”,這同先前所述的李典、許褚、李通等家族十分類似。
 譙沛武人集團的代表曹仁
譙沛武人集團的代表曹仁正因為如此,曹操深知在東漢末年天下板蕩、重新洗牌的時代背景下人力的重要性,《三國志 武帝紀》記載,曹操曾在和袁紹的溝通中指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的主張。
而事實也證明了,在戰亂年代,人力的作用非常大,其不僅能夠為農業生產和軍隊建設補充人員,更能夠提供智力支持。曹操連續頒布三道求賢令,也充分證實了人才資源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雖然重視人力作用,但也並非絕對排斥大士族擁有的政治權勢和文化地位,其積極和潁川士族的合作能夠證明這一點。
但是在曹魏後期,時局趨於穩定,大士族政治優勢的作用反超人力的作用,致使曹操和潁川士族之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最後談劉備。
劉備早年和商人頗有淵源,《三國志 先主傳》載:“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鏇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
爾後,劉備執掌徐州,後值敗績,幾乎全軍覆沒,此時徐州大商人麋竺“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賴此復振”。可見劉備創業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依仗大商人的支柱。
但是大商人的財貨資助往往只能起到一時性的作用,相對於強大的政治權勢和血濃於水的宗族關係,財貨資助雖然能夠起到臨時救濟作用,但很難穩定,故而劉備早年創業四處奔波流浪。
由此可見,東漢末年諸侯的創業,基本上都依靠了各類的豪族,只是最後的結果各有不同,而從諸侯創業的結果我們亦能夠看出東漢末年豪族演變的趨勢。
豪族的演變趨勢
3
在我看來,豪族這一概念並沒有非常界限分明,豪族往往兼而有政治權勢、大量人力和巨額財富,是一個集合體。但是在東漢末年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區別於傳統的主流豪強的非主流豪族的出現以及其積極作用卻不容忽視。
東漢末年,天下動盪,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地方宗族勢力極易抱團取暖,形成自衛武裝,如兗州山陽李典家族“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許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他們糾契約族,形成自己的武裝以保衛家園,同時在與入主當地的諸侯產生共鳴時,亦逐步成為諸侯的武裝力量,如李典家族、李通家族、臧霸勢力。
而大商人除了保障自身安全,往往也會主動尋求政治投資,在東漢之前,大商人呂不韋和雁門馬邑豪族聶壹都是例證,當然此二人的政治投機意味要大於保障自身安全。
不過,在東漢末年混亂的環境下,身處四戰之地徐州的糜竺出於商人的敏銳,也必須尋找合適的人選進行政治投資,以確保整個家族的安全。而最後的事實證明,糜竺的投資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由此可見,在東漢亂世的背景下,非主流豪強的大宗族和大商人都缺乏安全感,因此他們會主動地尋求和政治勢力(諸侯)的合作,而缺乏人力財力的政治(諸侯)勢力亦樂於接受他們的合作,因此產生和壯大了曹操、劉備這樣的勢力。
 豪族催生了三國
豪族催生了三國而傳統的主流豪強自身先天擁有政治勢力和文化地位,對於時代的變化沒有非主流豪強那樣敏感。故而,從主流豪族與非主流豪族各自的特點上看:
在整體局勢動盪和混亂時,主流豪族的話語權出現一時性失靈,非主流豪族的異軍突起;在整體局勢趨於穩定和平衡時,非主流豪族漸漸趨於平淡乃至被主流豪族吸納。
但是,不容否認的是,曹操、劉備勢力依靠非主流豪族建立起的政權與以往的政權形式不同,延緩了大士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壟斷,激發了其他社會力量的積極作用,有其積極的一面。
三國志 陳寅恪 大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