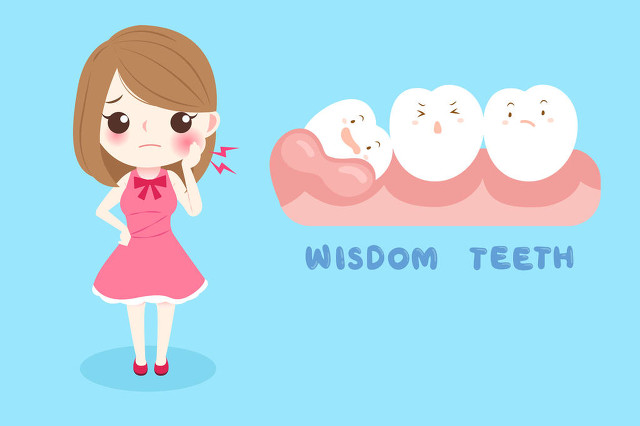明清之際,基督教耶穌會士在華傳教200年,在傳教的同時,也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帶來了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和碰撞。中國耶穌會傳教區的創始人利瑪竇推行“中國文化適應政策”,客觀上促進了中西交融,成為後來傳教士的模範。本文將就耶穌會傳教士來華的背景、利瑪竇在華傳教的策略以及初期來華耶穌會傳教士的評價這三方面作一個簡單的探討。

一、耶穌會傳教士來華的背景
基督教傳入中國,前後有三次。第一次在唐代,中國人稱之為景教;第二次在元代,統稱為也里可溫教;第三次在明末,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這裡要說明一點,我們必須將明清之際的傳教士與19世紀鴉片戰爭後帶有殖民色彩的傳教士區別開來。本文討論的是明清之際即初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在基督教三次來華中,前兩次成效不大,“都沒有傳來什麼思想。”相比之下,明清之際基督教再次來華,具有更深刻的影響。
第三次基督教來華,從16世紀末開始到18世紀末,前後約延續了兩個世紀。明末清初的二百餘年,無論從中國的角度出發,還是從世界的眼光來看,這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分析耶穌會傳教士來華的背景,有利於加深對明清耶穌會士在華傳教活動的理解。
1. 地理大發現與海外殖民擴張的刺激
15世紀末16世紀初,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麥哲倫實現了環球航行。隨著新航路的開闢,歐洲進入了大航海時代,歐洲各國紛紛走向了海外殖民擴張,爭取海外廣闊的地域和豐富的資源。歐洲殖民列強之間爭奪的觸角所及非洲、美洲還有亞洲。
為了爭奪更多的海外殖民地和開闢更廣闊的海外市場,歐洲殖民列強將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列入殖民擴張的計畫。明代末年,耶穌會士初期來華,羅明堅、利瑪竇首先打開中國大門。為此,“某些很有眼光的歐洲君主尤其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很明智地把耶穌會士們納入了自己建立和發展資外殖民地的軌道,使耶穌會士們的傳教活動成為其執行殖民擴張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們一方面實行‘炮艦政策’,直接出兵掠奪當時尚處於‘落後’狀態的國家和人民;同時又利用攻心術,在思想和文化方面進行滲透,‘傳教’和‘福音化’是他們得心應手的策略。”
在大海航時代,新航路的開闢正好與天主教的振興同時到來,這極大調動了傳教士們的熱情。由於海外殖民擴張與尋找更廣闊傳教基地的需要,基督教對外傳教的海外派應運而生。當然,這僅為傳教士來華的其中一個方面的背景。
2. 宗教改革衝擊下天主教的危機自救
16世紀至17世紀,歐洲發生了宗教改革。改革將矛頭對準了羅馬教會的神權統治,要求改革建立適應時代發展的“民族教會”或者“廉價教會”。歐洲各國的宗教改革,使羅馬天主教會在歐洲的社會、政治地位受到嚴重的威脅。
面對這樣的背景,“羅馬天主教教會為了重新占領失去的陣地,進而打擊新教勢力,發動了一系列包括自身整頓在內的反宗教改革措施,在這種背景下,耶穌會應運而生。”在1534年,耶穌會由西班牙人依納爵•羅伊納創立並於1540年由教皇保羅三世批准。此後,耶穌會派傳教士到海外進行傳教活動,尋求新的天主教傳教區,其中東方和中國便成了傳教布道的主要對象。

3. 明末清初的中國社會提供來華契機
在16至17世紀的明清朝代更替之際,中國社會處於動盪、大變革之中。中國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中國的四大發明一直是中國的驕傲。但是走到明清時期的中國,已經在走向了下坡路。與此同時,西歐一些國家開始建立起了資本主義制度,近代自然科學技術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方面迅速發展。而在當時的中國,宋明理學禁錮著人們的思想,知識分子脫離實際,學風空疏,中國人卻還沉浸在“天朝夢國”中獨尊自大。
“但自十六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明朝,政治漸趨黑暗,階級矛盾加劇,戰爭頻仍,加上清朝的統一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直到十七世紀七十年代才進入恢復時期。由於清朝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致使中國仍然處於緩慢發展的封建社會生產狀態, 科學技術因此遠遠落後於西方, 社會制度也不如西方先進。”
由於中國的落伍,明末掀起了“西學東漸”,一些開明君主和愛國上層士大夫對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技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藉此富國強兵。明末的中國社會給耶穌會提供了來華傳教的有利契機。
二、利瑪竇在華傳教的策略
最先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是聖方濟名•沙勿略。但是他未能進入中國大陸,終死於廣東上川島。真正為耶穌會在中國傳教奠定基礎的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利瑪竇於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傳教。從利瑪竇開始,隨著西方傳教士的不斷東來,在中國逐漸出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高潮。利瑪竇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順利傳教,是因為他對中國情況有充分把握,並且“入鄉隨俗”,採取了“中國文化適應政策”,從各方面取得信任,減少傳教的阻力。

1. 走“親近路線”,順應中國風俗習慣
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傳教,面對的是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淵博的思想傳統的東方大國,畢竟與非洲、美洲有相當大的區別。要向在中國順利傳教,就必須了解清中國情況,以減少中國人對傳教士和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利瑪竇神父是勇敢的嘗試者和改革者,他首先採取的是適應中國風俗的作法。
兩個不同文明的國家,首先的障礙就是語言不通。語言在溝通、理解文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此,利瑪竇一到中國,便刻苦學習漢語,邁開傳教過程中溝通的第一步。“1582年,利瑪竇在澳門學習‘聖萬迪諾新信徒學校’學習中文。1583年,來到肇慶後,利瑪竇緘口不談宗教,而是更加刻苦等學習漢語。”除了謹慎踏實地學習語言外,他們還適應了中國當地的風俗習慣,公開穿戴儒生們的服裝,按照中國當時文人的典型裝扮來打扮自己。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凡事講禮節。要想贏得更多人的認可和信任,他們也注意起中國禮節,並在潛移默化中融化在自己的行為當中。
利瑪竇“能謙虛謹慎地學漢語,恭敬地穿儒服,努力地接受和適應中國文化,結交中國朋友,首先使自己中國化。這樣,利瑪竇在中國的言行舉止就成了後來之耶穌會士們仿效的榜樣。”
2.走“思想路線”,調和天主教教義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
僅在外在上適應中國風俗還是遠遠不夠的。對於耶穌會士來講,下一步的任務便是如何也讓天主教教義為中國人接受。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一直以來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在中國人腦海中和行為中根深蒂固。利瑪竇第二步即“引經據典地將天主教的宗教教義與儒家理論進行比附、調和,試圖說明二者之間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
利瑪竇研讀儒家哲學思想和中國傳統倫理觀,“首先把基督教說成是一種近似儒教的倫理和政治教理,與人類的理智相吻合。”利瑪竇以基督教的觀點來解釋儒學,將基督教的上帝類比於儒學的天、天命,使基督教本土化,便於中國人接受。
以利瑪竇為例,其他傳教士也存在這種現象。“在16世紀初葉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人曾認為,在送子娘娘觀音的身上發現了與懷抱聖嬰的聖母馬利亞的之相似性。”耶穌會士在華傳教也找到了這種相似。在沿海地區,它與對女神媽祖的信仰結合在一起,又被稱為“天妃”、“天后”。
耶穌會士採取這種相對寬容且明智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迎合中國人的心理特徵,這不失為一種較為大膽成功的嘗試,也為以後較長一段時間內在中國順利傳教的前提。
3.走“上層路線”,側重結實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期間,逐漸了解了中國國情,決定要走上層路線,結交中國皇帝、士大夫和社會名流等社會上層人士。
其一,在地大物博、唯我獨尊的中國,為了獲得在中國傳教的合法地位,必須取得中國朝廷和士大夫的信任。得到了他們的信任,更有利於減少在華傳教的阻力和基督教的進一步傳播。每至一地,利瑪竇都要拜訪和結識當地官員和名流。利瑪竇與當時一些出名的上層人士交往甚密,在傳播中西文化時也成功地將他們歸化為天主教的信徒。“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都直接受利瑪竇的宣教和學術上的誘導,先後受禮。”
其二,入華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熱衷於“上層路線”,也是由他們的社會出身所決定的。據耿昇先生統計分析,“16-18世紀的入華耶穌會士們,基本上都是屬於中上層社會出身的人。”由社會出身出發,走“上層路線”,在中國採取“文化適應政策”,也相對合理的。

4.走“科學路線”,宣揚西方先進科學知識
16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鄙視番夷專制國家,西方外來的意識形態要進來實屬不易。利瑪竇意識到了這一點,認為“不可能直截了當的改變這個國家的信仰,中國人是如此的深信他們比蠻夷優越,以至首先應當使他們改變輕視歐洲人的態度。”因此,為了改變中國人的態度,利瑪竇首先用西方先進科學成就來引起中國士大夫的關注和崇敬,以便於進一步的傳教活動。
上流社會對他們介紹進中國的歐洲奇物比如三菱鏡、地球儀、世界地圖、鐘錶等頗感興趣,逐漸從形式上到文化認同上接納了這些傳教士。從器物的傳進到譯著的傳播,早期耶穌會士以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為手段,達到了推行天主教的目的。這逐漸形成了一種互為表里的傳教策略。
三、初期來華耶穌會傳教士的評價
對於耶穌會傳教士在華傳教,學術界各方的褒貶各異。2007年是基督新教入華200周年,林中澤教授就基督教入華二百年的總體評價作了一個整體巨觀的概括。“就國內的情況而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是貶多於褒,整個八十年代是褒貶並行,而從九十年代開始則是褒多於貶。”在筆者看來,無論是褒的一方還是貶的一方,皆難以做到較為全面地評價來華傳教士,畢竟耶穌會傳教士功過兼具。本文只論述初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筆者愚見耶穌會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有得有失,有功也有過,但是他們值得肯定的地方還是需要我們肯定的。
首先是褒揚。其一,不可否認的是耶穌會士向中國輸入了近代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西方體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動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與更新的作用。另外,“西學東漸”至少開拓了國人的眼光,使他們從“天朝上國”的盲尊自大開始感受到了西方的先進科技成果。中國人對西方世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開始學會用“世界”的眼光來看待事物。即使這些變化在上層人物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也沒能夠引起整箇中國社會的變動。但是這一步的關鍵,應該值得肯定。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如利瑪竇,長期生活在中國,並與進步人士有密切交流,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對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其二,耶穌會士也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比較系統全面地介紹到西方去,甚至掀起了一場“中國熱”的風潮。且不論其目的,這些舉動本身也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碰撞,這是值得褒揚的一點。
其次是貶斥。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是與西方殖民主義侵略聯繫在一起。的確,從傳教士來華背景來看,為了爭奪更多的海外殖民地和開闢更廣闊的海外市場,歐洲殖民列強將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列入殖民擴張的計畫。這是傳教士令人詬病的一點。但是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將明清之際的傳教士與19世紀鴉片戰爭後的傳教士區別開來。本文所討論的初期入華的傳教士也不乏帶有殖民色彩,但是利瑪竇時代的傳教士們,大都跟尋著利瑪竇走“中國文化適應政策”。他們淡化傳教目的,熱衷於中西文化交流互融,甚至可以說,有些人被中國文化所同化。
對於耶穌會士來華傳教活動的評價無論是貶是褒,筆者認為該褒之處則褒,該貶之處則貶,但是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至少有一點,即應該肯定耶穌會士在中西文化交流這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基督教 利瑪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