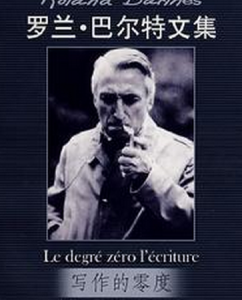概述
 羅蘭·巴特
羅蘭·巴特零度寫作,來源於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195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寫作的零度》。現在零度寫作方式多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摻雜任何個人的想法,完全是機械地陳述。這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是極其艱難的,將自己淪為寫字的機器,很是悲哀。2009年7月16日一位網友在百度“魔獸世界”貼吧中發了一則名為《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帖子,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篇只有標題的空帖獲得了回帖數已經達到31萬多,點擊率已達1084萬多。只因一句“媽媽喊你回家吃飯”而擴張成為無數網友的“群體性事件”,乃至變成一場盛大的網路狂歡。一句呼喊難道就喊出了千千萬萬寂寞的靈魂。
發現
零度寫作所指與能指既無必然聯繫,自然不能構成一種二元對立式的邏輯中心主義,能指並非所指的附屬物。相反,能指具有獨立的品質和自由權利,它可以完全游離於所指之外。羅蘭·巴特在十八、九世紀的文學中,欣喜地發現了能指的這種獨立性和自由性。在此之前,古典寫作中的語言符號承載的是工具性職能,這種工具性功能要求使語言符號成為一個過程,而不是目的,因而它必須是透明、直接的。語言符號存在的必要性來自於對意義、情感、思想的表達或轉譯。然而,語言的發展和作家對語言的創造性使用,使得語言符號這一形式變的“不透明”了,它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流通方式,“文學形式發展了一種獨立於其機制和其和諧性的第二性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種重量。”擺脫了附屬地位的語言和形式,獲得了自己的質地和分量,不再隱匿於意義之後,相反,它成為一個觀察和思考的對象,一個獨立的客體。
分析
語言、形式獨立性的發現,迫使人們不能繼續把字詞看成思想、內容的裝飾品。作為一個獨立客體——十九世紀以來,尤其是在今天的現代寫作中,字詞和語流走上前台,通過自身的組合和交流激發起審美的愉悅或相反的感覺——這正是形式的意義所在。形式自身具有引發某種情感,激勵某種思考的意義生產機制,字詞的不同搭配,甚至僅僅由於不同語境的因素,就會源源不斷地生產出豐富的意義來。單獨的或者連續的字詞,語流,它們構成一個封閉自足的整體,一套完整的記號。在這個基礎上才可以說,作家也可以憑藉字詞的這種運動,得以交流和表現某種情感、思想,對善的態度,對歷史的思考等等。
古典寫作同樣藉助於字詞和語流,然而它秉持這樣一種觀念:字詞和語流因某種外在於它的意義而存在,隨著意義的表達,字詞和語流在前進之中相互淹沒,最終只剩下一個意義的核心,而字詞和語流已經隱匿不見。暫且不論形式自身的意義生產機制,如果說字詞背後的確存在某種意義,那么首先也必須看到,正是字詞和語流的連續前進,意義、思想和情感才可以得以產生。“言語就是一種包含著更富精神性的構思的時間,在其中,‘思想’通過偶然出現的字詞而逐漸形成和確立。”語言行為造就了意義的果實,沒有語言行為,意義就無從產生。語言符號和某種意義的交遇,顯然不能不以語言符號的運動為前提。
獨立品質使形式不再負載某種情感或思想,不再是作家意圖的具體體現,不再是作家主體的一個輻射。獨立的字詞由於消除了一切相關的固定的聯繫,產生了“不確定的而可能存在的無數關係”。字詞的這種不確定性和潛存的無數可能性,在水平結構和垂直結構中隨處可見。在這個屬於自己的純粹世界裡,字詞與字詞互相關聯,語流與語流相互撞擊,“詩的字詞是一種沒有直接過去的行為,一種沒有四周環境的行為,它只提供了從一切與其有聯繫的根源處產生的濃密的反射陰影。”字詞即是一切,它既是一個獨立的客體,又是一個獨立的主體。
這顯然與古典寫作對語言的工具性的交流功能相牴觸,和被稱為“風格”的東西想牴觸:風格充滿了個人性的東西,致使字詞成為創作主體的奴隸。而字詞獨立品質的發現,致使創作主體不再擁有支配和調遣字詞的權力,後者通過其非連續性的組合,生產不確定意義的機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個語言自足封閉的狂歡世界的到來。在羅蘭·巴特看來,字詞即一種一般形式,是一個“類”。顯然,“類”包含了所有的個性,又否定了所有的個性。字詞由於蘊涵過多而充滿不確定的特徵:正是存在一切的可能性,使得每一種可能性都“不在場”,一種可能性與另一種可能性或者互相加強,或者互相衝突,而最終,它們因此又產生了新的更多的可能性。意義在字詞的連續中不斷產生,無法停留,即“既無意圖的預期,也無意圖的永久性”。所有的字詞均是“不及物”的,沒有意指,沒有方向。字詞的連續又是一個不斷否定的過程,充滿可能性,沒有趨向,處在運動當中卻在勢均力敵的對立因素中保持靜止狀態,中性、自足、飽和、客觀——這就是羅蘭·巴特一再強調的語言行為:零度的寫作。
特點
零度寫作這種中性的和“客觀的”寫作方式,與古典寫作所力圖表現的“文字的現實的客觀再現”截然不同。羅蘭·巴特推舉零度寫作,恰恰意在揭開古典寫作中處處標榜的“真實”和“自然”的神話,暴露古典寫作中“客觀”的虛偽性。古典語言在意義和字詞之間虛構了一種透明的確定的關係,通過字詞之間的連續性和直線性關聯,來隱喻現行法則的合理性,以及一種理性的生活態度的必要性。羅蘭·巴特發現,古典寫作中過去式的歷史寫作所表明的秩序,以及第三人稱協作所創設的旁觀者的安全地位,都力圖表明世界的確定性和客觀性,並因此表明,古典寫作正是現實世界的一個翻版,它創造了一個似真的審美世界。而字詞是這個世界表現自己的一種方式而已。
現代寫作恰恰相反。語言的獨立品質使得它們即使構成一個連續的語言結構,仍保有自身的獨立地位。如果說古典語言是線性的不可逆的,現代語言則是一些獨立、靜止的語言片段的臨時聚會,它們可能隨時分化,即使前後相依,也可能貌合神離,充滿矛盾和悖論。現代寫作中“一種語言自足體的爆發性摧毀了一切倫理意義”。現代語言的無序和混亂,以為種種偽裝,不可能提供給一個完整、穩固的世界的感受,藉此暗示了資產階級所標榜的秩序、公正、理性現實的虛假性。
零度寫作強調由字詞獨立品質所帶來的多種可能性和無趨向性。然而這種無趨向性越來越被狹隘地理解和使用了。在今天的文學現實中,人們不無隨意地用零度寫作來定義那些採用了外部聚焦,行為主義式的敘事規範,新寫實小時就時常不乏貶義地冠以零度寫作的頭銜,還時常把九十年代被稱作先鋒寫作,或那些不再承載某種主流意識形態,標榜無意義或消解中心的寫作,或一些表現所謂後現代主義虛無態度的寫作,也稱為零度寫作了。零度寫作竟然變成類似於遊戲的寫作方式了。零度寫作還成為區分文學是否“介入”。今天這種種的文學現實對“零度寫作”的標舉,顯然已遠遠疏離了羅蘭·巴特論證語言、字詞、形式獨立品質的初衷。如果說,零度寫作質疑和消解了語言中的“詞”與“物”的透明性,很難說今天是走得更遠,還是僅僅在羅蘭·巴特的這一質疑里張望和躊躇。
發展
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思潮的發展歷程中,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掀動了五十年代之後語言學革命的衣角,語言本體論、自律論,形式主義觀念應聲而至。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都從語言學革命中受益良多。《寫作的零度》正是在語言學革命深刻影響的背景中,發現了“形式”的革命性能力,對傳統的形式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反撥。
索緒爾從符號中分析出所指與能指兩個維度,前者是概念、內涵,後者是音節(音響形象)、字詞、形式,如“某種動物”表示為“cat”這個音節。但通常,只把能指維度稱為(狹義的)符號。所指和能指的遇合完全是偶然性的,任意的,二者之間並無可以論證的必然聯繫。這說明,所指與能指的聯繫並非出自天然,而是人為賦予的結果,是一種約定俗成的作用,一種習慣用法。
寫作狀態
 零度寫作高手劉曉剛
零度寫作高手劉曉剛零度寫作是一種以“零度”的感情投入到寫作行為當中去的狀態。零度寫作並不是缺乏感情,更不是不要感情;相反,是將澎湃飽滿的感情降至冰點,讓理性之花升華,寫作者從而得以客觀、冷靜、從容地抒寫。一個寫作者,最怕的就是讓泛濫的感情淹沒了他的心靈,淹沒了他的視野,淹沒了他的筆端。感情成災,如脫韁之野馬,如決堤之洪水,作品成了主體某一狀態下情緒失控的圖解和詮釋。這樣的作品示人,人莫不笑之。
一個人的感情,無不出於愛憎。憎必傷人,也自傷;愛太切太過,對人也莫不有害,且易折。零度寫作,就是以第三者的立場冷眼旁觀愛憎兩種,冷眼旁觀萬千世界種種,而後能不偏不倚,不躁不急,心平氣和,以臻寫作化境。 在零度寫作者的眼裡筆下,無論愛憎美醜,都成一審美客觀對象,寫作者與他寄託或生髮感情的對象之間的關係猶如高超的匠人之於金銀胚胎。零度寫作將熾熱的感情凝淀下來,看似冷靜淡漠,實是將愛升華到了大愛,鹹情通過文字表達得更深沉、細膩、熱烈、作品被賦予生命得以流傳。
形式意義
古典寫作
古典寫作同樣藉助於字詞和語流,然而它秉持這樣一種觀念:字詞和語流因某種外在於它的意義而存在,隨著意義的表達,字詞和語流在前進之中相互淹沒,最終只剩下一個意義的核心,而字詞和語流已經隱匿不見。暫且不論形式自身的意義生產機制,如果說字詞背後的確存在某種意義,那么首先也必須看到,正是字詞和語流的連續前進,意義、思想和情感才可以得以產生。“言語就是一種包含著更富精神性的構思的時間,在其中,‘思想’通過偶然出現的字詞而逐漸形成和確立。”語言行為造就了意義的果實,沒有語言行為,意義就無從產生。語言符號和某種意義的交遇,顯然不能不以語言符號的運動為前提。獨立品質
獨立品質使形式不再負載某種情感或思想,不再是作家意圖的具體體現,不再是作家主體的一個輻射。獨立的字詞由於消除了一切相關的固定的聯繫,產生了“不確定的而可能存在的無數關係”。字詞的這種不確定性和潛存的無數可能性,在水平結構和垂直結構中隨處可見。在這個屬於自己的純粹世界裡,字詞與字詞互相關聯,語流與語流相互撞擊,“詩的字詞是一種沒有直接過去的行為,一種沒有四周環境的行為,它只提供了從一切與其有聯繫的根源處產生的濃密的反射陰影。”字詞即是一切,它既是一個獨立的客體,又是一個獨立的主體。主要特點
中性客觀
這種中性的和“客觀的”零度寫作,與古典寫作所力圖表現的“文字的現實的客觀再現”截然不同。羅蘭·巴特推舉零度寫作,恰恰意在揭開古典寫作中處處標榜的“真實”和“自然”的神話,暴露古典寫作中“客觀”的虛偽性。古典語言在意義和字詞之間虛構了一種透明的確定的關係,通過字詞之間的連續性和直線性關聯,來隱喻現行法則的合理性,以及一種理性的生活態度的必要性。羅蘭·巴特發現,古典寫作中過去式的歷史寫作所表明的秩序,以及第三人稱協作所創設的旁觀者的安全地位,都力圖表明世界的確定性和客觀性,並因此表明,古典寫作正是現實世界的一個翻版,它創造了一個似真的審美世界。而字詞是這個世界表現自己的一種方式而已。語言獨立
零度寫作強調由字詞獨立品質所帶來的多種可能性和無趨向性。然而這種無趨向性越來越被狹隘地理解和使用了。在今天的文學現實中,不無隨意地用零度寫作來定義那些採用了外部聚焦,行為主義式的敘事規範,新寫實小時就時常不乏貶義地冠以零度寫作的頭銜。人們還時常把九十年代被稱作先鋒寫作,或那些不再承載某種主流意識形態,標榜無意義或消解中心的寫作,或一些表現所謂後現代主義虛無態度的寫作,也稱為零度寫作了。零度寫作竟然變成類似於遊戲的寫作方式了。零度寫作還成為區分文學是否“介入”。今天這種種的文學現實對“零度寫作”的標舉,顯然已遠遠疏離了羅蘭·巴特論證語言、字詞、形式獨立品質的初衷。如果說,零度寫作質疑和消解了語言中的“詞”與“物”的透明性,很難說今天是走得更遠,還是僅僅在羅蘭·巴特的這一質疑里張望和躊躇。賈君鵬事件
事件起因
2009年7月16日上午10點59分,一位IP為“222.94.255.*”的網友在百度“魔獸世界”貼吧中發了一則名為《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帖子,帖中內容只有“RT”兩個字母意思為“如題”。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篇只有標題的空帖在發出短短6小時內獲得了39萬多的點擊率,超過17000名網友參與回帖。截至20日18時,回帖數已經達到31萬多,點擊率已達1084萬多,而這僅用了4天時間。這被不少網友稱為“中文網路世界的奇蹟”,而對於這樣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賈君鵬”突然火起來的背後到底說明了什麼,是寂寞的網路文化?還是幕後的推手炒作?網友、專家一時眾說紛紜。網友回帖
回帖中大量網友還將網名改為“賈君鵬媽媽”、“賈君鵬爸爸”、“賈君鵬爺爺”、“賈君鵬姥爺”、“賈君鵬奶奶”等等。隨著回帖數幾何級攀升,賈君鵬的“七大姑八大姨們”紛紛現身貼吧,形成一個龐大的“賈君鵬家族”。就連“賈君鵬的同學”和“賈君鵬的班主任”也趕來湊熱鬧,回帖內容也愈發無厘頭。 一個被反覆引用的網友回帖或許說明了原因:“我們跟的不是帖子,是寂寞。”帖子所在的魔獸吧,大部分吧友都是魔獸世界的玩家。2009年6月初,《魔獸世界》由於運營權的改變,遊戲伺服器開始暫時關閉,目前已經超過了40天,這使得上百萬名魔獸玩家處於焦急的待中。 網友惡搞的“賈君鵬回家吃飯”
網友惡搞的“賈君鵬回家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