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歷
1917年7月20日出生於湖北。
 武漢大學
武漢大學1937年畢業於河南開封濟汴中學,同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1943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同年進入中央研究員社會研究所讀研究生。
1946年1月任助理研究員。
1950年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55年任副研究員。
1979年任研究員,1986年8月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1999年1月退休。
2012年夏病逝,享年95歲。
主要論著
獨著 :China’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931~1946,社會研究所,1947;《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1985~1914)》科學出版社,1957;《十九 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唐廷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人民出版社,1987;《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金融活動》,人民出版社,1999;《中國資 本主義的發展與不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總體考察和個案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近代中外經濟關係史論集》,方誌出版社,2006。合著:Industrial Production&Employment in Pre-war China,Ecomonic Journal,1946.9;《中國國民所得(1933)》,中華書局,1947;《 中國近代經濟統計史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中國通史》第10 冊,人民出版社,1992。 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
人物評價
潛心研究
 汪敬虞
汪敬虞1943年,汪敬虞從武漢大學經濟系畢業。他拒絕了俸祿優厚的中央銀行的聘約,懷著研究學問的堅定意願,進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當一名研究生。那裡的薪俸菲薄,條件艱苦,沒有象樣的工作環境,可他卻安於清貧。在四川的一個偏僻山村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潛心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
汪敬虞在大學期間,就表現出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工汪敬虞的氣質和素養。從1942年開始,他在認真攻讀大學課程的同時,以極大的興趣開始研究國際金融問題,在重慶的《金融知識》雜誌上先後發表了《紐約金融市場之分析》、《聯邦準備制度信用統制論》等文章,對美國的金融制度作出了頗有見地的分析。此外,他還寫了一些介紹金融和經濟學知識的文章。
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時期,汪敬虞主要研究中國工業生產。在巫寶三主編的《中國國民所得(1933年)》一書中,他擔任其中工業部分的研究。該書於1947年出版。在中國經濟學界,這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有影響的著作。當時,關於中國國民收入和工業發展水平的研究很少,這部著作是最為完備和精細的。一直到今天,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工汪敬虞們仍然不時需要引用這一部書的研究成果。
 汪敬虞
汪敬虞在中央研究院時期,汪敬虞還用英文發表了專著《中國的工業生產,1931-1946》(China’sIndustrialProduction,1931-1946)和論文二十餘篇,其中有在英國皇家經濟學會英文雜誌《經濟學報》(TheEconomicJournal)上發表的《戰前中國工業生產與就業》
(IndustrialProductionandEmploymentinPrewarChina)以及在國內發表的《戰前中國工業生產中外廠生產的比重問題》和研究抗日戰爭時期華北等地工業生產的系列文章。
汪敬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經濟的研究中,得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1949年初,他在報紙上撰文指出:“中國需要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和計畫經濟是不能分開的”,有人主張實行“自由競爭的社會主義”,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行不通的。
論著豐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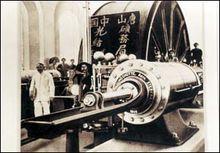 抗日戰爭前中國工業
抗日戰爭前中國工業1953年,汪敬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舊中國為什麼不能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文章。文章剖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對中國民族工業的壓迫和阻撓。他指出:“歷史的現實證明了毛主席的科學的結論,教育了中國人民,只有根本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為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業化。”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當時在《人民日報》主持工作的鄧拓曾親自審閱了文稿,並提出了意見。發表以後,《中國建設》和《人民中國》以及國外一些報刊作了轉載,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
1957年,他彙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出版了,這部近百萬字的資料巨著是一部比較完備、學術價值很高、很有影響的書。出版以後,國內外都有評論和介紹。
在掌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汪敬虞做了許多專題研究。從1953年到1965年,他在《歷史研究》、《經濟研究》、《新建設》和《學術研究》等雜誌上發表了多篇論文,其中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主要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民族工業》、《五四運動的經濟背景》、《關於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鬥爭的資料》、《關於繼昌隆絲廠的若干史料和值得研究的幾個問題》、《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方法論》和《從上海織布局看洋務運動與資本主義發展關係問題》等;研究外國在華資本的主要有:《十九世紀外國銀行在中國勢力的擴張極其對中國通商口岸金融市場的控制》、《關於十九世紀外國在華船舶修造工業的史料》、《十九世紀外國在華的工業投資》等。這些論文提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觀點,開掘既深,又每每闡述了研究中所碰到的一些新問題供大家討論,因而使人們耳目一新。
 汪敬虞
汪敬虞在1979年以後的幾年中,他的專著《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唐廷樞研究》和《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相繼出版。他還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等雜誌上發表了論文《試論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再論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論中國資本主義兩個部分的產生——兼論洋務運動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略論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關於民族資本現代企業發生問題的討論》等等。其中《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唐廷樞研究》兩書受到國內學術界的好評。《再論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一文獲得《歷史研究》第一屆優秀論文的獎勵。進入90年代以後,汪敬虞的學術成果取得大豐收,除了發表大量論文之外,他所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上中下三冊出版,並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等多項大獎,他個人的著作《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金融活動》、《汪敬虞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總體考察和個案辨析》相繼出版。
治學嚴謹
 汪敬虞
汪敬虞汪敬虞是中國經濟史學界的知名學者,但他為人虛懷若谷,處世謙讓。他工作認真,一絲不苟。對於別人向他請教的事,他急人所急,盡力相助。他抽不出時間來整理自己的一部書稿,卻花了大量時間替別人看稿,哪怕是洋洋百萬言的鴻篇巨著,他總是認真閱讀後提出十分具體和中肯的意見。對於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他循循善誘,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傳授給他們,處處為他們考慮,主動為他們創造各種條件。他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為別人(包括自己的學生)修改稿子,發表時卻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他總說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傳統。汪敬虞治學嚴謹,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資料工作,他樂意為從事研究工作的人整理出一些比較可用的資料。他是以協助巫寶三從事中國國民收入的估計開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為了使自己所分擔的中國工業生產部分獲得比較精確的數字,他不避繁難,從零碎的資料中,整理出比較完整的統計,而不願圖省事,採用籠統估計的辦法。例如,關於抗日戰爭前中國工業生產的外厂部分,有人以外廠資本為華廠資本三倍為依據,估計外廠生產也相當於華廠生產的三倍左右。汪敬虞認為,這樣估計雖然省事,但未必符合實際。因為,第一,當時對外廠資本和華廠資本的估計本身就不完整,而且在已有的估計中,兩者的範圍也不一致;第二,資本額的增加與生產額的增加並不能構成正比例的關係。他寧可一家企業一家企業地收集資料,日積月累,不斷補充和修正,而不願作過於粗疏的估計。
當然他並不排斥合理的估計。鑒於中國歷史上遺留的統計資料的貧乏,可靠性又極低,他認為大力收集整理統計之外,還應該容許用合理的估計數字對客觀的經濟形勢,特別是巨觀方面的經濟進行估量。所謂合理,就是這種估計既有充分的事實根據,又有嚴密的邏輯推理。
學風嚴謹
 1933年的中國工業
1933年的中國工業汪敬虞的嚴謹學風,還表現在他從不掩飾自己工作中的失誤和不足之處。像大多數有才能有學問的學者一樣,在他對自己作估價時,看得更多的倒是自己的不足之處。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經和郭沫若、張仲實兩位前輩在古史方面有過接觸,一是他1951年曾為郭老查考希臘黑勞士(Helots)的身份地位,一是1952年曾為張仲實先生所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根據英譯本進行校核。這兩項工作都得到兩位前輩的稱許,但他始終認為自己擔任這兩項工作並不相稱,惟恐產生誤差有負重託。1953年他又受嚴中平先生之命合作翻譯馬克思論中國的幾篇評論。[3]在翻譯過程中,他深深感受到,要準確地翻譯馬克思的著作,需要博大精深的理論修養和知識結構。他不滿意自己的工作。該譯稿曾請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校閱,向達寫了一篇譯後記,對有關史實作了詳盡的論述,這使他親身感覺到前輩學者的淵博恢弘,同時也感覺到自己的不足。他認為在他所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和參加編輯的《中國近代統計資料選輯》中,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誤,他多次計畫作徹底的修改補充,卻始終未能如願,因而經常感到不安。他對自己的其他一些著作也自我要求甚嚴,反覆反省。
主要貢獻
資料彙編
汪敬虞為收集和整理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勾勒出了1895至1914年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基本輪廓,使讀者能了解外國在華工業資本、官辦工業資本和中國民族私人工業資本的基本狀況及相互關係。這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做了一件極有益的基礎工作。1959年和1962年,汪敬虞和其他一些為編寫《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5)》,曾兩次到上海收集資料,前後工作一年以上。上海是近百年帝國主義侵華的主要基地,也是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城市。在上海藏有大量的歷史文獻。他們在上海期間,先後共收集到中西文資料數百萬字,受到學術界的注意。對此,1962年上海《文匯報》專門作了報導。
外資研究
關於外資侵華的研究。汪敬虞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和《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金融活動》等三部專著及一些論文。《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是一部著重分析歷史過程的專著,涉及到外資侵華的每一個方面。這部大著由十七個相對獨立的專題組成,是迄今所能見到的關於研究十九世紀外資侵華過程的最為完整和詳盡的著作。
歷史過程如果說,《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是從面上來把握當時的歷史過程的話,那么《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則是以一個典型人物為中心,作輻射狀的研究,以此來深刻地展現外國侵華的歷史過程。在西方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中,有所謂“赫德中心論”這樣一種說法。他們美化赫德,歪曲歷史。這是對中國人民歷史的挑戰。《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就是為了接受這個挑戰而撰寫的。以豐富的史實,揭示了赫德在中國海關的罪惡活動,揭示了他插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掠奪,插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掠奪,還參與了他們在中國的非法的暴力掠奪的罪行。《赫德與近代中西關係》對赫德活動的特點進行透視,揭示了這個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金融活動》第三部著作則是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的《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金融活動》。正如汪敬虞在前言中告訴的,這項工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之末,距本書出版已有40年之久。在此期間,汪敬虞披閱了北京各圖書中心所藏資料,還先後兩次赴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收集館藏19世紀中西文報刊和各種遺存文獻中的有關資料,並據此撰寫了一部30萬字的專著初稿。其後又在此基礎上,先後寫了近50萬字的專題論文。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專著既未能定稿付印,專題論文也有一部分未能及時發表。後來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第二卷(第一卷是嚴中平先生主編的),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尋常,直到二卷脫稿後,才終於揀起自己開始於數十年前的稿子。
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首先在於其歷史資料異乎尋常的豐富。外國在華金融活動之所以是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首先就在於研究資料的不易獲得。研究華資金融好歹還有檔案可看,而外國在華金融業的檔案資料很少,特別是1927年以前的外國銀行檔案,目前在國內幾乎看不到。而當時幾種主要的金融業刊物,如《銀行周報》、《錢業月報》等,也主要是介紹華資金融業的情況,對外資金融的介紹比較簡單。
買辦研究
汪敬虞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唐廷樞研究》,此外在一些文章中也涉及買辦問題。在《唐廷樞研究》中,他研究了唐廷樞的生平。他不同意以往有關研究中的揚鄭(觀應)抑唐(廷樞)之論。有人認為唐是地地道道的“洋務派集團中的人物”,“屬於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而鄭則代表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汪敬虞認為,唐廷樞和鄭觀應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主要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是由買辦而投身於洋務企業。至於兩人的不同之處,在思想理論方面,鄭觀應固然比唐廷樞看得深遠,他的著作寫了唐“看不到也說不出的東西”,但在社會實踐和實際效果方面,唐是高鄭一籌的。以唐廷樞的生平為中心線索,生髮開去,精闢地闡述了買辦研究中的幾個重要理論。從雙重身份的研究,汪敬虞得出了買辦財富主要來自其自營商業的重要論斷。這同過去一般所認為的買辦收入主要來自佣金的說法是不一樣的。汪敬虞指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洋行與買辦之間,佣金制度還沒有正式建立。當時有許多洋行寧願支付固定的工資,而不願買辦在生意中抽取佣金。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佣金制度逐漸建立起來。最初買辦的佣金,一般為2%,其後由於競爭,佣金趨於下降。到了六十年代後期,有的仍能維持2%,有的則已下降到1%。從七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八十年代終了,1%的佣金率已成為普遍的現象。到九十年代初,則進一步下降為0.5%以至0.25%。從1865年至1894年的三十年中,貿易總額累計為49億海關兩。三十年間,佣金的數額按最高的比例計算,即使全部進出口貿易都經買辦之手,並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1億兩;如按最低的比例計算,則不過1200萬多兩。這個數目,顯然不足以構成數以千百計的買辦的暴發財富的主要部分。汪敬虞認為,買辦以其特殊身份所從事的自營商業是他暴富的主要途徑。
汪敬虞還論證了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時期,買辦資本大量向民族資本轉化的史實。汪敬虞以豐富的史實說明:中國最早的一批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資本,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由買辦資本轉化而來。接著,汪敬虞分析了為什麼買辦比甚至積累了更多財富的官僚、地主和舊式商人更願意投資於資本主義新式企業的原因。汪敬虞指出:買辦之所以最先投資新式企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觸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是他的資本最先享受了這種剝削方式的“果實”。他的資本運動和他的主人——外國資本家的資本運動,保持亦步亦趨的關係。追求最大利潤的原則,在作為外國掠奪者的工具的買辦資本的身上,同樣起著支配的作用。作為外國侵略者的貿易掠奪的工具,買辦在分取佣金之外,還建立了自己的商業機構,從中分取更多的商業利潤。當外國侵略者從流通領域擴大到生產領域,從貿易活動擴大到投資活動的時候,買辦也自然而然地在附股外國企業之外,又建立起自己的企業,從而取得更多的企業利潤。買辦資本從流通領域向生產領域的轉化,從附著於外國企業到自辦企業的轉化,這並不是出於買辦的愛國心和民族感,但是它代表著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的轉化,是歷史的進步。同時,它又使新生的中國資本主義企業和外國資本勢力不能不發生先天的依存關係。
研究作品
汪敬虞在這方面的作品有《試論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論中國資本主義兩個部分的產生——兼論洋務企業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關於民族資本現代企業發生問題的討論》、《略論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產生過程》、《中國近代手工業及其在中國資本主義產生中的地位》等文章。經濟史學界有許多人的意見認為:由於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的性質不同,因此,兩者的產生也必然沿著截然不同的途徑。從早期的洋務派企業到北洋軍閥官僚資本以至四大家族的形成,這是官僚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一條途徑。而早期的民間近代企業,則是繼承封建社會中的資本主義萌芽來的,由此而發展為民族資本主義。對此,他作出了不同結論。他以煤礦、紗廠、雲南銅礦、四川鹽井等行業的情況為例,論證了在中國現代工業產生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許多部門中原有的手工業,並沒有發展成為使用機器生產的現代工業。
中國手工工場向大機器工廠過渡,不是發生在大機器工業出現之前,而是發生在大機器工業出現之後,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特點的產生是由於中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特別堅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後,在為外資掠奪原料、推銷成品服務的行業(如廣東的繅絲業、上海的船舶修造業等)中,出現手工業向機器“過渡”的可能性。但深入的研究表明,從經營者、資金、機器、技術等諸方面看,新式的機器工業都不是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因而,從資本主義萌芽到早期民間近代企業不可能是大量的,更不可能是主要途徑。也就是說,兩者之間並無直接繼承性。至於洋務派企業,也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看作是官僚資本主義的起點,因為官督商辦企業中始終存在著兩種力量和兩個前途的矛盾鬥爭,有些官督商辦企業後來演化為商辦企業。他認為,為了證明一脈相承,而把洋務派的企業說成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企業,這是來自一種沒有根據的簡單類比的結論。
汪敬虞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產生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有大的和中小的不同,也就是有官僚、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的區別。但是,承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本的同時存在,並不一定意味著它們的產生,也沿著截然不同的途徑。也就是說,要看到過程的複雜性,不能簡單化,一刀切。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產生,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途徑,也可以說三種不同的類型。他以繅絲工業為例,說明在中國民族繅絲工業的發生過程中,既有純粹商辦繅絲廠的設立,也有洋行買辦附股外商絲廠和洋務派官辦絲廠的轉化。這三種途徑帶有普遍性。
汪敬虞認為,在現有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專著中,談到現代企業產生的歷史條件,幾乎無一例外地從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貨幣財富的積累三個方面進行分析。這是需要的。但這種分析不能從概念出發,不能像分析西方國家那樣來分析中國,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不同,一定要從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來進行研究。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則幾乎成為所有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片空白,這就是從生產力的變革方面去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產生。生產力的研究,也就是用什麼生產工具進行生產的研究。這是區別各種經濟時代的最後根據。在這方面,他研究了外國技術的引進同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的關係。
汪敬虞對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形成的過程。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工商行業,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條件下,面臨著兩種不同的變化。一是受到外資的排擠和打擊,從而走向衰落,甚至遭到淘汰;一是轉而適應入侵的資本主義的需要,從而得到保存,甚至還有所發展。
工業資本研究
1933年的中國工業
在巫寶三主編的《中國國民所得,1933》一書中,汪敬虞承擔製造業部分的研究。當時的經濟統計研究所有一個關於1933年中國工廠生產的統計。但這個統計有三個主要遺漏的地方:未包括外廠;未包括東北和一些邊遠省份的工廠;未包括發電、貨幣製造、影片製造等工廠。汪敬虞的統計則補充了這些遺漏,並作了其它一些修正和補充,作出了一個比較完整和準確的統計。在英國皇家經濟學會主辦的英文雜誌《經濟學報》上發表的《戰前中國的工業生產和僱工狀況》一文中,汪敬虞把1933年中國工業發展水平同西方國家作了比較。他還對抗日戰爭時期華北的工業生產發展水平作過很深入的研究,主要論文有:《戰時華北工業資本與生產估計》、《戰時華北工業生產指數》、《戰時華北工業資本、就業與生產》等。這些工作在當時都是具有開拓性的。
中國經濟史研究
這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過去流行的中國近代史的中心線索是所謂“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上世紀八十年代許多學者提出異議,認為應該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中心線索。汪敬虞則在此基礎上更深入一步,認為不僅要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要研究它的不能充分發展及其原因。這種不能充分發展,不僅表現在資本主義的總體水平上,而且表現為點與面的不協調,表現為點上的發展與面上的不發展並存的局面,先進的工業與傳統的農業長期並存,機器大工業與手工業長期並存。
汪敬虞認為,研究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不發展,不僅能更為準確地認識中國近代史,也能啟迪對當前現實的反思,因為這是認識中國國情的基礎。關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問題,曾由《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在1989年組織了一次筆談形式的大討論,以後在別的刊物上也出現了專題討論的文字。汪敬虞在這些討論中汲取營養,並把自己的觀點闡述得越來越清楚。2002年,他出版了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問題的《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
綜合研究
汪敬虞參加了由嚴中平先生主持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的專題研究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晚期,汪敬虞則主持了《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這一“八五”國家重點研究項目。該項目歷時十餘年,汪敬虞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尋常。最終的成果是於2000年出版的,全書178萬字,分上中下三冊[8]。該書的寫汪敬虞們在汪敬虞的布置下,注重發掘第一手資料,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構造總的研究體系,成為有分量的巨著。汪敬虞近期發表的論文集《汪敬虞集》和《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總體考察和個案辨析》也可以歸入綜合研究的範疇。前者收集了汪敬虞的論文19篇,後者則收集了汪敬虞的論文20篇,兩者的內容少有重複之處,都從巨觀和微觀兩個方面論證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