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成毛筆莊古文記載
“夫治世之功,莫尚於筆,能舉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聖人之志,非筆不能宣,實天地之偉器也。”制筆之藝始自稽古。昔黃帝垂拱以治,而興文明;倉頡氏俯仰天地萬物之形,然後作字,而泣鬼神;嬴秦做主中國,斯相變字古法,而書同文,蒙將軍損益聿工,而筆同制,後世以為制筆之師、祖也;漢魏以降,歷代高手匠人各有增益;至於唐宋,則璨然大備;而有清一代,制筆之藝愈精,多有前代之未發明者,更以隴海路為界,有南北派之分。
張學成毛筆莊者,創自清光、宣年間,屬南派贛系,與吳興“湖筆”同一祖源。自曾祖開基,綿延至今,幾近百年。民國初,避兵亂,祖父西遷入滇。初,因不合滇雲裝口,慘澹經營而已;遂潛心鑽研,結合滇人(昆明)使用習慣,改革制筆工藝,又推出發岔包修服務,遂聲名漸響,先後在正義路、武成路購置鋪面以“前店後坊”式經營,至此張學成毛筆莊初見規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昆頗有名氣。
現主事人明傑先生自幼隨父學藝,青年時曾遊歷齊魯陝甘諸路,與北派同行研討切磋、共相發明,是以能兼得南北派之精義(南之羊毫、紫毫;北之狼毫、兼豪)。後併入合作社,忽值風雷改,旋至蹉跌,困而彌篤,始終堅信:制筆者如用筆者,心正則藝能精,藝精則筆正。以心正為上,虛懷若谷,總齊四德(尖、齊、圓、健)。改革開放以後,為弘揚民族手工藝,回報廣大老滇人數十年之支持、厚愛,張學成毛筆莊重新掛牌營業,逐漸恢復各種名牌筆的製作銷售,技術上精益求精,同時隨時代發展,力求有所變,又有所不變;恢復“發岔包修”,推出“當面試寫”的服務;又與時俱進,恢復和發展了具有觀賞和紀念性質的“人發”和“胎毛”筆的製作。
正所謂:“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天緯地,錯綜群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晉郭璞)
張學成毛筆莊品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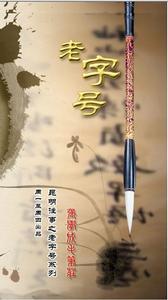
一、祈福筆
朱衣筆,亦即胎毛筆,是將顧客提供之小兒胎毛製成筆,以祈求子女健康成長、聰慧能幹。
春秋筆,也稱祈壽(福)筆,是將顧客提供之老者頭髮或鬍鬚製成筆,以祈求三星高照,賜給持此筆者多壽、多福、多喜。
五色生花筆,也稱文昌筆,是將顧客提供之將參加中高考等升學考試之學子頭髮製成筆,並用五色絲線纏繞,以祈求文昌帝君庇佑,賜給持此筆者多智、多慧、多祿。
二、紀念筆
夫妻結婚紀念筆:將顧客提供之夫妻二人頭髮製成筆,取結髮同心之意,刻字紀念。
夫婦結婚周年紀念筆:將顧客提供之夫妻二人頭髮製成筆,作為結婚周年的見證,按結婚年限,筆桿分別取竹、木、牛角、象牙、金屬、景泰藍等,刻字紀念。
友誼常青紀念筆:將顧客提供之多人頭髮製成筆,可兩人、三人、乃至多人,取同心同德之意,刻字紀念。
江右商幫曾經輝煌
張學成推著獨輪車,從江西到昆明,整整走了48天。
那應該是民國初年。張學成為避兵亂,西遷入滇。後不久,在昆明這片土地上,就有了一家“張學成毛筆莊”。
走進歷史的年輪,可以很清晰地了解:這位成就百年老字號的人,只是個普普通通的江西商人,但,也是與“江右商幫”有關的江西商人。
江右商幫,是一個已不太能為國人所記起的名字。顯然,談起商業、商人,人們說得更多的是晉商、徽商,或者寧波幫、潮州幫。確實,它們紅極大江南北,財流五湖四海。
而江右商幫,只能算有“曾經的輝煌”。
歷史賦予它的活躍期是,500年。從元末明初興起,明朝前期獨領風騷;明朝中後期及清朝前期,與晉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走向衰落。在那個時期,中國有十大商幫: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陝西商幫、寧波商幫、山東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
所謂的江右商幫,指的其實就是江西商人。魏僖著《日錄雜說》記載:“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蓋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故,古代江西商人習稱江右商幫。當然,十大商幫的區分,所依據的絕不僅僅是地域,重要的是不同的經商之道。江右商幫的特點,以現在的話說,是充滿了“草根”色彩。
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描繪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江西商人的小本經營狀態躍然紙上。
“無江西商人不成市場”,在幅員遼闊的古老帝國里,江右商幫的“草根”們,靠著雙腳,挑著擔子,走州過府,深入城鄉村舍,融通著有無。它不像後來崛起的晉商和徽商,要么搞壟斷經營,要么靠官府力量。它以人數眾多、積極活躍、不避艱險、滲透力強著稱。挾小本,收微貨,隨收隨賣,操業甚廣:“挑擔燈芯草,一路賣三年。莫看生意小,蓋樓又買田。”
可以想像,張學成就是這樣隨著祖先的腳步,來到雲南昆明,做起了賣毛筆的小本生意。不僅是他,昆明的“張學林筆墨莊”、“張學文筆墨莊”,也都為江西人所有,甚至整個昆明的毛筆市場,都由江西人壟斷著。歷史可查,當時有20多位江西撫州一帶的人,在昆明做著大大小小的毛筆生意。這是江右商幫與雲南的淵源,更具體地,是撫州商人與雲南的淵源。
明朝時,曾在雲南做官的浙江人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論及當時的商業之盛,他又感慨:“作客(外出經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撫州。”
王士性的記載絕非虛言。在雲南普洱的茶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著十幾座江右商幫的會館。這些會館遍布大江南北,甚至流傳到了東南亞。至今,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仍有江西會館留存。由此,江右商幫“曾經的輝煌”可見一斑。
但它終究走向了沒落,為何?
有人說,江西文化受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影響太重,或者“小富即安”,往往是在外賺了一點錢,便回家買田置地而不再經商。有人說,“人稠地狹”是驅動它原來商業精神的根本動力,某段時期的人口銳減改變了這樣的狀況,江西人也就開始安享“土裡刨食”的生活。而走州過府的辛苦,作客他鄉的艱難,開始被視為畏途。江右商幫逐漸消失了,江西人的商業精神也隨之被塵封。還有人將其歸結為江西商人競爭意識不強、“做大”意識缺失、危機意識淡薄、冒險意識不足……一言以蔽之,江西商人多商業智慧,少商業精神。可以印證的是,現今,也有很多江西商人活躍在全國各地,也確有一定的業績,但其規模及影響與外省同類競爭者相比,似乎總少了一份獨領風騷、傲視群雄的霸氣和決心。
盛與衰,究其原因,現難有定論。
可江西人不能不反思、探究:祖先吃苦耐勞,擅長經營的特質為何未能傳衍?新一代的贛商崛起又在何時?為重現昔日商戰雄風,後人又該如何拼搏?
口述歷史
“那時政府辦公都用我們的筆”
桂煥蘭(張學成毛筆莊第四代傳人張明傑的夫人)
我的娘家也做毛筆,不過不如張學成毛筆莊有名氣。
一款好的毛筆必須具備“四德”,即“尖、齊、圓、健”四點。要做好一支毛筆,共有四大工序,一百多道小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馬虎:首先是選料,狼毫要東北冬天黃鼠狼的尾須,羊毫要江浙一帶的羊毛,筆桿可以從西山區墨雨龍潭選上好的竹子……
第一道大工序是“水盆”:在水裡梳理毛須,無論天寒地凍,一律不準用熱水,還要脫脂;第二道大工序是“乾作”:做筆桿,裝筆頭;第三道工序是“整筆”,就是把筆頭梳理得美觀齊整;第四道就是“刻字”,在筆桿上鐫刻下什麼筆,出自哪裡。小工序很多,要說清太難。
我的後輩,沒有一個會全部制筆工藝。大兒子還算好,能刻字,近些年我做的毛筆,字都是他刻的,但關鍵的筆頭,他還是不會弄。
其實,我們也沒想過要後輩來學這門手藝,除了用毛筆的人少了的原因,也跟當年我一家子受的難有關。
毛筆生意開始不好,是從1952年開始的。1958年,各種各樣的原因,張明傑被“勞改”,一直到1983年才放出來。那些時候,我30歲不到,一個人養著一大家子,苦呀!去看張明傑的時候,他有時會問:“還做毛筆沒?”我就賭氣說,都家破人亡了,還做什麼毛筆。其實,我說的也是真心話,後來小孩長大了,我也沒想讓他們學這個手藝。
不過,為了餬口,張明傑出來後,還是做起了毛筆生意,先是在大觀街上擺小攤,後來,又到現在的小巷(西安馬路)租了小鋪子。毛筆都是我和張明傑在家裡做的,後輩有時幫點雜活,但也不怎么弄。2000年,張明傑的眼睛又失明了,做不成毛筆,最後就只剩下我做了。
在這裡開了那么多年的小鋪子,每個月其實賺不了多少錢,除了房租就沒什麼了。你看我在這坐一天,就沒幾個來買毛筆的。也算好的了,現在還有些人喜歡練書法,小孩子也學點毛筆字,也還有些人識貨,就喜歡我這的筆,找著買,說是很多商場賣的筆質量很不好,就是沒有“四德”,用不了多久就壞了。
不過,不管怎么樣,只要我還賣筆,筆就還是像老樣子,做得“扎紮實實”的,你是不知道,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的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交通廳那些政府衙門,辦公用的都是我們的筆。龍雲的秘書來買筆,我們最多也只是給七折。
還有,原來的“發叉保修”、“當面試寫”的服務,我也會堅持,做生意要實在嘛。
金字招牌,絕佳口碑
買毛筆可以試墨,不好包退阿允暢(原昆明某報記者)
1987年11月21日,在昆明大觀街一個毛筆的小攤上,擺設著各種大小不同的毛筆,棚頂懸掛一塊張學成筆莊的招牌。一位銀髮閃閃,紅光滿面的老叟在售筆。一些中國書法愛好者正在挑選,端詳著一支支的筆鋒……
這位售毛筆的白髮老叟,叫張明傑,祖籍江西,是有名制筆師張學成的後代。解放前,張學林、張學成兄弟的毛筆覆蓋了雲南。記者小時讀私塾,用的都是張氏兄弟的毛筆,據張明傑老師傅說,從他父親起,在雲南制毛筆,已足足有90多年。直到1956年,張學成毛筆莊才沒有做筆。文革中,他又被遣送農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指引下,又使沉寂了30年的張學成毛筆莊甦醒了。
張明傑說,製作一支好筆,要用好的原料和精緻的工藝。他為了恢復名品,滿足各方需求,花高價去買好原料來製作。
他對來買毛筆的顧客說:“我的毛筆可以試墨,如果筆鋒發叉,包退。”待顧客選好筆後,如果試,張明傑就打開擺在攤上的墨盒讓顧客蘸墨試書。這在春城還是鮮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