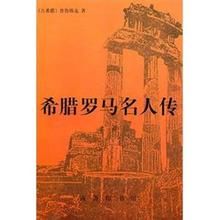《呂庫古傳》是研究希臘歷史、尤其是斯巴達歷史不可不讀的重要歷史文獻,歷來為後世史學家——包括哲學史家和教育史家所重視。例如,羅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學史》中大段引用了《呂庫古傳》中的資料,幾乎所有的教育史著作在敘述斯巴達教育時都參考了普魯塔克在《呂庫古傳》中的記載。可以說,《呂庫古傳》現已成為人們研究斯巴達教育的主要資料來源。
簡介
閱讀《呂庫古傳》使我們確信,斯巴達教育屬於非常古老的人類教育類型。研究斯巴達教育,可以“使我們追溯到這樣的時代,即具有某些共同特徵的人們(如相同的年齡、性別、職業、圖騰),為能抗拒自己周圍不可捉摸的世界的神秘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總要在部落內部組成一些相互從屬的群體,任何人不敢輕易進入或離開這種群體。由於條件改變而引起的群體變化,就需要經過一定的典禮儀式,把人們納入新的群體,在這種納入儀式中,尤其重要又極其普遍的是男童青春期的納入儀式。” 正像博伊德和金所指出的,如果我們不迫使自己接受斯巴達人尚帶有人類早期生活中那些極其原始的生活習俗的原型這一結論,我們就不能研究保守的斯巴達教育制度。 斯巴達生活中那些顯著特徵,原為希臘人所公有,但斯巴達人特殊的生存環境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與外部世界相隔絕,他們在很長時間內墨守著原始部落時代的一些古老生活方式,從而為後世保留了一個早期人類教育的典型。但許多人顯然是把斯巴達人中那些近於史前人類生活的慣例的生活特徵都歸於一次特別的法令,其謬誤已為上述兩位史家所指出。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斯巴達人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培養他們自己時代的德性的。
作者簡介
普魯塔克(約46—約120),出生於希臘中部貝奧提亞地區一個名叫凱羅涅亞的小鎮。其父是一位對哲學很有研究的歷史學者,這給普魯塔克很大影響。普魯塔克少年遊學於雅典,拜逍遙派哲學家為師,兼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畢達哥拉斯各派學說之長,獲得廣泛而充分的文化教養。
普魯塔克一生擔任過許多公職,在潛心著作的同時還熱心於公益事業。他是古代多產作家之一,其著述共有277種,除去其中130種已散失,另一部分為偽書外,保存至今的尚有100多種,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稱作《道德論叢》,約60篇,包羅有關倫理道德、宗教、哲學、政治、科學、文藝各方面的論述。另一類稱作《名人傳》,包括現存的希臘羅馬名人傳記50篇。兩類著作互為補充、相輔相成,一個向我們表明古代世界在行動領域裡取得什麼成就,一個向我們說明古代世界在思想領域裡想要達到什麼目標和取得什麼樣的成就。
雖然普魯塔克撰述希臘羅馬名人傳的主要目的乃是為了發揮和宣揚他的倫理思想,但使他名垂千古的卻是《名人傳》而不是《道德論叢》。《名人傳》以古代廣闊的歷史舞台為背景,塑造希臘羅馬歷史上各種類型的人物形象。普魯塔克純樸、清晰、曉暢的文體,細緻入微的人物刻畫,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以及行文中綴嵌的奇聞逸事和雋語名言,使他的《名人傳》贏得一代代讀者的讚賞,成為西方世界流傳最廣的經典著作之一,尤其文藝
復興以後,《名人傳》被翻譯成法文和英文,影響日益擴大,幾乎成了家喻戶曉、人人愛讀的經典名著。像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亞、培根、拿破崙、貝多芬、歌德、希勒、尼采……都十分喜愛普魯塔克的著作 。
普魯塔克在為呂庫古樹碑立傳的過程中,詳述了斯巴達在培養德性方面的各種做法,這些做法集中到一點,就是使斯巴達人的生活教育化,把包括政治、經濟在內的各種社會活動與德性的培養緊密結合起來。
主要內容
斯巴達人極力維護社會成員內部在政治、經濟活動中的平等權利,竭力防止兩極分化,以求整個民族在穩定和團結中求得生存和發展。這是人類早年求生本能的反映。沒有這種根深蒂固的生存需要作基礎,所謂的呂庫古立法就不可實現。呂庫古立法主要有三項內容: (1)創建了由28人組成的元老院。普魯塔克在論述創建元老院的意義時引用柏拉圖的話說,由於元老院同國王們在最重要的事務上具有同樣的決定權,從而給國家大事的協商帶來了穩定和節制。(2)重新分配土地。當時斯巴達人的兩極分化已趨嚴重,“在這方面存在著駭人聽聞的不平等:城邦因充滿了貧窮的、無依無靠的人而負擔沉重,而財富卻全部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他決心要消除驕橫、嫉妒、罪行、奢侈以及那更加根深蒂固地折磨著國家的弊病:貧與富。他說服了同胞將所有的土地變成了一整塊,然後重新加以分配;勸說他們彼此在劃一的、生計上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生活在一起,單憑美德去博取功名;使他們確信在人與人之間除了那種因行徑卑賤而遭到譴責和因行為高尚而備受讚揚的區別以外,是不存在其它差別和不平等的。”
除了重新分配土地,呂庫古還分配了斯巴達人的流動財產。他看出人們是不容忍自己的財產直接從身邊被取走的,於是,就採取了另一種方法:用政治謀略去克服他們的貪婪。他取消了所有的金銀貨幣,規定只準使用鐵幣,這種鐵幣易碎,幣值甚小,一大堆沉重的鐵幣只有些微的價值,它們“即不便收藏,也不值得收藏,不,甚至切成碎片也不能帶來任何利益,還有誰要去偷竊它呢?” 所以這種鐵幣通行的時候,許多罪惡都從斯巴達消失了。” 當然,消失的不僅有罪惡,也有新興的文明的萌芽,這是普魯塔克沒有看到也不願看到的。他說:“因為沒有貨幣,就不可能購買外國貨物或古玩擺設;航海商旅就不再將貨物運入斯巴達的港口;修辭學教師就不再涉足拉科尼亞的土地,就再沒有流竄四方的占卜者,再沒有蓄養妓女的人,再沒有金匠和銀匠。於是,奢侈就這樣漸漸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 無須說得,取消了“奢侈”這類一般道德家視為“惡”的東西,也就取消了歷史發展的有力槓桿,——當然,這也是普魯塔克所不能理解的。
根據普魯塔克的記述,為了更進一步地打擊奢侈風尚和剷除致富的慾念,呂庫古採取了第三個、同時也是最為精心構思的政治措施:即公共食堂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們相互結伴共進三餐,飲用同樣的、指定的食物,而不是在家裡,倚靠著華貴的睡椅,坐在華貴的桌前,讓僕人和廚子侍候自己,像貪婪的動物,在昏暗中吃得腦滿腸肥,屈服於每一種貪慾和各種饕餮之徒的惡習,並且需要長時間的睡眠、熱水浴、充裕的休息,這一切不僅毀壞了他們的性格,而且也損害了他們的身體。基於此,普魯塔克由衷地稱讚公餐制“真是一個偉大的成就,而且是一個更偉大的成就。”
在普魯塔克看來,呂庫古的這三項措施從根本上涵育了斯巴達人的德性——元老院帶來了政治上的節制和穩定,重新分配土地和流動資產從根本上消除了貧富不均這一社會痼疾,養成了斯巴達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生活在一起,單憑美德去博取功名的高尚精神;公餐制不僅使得財富成了不再引人產生欲望的對象,而且使公共食堂成了涵育簡樸、友愛、志趣相投、好惡一致等共同行為規範的學校。
呂庫古制定的這些法律沒有一條是寫成文字的。普魯塔克說,一方面確有神諭禁止他這樣做,而他自己覺得,倘若那些促使城邦的繁榮與美德的最主要的和最有約束力的原則,深深地在公民們的習慣和訓練中紮下了根,它們就會經久不變和牢固可靠,因為通過教育使青年人明確堅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強制更具有約束的力量,教育對於每個青年來說,就起著立法者的職能……呂庫古使得教育完完全全地擔負起立法的功能。 用教育代立法,或者,把教育與立法緊密結合起來,運用教育的力量去促進立法執法工作,確是一條值得注意的歷史經驗。不過,呂庫古當年是否像他的傳記作者所說的那樣是由於神諭或對教育的自覺認識而不制定成文法,這是一個問題。另外,我們也應明確,像公餐制這樣特殊的制度並不是一個人的立法就能確立的,從普魯塔克自己的敘述來看 ,它確是一種古老的社會風俗,而非一次人為的立法活動就能規定和長期實行起來的。
斯巴達教育中的許多因素,都是從原始部落生活風俗中沿襲下來的。例如斯巴達國家對女子教育的重視,就反映了婦女在人類早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過去我們只注意這一現象的健康方面,而很少指出它實際上是史前社會的一種十分落後的遺存。不過,這種在時間意義講非常“落後”或原始的教育,確是令人懷念和想往的:那時的教育與生活水乳交融,互不隔離,它不僅是自然的、平等的,而且是詩意的、智慧的,它在兩性自然平等的發展中,有意無意地遵循著許多規律性的東西:如兩性相互激勵等。普魯塔克說,呂庫古讓少女兒同青年男子一樣習慣於運動時只穿著短袖束腰外衣,在某些歡慶節里舞蹈、唱歌,青年男子則在四旁觀看。她們時而善意地揶揄和挑剔那些行為失檢的青年男子,時而歌頌那些表現出高貴品質的人,以激勵起青年男子們的豪情壯志。 普魯塔克說,少女們衣著雖少——她們參加節日遊行或體育競賽時,半裸著身體出現在青年男子的眾目睽睽之下——卻絲毫不失體面,因為輕浮放蕩已一掃而盡,伴隨著她們的是莊重貞節;不僅如此,這樣還使她們養成了樸質的習慣和對身體健美的熱烈追求。同時,這也給女性們體驗到了一種高尚的情操,因為她們感到在勇氣和抱負這個領域裡,自己也占有一席之地。 普魯塔克還詳細描述了斯巴達人古樸原始的婚姻風習 ,他認為這種婚姻生活鍛鍊了斯巴達人自我克制和節制的能力。作者的許多敘述無疑是些溢美之詞,但它確實為我們提供了古人從衣、食、色等基本方面,自我束縛、自我塑造這一歷史過程的某些重要信息。
普魯塔克不僅從巨觀方面為我們描繪了斯巴達教育的社會歷史畫面,而且還對斯巴達人如何培養合格社會成員作了非常具體生動的敘述。下面我們從個體發展角度來看看斯巴達是如何培養理想德性的。
普魯塔克說,呂庫古把教育看作是立法者最偉大、最崇高的任務。他追根溯源,從精心調整婚姻與生育狀況開始培養下一代的工作。在這裡,普魯塔克顯然又是把斯巴達人的一些風俗歸結為個人立法。根據他的記載,斯巴達人當時在婚姻生活中還有公妻制的成分,但他強調指出:“那時在婚姻關係上普遍存在的自由,目的在於得到健壯的體魄和建立良好的政治,遠不同於後日人們歸咎於婦女的那种放盪和淫亂。 他舉例說,一個年老而妻少的人,如果他看上並器重一位俊美高貴的青年,就可以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妻子,讓他們生子並給予撫養。一個受人尊敬的男子如發現一位婦女給自己的丈夫生下了健美的孩子且舉止端莊而得到自己丈夫的讚美和愛慕,他就可以徵得那婦女丈夫的同意,得到她的歡心。這樣,高貴的種子就播進了能夠結出美麗果實的土壤里。呂庫古不把孩子看作父親的特殊財產,而是國家的公共財富。因此,他不願本邦的公民由隨意結合的父母所生,而希望他們是最優秀的人們的後代。他認為人類制定的許多法律是愚蠢的:“他們繁育犬馬時反倒堅持要得到最佳雄性配種,不惜金錢和利用私人交誼;但是,他們卻將自己的妻子鎖在深宅內院,讓她們只為自己生兒育女,哪怕他們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頭,或是病夫。仿佛血統低劣的子女不首先反映出占有和撫養他們的那些人的低劣、而血統優秀的孩子也不首先反映出占有和撫養他們的那些人的優秀品質似的。”
由於孩子是國家的,父親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撫養孩子。孩子出生後必須經過部落長者的檢查。如果嬰兒勻壯結實,他們就命令他撫養,如果孩子瘦弱畸形,他們就將其扔掉。“他們深信:倘若造物主一開始就沒有把健康和力量賦於這條生命,它的存在於己於國都是毫無禪益的。根據同樣的原則,婦女們往往用酒而不是用水給新生兒沐浴,以此考驗嬰兒的體質。據說烈性的酒會使體弱和患癲癇病的嬰兒驚厥、失去知覺,對於壯碩的嬰兒,卻像煉鋼一樣經受了一次鍛鍊,反能增加其堅強的素質。保姆也極其用心,精於護理。她們不用襁褓裹著嬰兒,任嬰兒的肢體自由發展。她們還教育嬰兒知足常樂、不挑食、不怕黑、不怕獨處,不讓他們沾染上暴燥和哭鬧等等不良習慣。”
孩子長到七歲時,就全部由國家收養,編入連隊。在連隊里他們遵從劃一的紀律,接受劃一的訓練,因而漸漸地習慣了彼此一道遊戲和學習。判斷能力卓越與格鬥極其勇敢的孩子被推舉為他所在連隊的隊長,其它孩子都密切注意他、服從他的命令,甘受他的責罰。所以普魯塔克說斯巴達人孩童時代的訓練實質上是一種關於服從的實踐。一切訓練都在於使他們善於服從命令、吃苦耐勞與能征善戰。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在體質方面的鍛鍊增加了。他們頭髮剪得極短,慣於打著光腳,遊戲時多半光裸著身子。到12歲時,他們就不再穿短袖緊身外衣了,一年發一件大氅,肌膚乾燥堅硬,很少洗沐和塗抹油膏。他們成群結夥住在一起,睡在自己用手從河邊折來的燈心草穗子堆積成的地鋪上。
各連隊的少年由精明能幹、最尚武好鬥的的埃壬率領。所謂“埃壬”是種稱號,指那些從少年班出去已經兩年的青年。他出則指揮其部下摹擬作戰,入則由少年們侍候飲食。偷竊是一件異常嚴肅的事,正如傳說講的那樣,一位少年偷了一隻幼狐,把它藏在自己的大氅里,這畜牲用尖牙利爪扒出了他的腸子,他還是強忍著痛苦,寧願死去,也不願讓人發現他的偷竊行徑。
埃壬常常這樣教育孩子,他吃罷晚飯往榻上一躺,命令這個孩子唱個歌,向那個孩子提幾個問題,如“誰是城邦里最優秀的人?”或者“你認為這個人的品行怎樣?”。孩子們就這樣慢慢習慣了怎樣做出正確的判斷,從小就培養其對公民為人行事的興趣。因為一個孩子若被問及誰是優秀的公民、或誰是聲名狼籍的公民而答不上來,就會被斷定為頭腦遲鈍的人,不是追求美德和榮譽的材料。同時,答話不僅要有理、有據,還要言辭簡潔準確。回答錯了就給予處分:伸出姆指讓埃壬咬一下。埃壬還常常當著長者和官吏的面處罰這些孩子,讓他們判斷他的處罰是否得當或有無道理。孩子們受處罰時,誰也不出面干預,但孩子們走開以後,倘若埃壬的處罰過於苛嚴或過於寬大,長者和官吏就會提出責問並給以指正。
教育下一代是城邦的大事,斯巴達的成年男性公民如果不是公務在身,他們就去督促少年的訓練,指點少年們做些有益的事情。少年們可以見到城邦的長者,因為長者非常關注少年們的訓練,經常到操練的場地去看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競賽,這不是出於好奇,而是作為長者應盡的義務。我們看到,對下一代的培養幾乎成了整個斯巴達人生活的中心。
斯巴達教育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男孩長到12歲以後,就可以與一些眷愛他們的青年男子交往。“寵愛少年的那些人,也分享少年們的榮譽,據說,某次某人因為他所寵愛的少年格鬥時脫口喊出了一句粗話,被行政長官罰了一筆款。這種鍾愛在斯巴達入當中得到普遍的讚許,甚至少女們也在優秀高貴的婦女裡面尋得鍾愛自己的人;然而,此中毫無嫉妒、競爭,相反,那些把他們的感情集中在同一少年身上的人,倒把他們的感情變成了彼此發展友誼的基礎,通過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使他們所鍾愛的少年成為儘可能高貴的人。” 斯巴達人同性之間的這種鍾愛是否只是教育意義的?普魯塔克極力美化斯巴達生活模式,對斯巴達人那種枯燥無味的軍營生活曾使男風盛行這一齷齪現象自然是不願提及了。不過,這一問題的歷史真實面目到底如何(如有人指出雅典教育大師蘇格拉底也有這問題),還待進一步研究。
要深入研究和評價《呂庫古傳》中的教育思想,必須對它所描述的時代有一個大體的確定,不然的話,我們對普魯塔克說呂庫古“是個溫良的人,天性傾向和平”,“斯巴達人在音樂與詩歌教育方面也很認真嚴肅,可與他們渴求談吐純潔所作的努力媲美”,斯巴達人運用語言的成就證明了“熱愛智慧勝過熱愛健身活動是斯巴達人與眾不同的特點” ……等等,感到不可理解。因為按照流行的說法,斯巴達人嗜武成性,殘忍無情,他們獨養勇德,文化上成就甚低……。殺戮希洛人就是最好的例證,而殺戮希洛人的秘密行刑(Krupteia,克魯普特亞)又是呂庫古設立的一個機構。對這些相互矛盾的說法應如何解釋呢?
普魯塔克自己認為:“斯巴達人開始對希洛人如此殘酷無情是較後時期的事情,尤其是大地震之後(在公元前464年),當時希洛人與美塞尼亞人一道反對斯巴達人,在境內燒殺虜掠,給城邦帶來深重的災難。我根據呂庫古在其它方面表現出來的慈祥和正義的性格分析,實在不能將‘克魯普特亞’這個如此令人痛恨的措施加諸在他的身上。” 他贊成古人的一種說法,認為呂庫古沒有參加過任何軍事活動,他的法律是在和平時期制定的。他還說:“呂庫古的主要目的並非要讓他的城邦去統治去統治其它眾多的城邦,相反,他認為整個城邦的幸福如同單獨個人的幸福一樣,繫於德行的廣為流布與自己領土範圍內的和諧。他所有措施調整的目的在於使人們思想開闊、自給自足,在所有一切方面都平和節制;並使他們儘可能長久地將這些品質保持下去。”
普魯塔克的意見是否可靠?說斯巴達人對希洛人從大地震以後才變得殘忍起來,值得商榷。現代研究認為,在公元前七世紀末以前,斯巴達人生活安逸自由,熱愛藝術和音樂,對殷勤的奴隸也有較好的態度,但到了公元前七世紀末的第二次麥西尼亞戰爭之後,斯巴達的文化發展才突然停滯。“例如,最近在斯巴達阿爾特彌斯神廟遺址的出土文物就揭示了這個民族藝術的突然變化。整個七世紀,都能看到一些生氣勃勃的、有地方色彩的藝術品的證據。這些藝術品無論在優美或滑稽方面都表現著典型的希臘人的意識。後來,在非常短暫的時間以後,神廟裡奉獻的祭品不再是精美的了,而且表現出幽默感的那些奇形怪狀的面具,甚至在祭品中再也找不到了。” 斯巴達巨大的社會變革很可能是第二次麥西尼亞戰爭(公元前640年一631年)之後的事,這就是說,如果呂庫古是公元前七世紀末以前的人物,或者說,普魯塔克在作傳時把他當作公元前七世紀末以前的人物,他所描述的乃是這個時期以前的斯巴達教育,那么他對呂庫古其人及他所處時代教育的那些描述,就不是完全不可信的。
對普魯塔克敘述時代有個大概的把握之後,許多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如斯巴達人不重視讀書識字的教育,這一點通常為現代教科書所批評,但對希臘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會因此苛求斯巴達,因為當時的希臘剛剛走出“黑暗時代”,書面文化還未發達,以幾百年後雅典高度繁榮的文化(文字)教育為參照系去批評斯巴達人,顯然不妥。從公元前800年到前500年間,伯羅奔尼撒的科林斯和阿哥斯曾一度是希臘各邦中文學藝術發展的先驅,到公元前七世紀時,斯巴達則遠遠超過她的許多對手,其後就是以米利都為首的小亞城邦,在那裡,希臘輝煌的哲學、科學和藝術之花,在六世紀開始吐蕊開放,而雅典文化的繁榮則是五世紀中期以後的事。對斯巴達和雅典的比較研究應該遵照時代對等的原則,否則許多結論便毫無意義。
評價
普魯塔克以呂庫古立法及其影響為線索,講了斯巴達在幾百年中的變化過程,可以說,一篇《呂庫古傳》就是一部斯巴達簡史。普魯塔克是個道德主義者,他完全從道德教化的角度去評點一切,所以他對許多歷史事實的解釋都是我們不能同意的。他雖然看到了私有財產對斯巴達社會體制的動搖作用,如他認為阿吉斯統治時期,斯巴達人從戰爭中帶回了大量金銀,使得國內充斥了對財富和奢侈的嗜好,從而破壞了呂庫古的“法律”,導致了斯巴達的衰敗,這固然有其歷史真實的一面,但他一味留戀過去,極力美化斯巴達社會中尚帶有濃重原始部落色彩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把它描繪成一個人類在道德上極其高尚和純潔的黃金時代。這種浪漫的懷古幽情本質上是反歷史的。但話說回來,正是普魯塔克的這種真摯、純樸的道德主義情愫,使得包括《呂庫古傳》在內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熠然生輝,使它從問世之日起,就成為西方世界的一種影響頗大的教化力量。至少,如果普魯塔克在創作名人記不懷有純潔道德的高尚意圖,他就不會在行文中那么詳細認真地描繪古代世界的教育風貌,從而為今天的教育史研究保存了大量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