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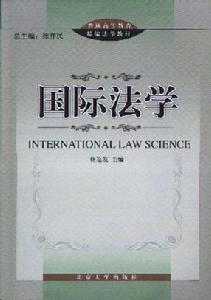 國際法學
國際法學正當性分析
 人道主義干涉
人道主義干涉首先,從倫理道德角度來考察“人道主義干涉”的正當性問題。就干涉行為本身而言,大規模侵害人權確實違背了人類社會基本的倫理道德觀,甚至可能對全人類安全構成威脅,對於這些行為的制止和干預當然是很有必要的,因此限制侵害者的自由並對其進行制裁,在理論上似乎具有倫理道德的可接受性。但從實際看,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都共有某些最根本的倫理信念但也必須肯定它們互相間存在形形色色具體的倫理準則和道德慣例,那么是否所有民族從其固有的倫理準則和道德慣例來對“人道主義干涉”的倫理上之可接受性來進行評價,無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其次,從實踐上的必要性角度來看,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波及到一定範圍時,為保護基本人權而進行干預當然是必要的。但在現實中,對於基本人權的國際保護存在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真正實質意義上的國際保護,即在聯合國體制下的保護,這種方式是在聯合國授權下的行動,是符合國際法的行為,是真正出於維護和實現人權的合法行為;另一種是沒有經過合法授權的個別國家的所謂人道主義的“干涉”,而後者之中不乏打著“保護人道主義”的旗幟而實質上卻是為達到其他目的的干涉的情況。聯合國體制下的國際人權保護在實踐中當然是必要的,並對實現和平安定的國際秩序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沒有經過合法授權的單方面的所謂人道主義干涉的“保護”卻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具有一定的潛在危害性。實踐已經證明,多數方面的人道主義干涉並非真正出於保護人權的目的,而是為少數國家推行霸權主義服務的。
最後,關於“人道主義干涉”在效果上是否具有無害性問題,需從兩方面來進行考察:既無損於國際秩序,也無害於被干涉國的獨立及其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但在實踐中,一些大國往往通過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來獲取各種經濟、軍事及政治利益。在這種複雜的干涉動機之下,要保證效果的無害性也就相當困難了。具體而言,人道主義干涉對國際社會秩序之害可從以下方面分析:其一,人道主義有可能會打破原有國際政治體制的相對平衡格局,會使世界政治格局的一極化發展趨勢更加明顯,因此,人道主義干涉試圖在現有國際安全和爭端法律體制外創設一個“超權利”的作法,這對國際社會穩定和秩序無疑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其二,人道主義干涉會打破數百年來形成的以國家主權原則為理論基石的國際法體系,使國際法失去原有的公平、正義、安全和秩序價值。同時,人道主義干涉所倡導的“人權高於主權”的法律理念會誘導國際法向有利於大國霸權主義的方向變異。
另外“人道主義干涉”對被干涉國之利益也是有害的,比如,會在國際政治和外交方面孤立被干涉國,扼殺被干涉國的經濟發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加劇被干涉國的災難,以北約對南聯盟的人道主義干涉為例,北約的干涉不但在南聯盟地區造成新的直接戰爭災難,而且因干涉而扶植的阿族部隊又成為在該地區製造災難的新根源。正如學者所指出,在人權政治的前提下,即使北約在南斯拉夫的人道主義干涉可以有條件地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但它在南斯拉夫造成了無辜平民的重大傷亡和生態環境的被破壞,這種不人道的後果事實上瓦解了它起先的人道合理性。
因此,國際上的“人道主義干涉”的實踐已經反覆證明了“人道主義干涉”的不正當性,忽視“人道主義干涉”所帶給人們的痛苦及其對國際秩序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盲目的認為“人道主義干涉”已經被各國文化傳統涵納,或者僅因看到其短期的表面效果就認定其具有正當性,這只是少數為某種目的實施干涉的大國的一面之辭。
合法性分析
 人道主義干涉
人道主義干涉首先,可以考查“人道主義干涉”是否符合國際習慣。所謂國際習慣是“國家在互相交往中長期實踐形成的不成文的行為規則”。②而國際法上習慣的構成,須有兩個要素:一是各國有重複類似行為,二是被各國認為有法律約束力。但從這兩方面來看,“人道主義干涉”都不具備國際習慣的要素:首先,儘管人道主義干涉作為一種思潮在西方一些國家學界裡較早存在,但並未形成國家在相當長時間內“反覆”“持續”和“前後一致”的實踐,而且聯合國成立以來國際實踐表明,很少有真正法律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干涉的例子,因為真正法律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干涉”必須是干涉者沒有“相關利益”,單純的人道主義關心應構成“干涉”最主要的動機,而沒有與人道主義同樣重要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或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
其次,人道主義干涉從發端于思潮到形成於實踐,一直遭到國際社會的抨擊和反對,更不要說“被一致認為這種做法是為現行國際法所要求的或是與現行國際法相符合的觀念”;再次,一直以來,人道主義干涉不僅遭到被干涉國的堅強抵抗,而且遭到其他大多數國家的反對,至於其他國家對這種做法的一致默認是無從談起的,其他國家從未也決不會對這種行為予以認同,這明顯地表明國際社會對干涉者的干涉行為缺乏信任。最後,從國際習慣的證據方面看,人道主義干涉無論是在國家之間的條約、宣言、聲明等各種外交文書中,還是在國際組織的判決、決議實踐中,或者在國內法規、判決、行政命令等形式中,不能找到支持人道主義干涉以成為國際習慣的規則證據。
其次,從現存的國際條約中也難以發現“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依據。從現有的國際條約來看,沒有任何一條款規定一國可對另一國實行“人道主義干涉”。相反,還有一些條約禁止此類干涉:如《美洲波哥大憲章》就有禁止個別的人道主義干涉的規定。由此看來,在現行的條約體系內,找不到“人道主義干涉”法律上的依據。雖然,一些學者企圖從《聯合國憲章》中找到“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性依據,但是可以看到《聯合國憲章》也難以為“人道主義干涉”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依據,比如“人道主義干涉”的支持們援引《聯合國憲章》第42條:安理會如認為第41條所規定之辦法為不足或已經證明為不足時,得採取必要之陸海空軍事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括聯合國會員國之陸海空軍軍事演習、示威、封鎖及其其他軍事行動。但是很顯然,要動用武力必須先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批准。如果人道主義干涉在事前獲得了安理會的授權或批准,則其
 軍事演習
軍事演習結語
綜上所述,“人道主義干涉”的存在既不符合當性的要求,也沒有國際法上的合法性依據,在實中它往往成為西方大國藉以干涉他國內政,謀取治軍事戰略利益的一種手段,因此對“人道主義涉”大唱讚歌並企圖使其合法化的傾向的觀點是分錯誤的,而種種打著“保護人權”旗幟進行“人道義干涉”的行為,無論是對國際秩序的穩定,還是於被干涉國的利益,都是有著不小的負面影響的,並非對人道主義危機的合法與正當的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