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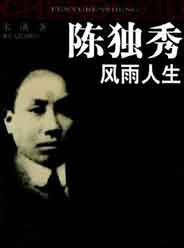 《陳獨秀風雨人生》
《陳獨秀風雨人生》這部30餘萬字的著作是朱洪教授撰寫的第六本有關陳獨秀的專著。本書既整合前幾本書的成果,又採用一些最新的共產國際的解密資料,對陳獨秀的考察更加全面。和以往的陳獨秀研究相比,關於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活動介紹,陳獨秀大革命後期的錯誤與共產國際的因果關係的分析,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走上托派道路的原因分析等,在這本書里,材料挖掘得更具體,背景揭示得更深刻。該書寫作手法上充滿濃烈的文學色彩,大大增強了可讀性。該書還附有150多幅珍貴歷史照片,及陳獨秀各個時期的書法作品。本書主要是寫陳獨秀生平,而一些歷史細節對更完整地認識陳獨秀,特別是更全面、深入、細緻地認識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所犯錯誤的具體過程。
作者簡介
朱洪,1957.3出生,安慶市人;1982.1畢業於安徽大學(安徽勞動大學);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安徽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安慶師範學院教授、皖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安慶市政協第十一屆委員、安慶市作協副主席。
背景資料
 作者朱洪
作者朱洪陳獨秀是共產黨的領袖和創始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他於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42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做《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時,肯定了陳獨秀:“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選出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陳獨秀從一個叱吒風雲的領袖,最後成為一個靠朋友接濟度日的平民,“何處漁歌驚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其人生很難用成功、失敗來總結。何謂成功,這本是一個哲學命題,本無標準答案,成功是過程,還是結果,是一時之成就還是永久之成果,沒人說得清。成功又不能用名利和地位來衡量,有的人看上去風光無限,內心卻充滿危機,有人碌碌無為,卻自得其樂。
從人生的歷程來看,有的人步步高升,日趨圓滿,可總逃不過生命的輪迴。陳獨秀則是另外一種人生,年少時就如飛龍在天,聲震中華,看過了人生最美好的風景,最後卻靠朋友接濟度日,悄然逝去。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已嘗盡,未嘗不是一種圓滿。
陳獨秀的最後歲月
陳獨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區30多里的石牆院。他坐了蔣介石的五年牢之後,因抗戰爆發而出獄。在暫住南京期間,蔣介石派陳立夫、陳果夫請他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還要求陳獨秀組織一個新共產黨,並供給十萬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五個名額,均遭陳獨秀拒絕。這時,老友胡適從美國寫信來力邀他去美國,說一家圖書公司請
他寫自傳,也被他婉言謝絕了。他認為,在國難當頭之際,跑到美國去寫自傳賺錢,拿共產黨人鮮血染紅的旗幟炫耀自己,那無異於褻瀆和背叛。此時他先後寄居傅斯年家和陳鍾凡家(陳是北大學生),靠朋友資助度日,後又拒絕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請求,乃偕夫人潘蘭珍赴武漢。在武漢期間,董必武曾受中共之託探望陳獨秀,爭取他到延安,並提出三個條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書面檢討,陳不同意,“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現在亂鬨鬨的時代,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麼過可悔?”他既拒絕了國民黨的高官厚祿,又拒絕作檢查才能前往延安,從此走向了茫然惆悵、窮困潦倒的漫長之路。1938年7月,陳獨秀從武漢輾轉長沙來到重慶,遇見同鄉、同學鄧季宣,經他又認識了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鄧蟾秋仰慕陳獨秀之名,邀請他來到江津縣,經過一番波折,最後定居於清朝拔貢楊魯丞家——石牆院。
說來湊巧。陳獨秀流落重慶期間,偶爾在地攤上發現了一本楊魯丞所著《皇清經解》抄本,很有興趣,出錢買下。到江津定居後,一次在某館喝茶時和鄧燮康提起此書,鄧告訴他,楊魯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陳獨秀說:“我花了兩天時間,反覆看了幾遍,寫得不錯,有價值。”鄧又告訴陳獨秀,當年號稱經史大家的章太炎來川時,楊魯丞曾把手稿拿去請教,章不欣賞他的作品,還批了“亂雜無章”幾個字,氣得楊魯丞沒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陳獨秀應邀答應為之整理,就這樣住進了石牆院。此時石牆院主人是楊魯丞後人楊明欽。陳獨秀住在大院平房右側一個小院,四間房子。陳獨秀之所以同意住進遠離江津、地處山坳的石牆院,除整理楊魯丞著作外,主要是為了有個安靜的落腳點,便於整理他在獄中就著手著作的《國小識字教本》。正如他入川後一首詩中所說:“除卻文章無嗜好”。《國小識字教本》,從字面上看容易誤解為一本粗淺的兒童識字課本,其實不然,它是擁有中西文化很高素養、特別是國學雄厚基礎、博古通今的陳獨秀最後一本學術力作,是總結我國幾千年和他幾十年來文字研究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我國歷來所謂“國小”,就是研究文字的學問。此書名為“教本”而非“課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這是有意為中國小教師普及國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學藍本,學術性雖高,但目的還是在於實用。此書完成後,稿件送審時,有關部門認為“國小”二字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兩萬元稿費退回去了。此時的陳獨秀已貧困交加、生活拮据,多么需要一筆錢度日,可他硬是退還這筆稿酬,這就是陳獨秀的性格。
陳獨秀落腳在石牆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饋贈,北大學生會是經常支持的,另方面靠賣文、賣字。他的詩、文、書法都屬一流。夫人潘蘭珍為生活所迫,避著陳獨秀典當了首飾,連柏文蔚(陳的老友、曾任安徽都督)贈給他的皮袍子也當了。為了補貼生活,在院牆後門外空地種過土豆。陳獨秀還被小偷光顧過。小偷可能以為很多名人來拜訪他,一定是個富戶,誰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物、《國小識字教本》手稿和印章“獨秀山民”。因陳獨秀始終是在國民黨特務監視下度日的,當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沒有追回,陳獨秀非常痛心。當友人前來安慰時,陳幽默地說:“這竊賊也真風雅啊!”石牆院為三進,中間以天井隔開,這天井大約200平米,青石鋪地,四周有雨槽,第三進正面是三間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陳獨秀就住在右側耳房。臥室是一間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開著半個“廳”,僅容一桌兩凳,是陳獨秀吃飯的地方,院的右側兩大間,大門有一大排隔柵,是陳獨秀寫作和會客的地方,小院中間有一個長方形花壇,中間有玉蘭一株,為陳獨秀所植。
陳獨秀住在石牆院,雖遠離城市,交通又不便,但前來拜訪的人絡繹不絕,有縣長和當地名紳,還有已做了大官的學界名人傅斯年、羅家倫。至於陳的老友高語罕、鄧仲純等安徽老鄉、北大同學,江津名流,就更多了。陳因坐過五年牢,到處奔波,生活不安定,此時年紀已大,心情又不好,吃飯早一頓晚一頓,熱一頓冷一頓,致患有胃病、高血壓、心臟病等。其間生病多由鄧仲純為他義務診治(鄧是留德醫生,在重慶開了一家延年醫院),其他醫生也為他義務治過病,有時則利用民間草方。1942年5月23日,曾代表陳獨秀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來探望陳獨秀(一說來探望的不是包,而是包的夫人夏松雲和張國燾夫人楊子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興,中午吃了四季豆燒肉,引起胃病復發,潘蘭珍延請好幾位醫生醫治無效。當陳獨秀生病臥床之際,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蘊山陪同下,探訪了陳獨秀。《成都晚報》吳塘的文章,對這次訪問有詳細記載:周恩來在朱蘊山陪同下,一走進石牆院,一股淒涼蕭索之氣向他襲來,不禁一陣心酸。走進房門,只見陳獨秀手捂著胃,停坐在一張木床上……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接著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陳獨秀費力地要支撐起來。周恩來走到床邊與陳獨秀握手,說:“獨秀先生,你就靠著,不要起來。”陳獨秀握著周恩來的手,心頭一陣潮湧,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湧上心頭。
周恩來此次拜訪,仍繼續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說:“李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來、毛澤東,黨中央沒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後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么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陳獨秀還是老脾氣,是直言不諱的。毛澤東始終不曾忘記過這位“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他再三講過,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斷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謠中傷陳獨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從日本人那裡拿300元津貼。
陳獨秀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向跟隨他多年的北大學生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後,喪事從簡,也不要登報。”並說:“小兒松年早已分居獨立(時在一中學任職),夫人家中無親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請你務必多多關照。並要囑夫人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自立,我在南京獄中,朋友贈我的五個顯德四年古瓷碗,留給蘭珍。後事料理後,稿費如有多餘,也留給她一部分……”話未說完,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與世長辭,時在1942年5月27日晚9時40分,享年63歲。當時除夫人潘蘭珍、三兒陳松年夫婦、孫女長璋、長瑜、侄孫長文等親屬外,尚有包惠僧、鄧仲純、何之瑜在側。陳獨秀去世後,衣裳、棺木與墓地等均由鄧蟾秋、鄧燮康贊助,社會各方多有支持,捐贈和賻儀總數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元,由北大同學會撥付。
陳獨秀靈柩於6月1日下午1時30分安葬於江津大西門外鼎山麓康莊,此地也是鄧蟾秋捐獻。出殯之日,陳獨秀親屬和雙後國小學生百餘人隨行送葬,從鶴山坪到康莊30里,兩旁站立許多人送葬,有人放鞭炮以示悼念。其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送葬隊伍正在肅穆中緩緩而行時,來了兩個陌生人找到鄧燮康加以盤問:“在這國難之秋,你帶頭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麼意思?”鄧反擊道:“我不管他是啥子黨,啥子派,一個愛國者客死於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為本地士紳,不忍看他陳屍於室!”陌生人厲聲質問道:“你們組織了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張旗鼓,是不是想再來一次小小的‘五四’運動?”鄧冷嘲道:“這么說來,你是害怕‘五四’運動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就躺在棺材裡,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吶喊了。而被“五四”運動啟蒙的中國竟然感覺不到他的死,沒有人高喊“陳君至堅聖高的精神萬歲”了。陳獨秀曾無奈地說過:“我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竟未能給貪官污吏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這正是陳獨秀一生的悲劇和憂思所在。同時,江津各界人士還在國立江津九中高三禮堂舉行陳獨秀簡樸肅穆的追悼會,參加者有安徽同鄉和本校學生,沒有花圈,沒有鮮花,沒有青松和翠柏,只有陳獨秀遺像放置在禮堂主席台桌子上,兩邊擺著幾副紙書的輓聯,其中三副:
其一:縱浪人間四十年,我知我罪兩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論,毀譽寧憑眾口傳。
其二:伊人去兮事跡猶存,人生功過自有評述。
其三:言皆斷制,行絕詭隨。橫覽九州,公真健者!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65年過去了,陳獨秀一生的是非功過應該更清楚了。
潘蘭珍在友人幫助下,在重慶附近一家私人農場找到一份工作。四年以後,她又回到上海,從原籍南通老家接回寄養在友人家中的養女小鳳共同生活,不幸患了子宮癌,於1949年11月去世。
圖書目錄
第一章皖城名士(1879.10-1901秋)
一不成龍就成蛇
二高曉嵐
三江南鄉試
四關東遭喪亂
第二章天生的領袖(1901秋-1908冬)
一青年勵志社
二藏書樓演說
三國民既風偃
四安徽俗話報
五吳越犧牲
六岳王會
七陳同甫再世
第三章老革命黨人(1908冬-1915夏)
一述哀
二高君曼
三勝友連翩六七人
四都督府秘書長
五蕪湖遇險
六恨不得食其人
七汝南晨雞
第四章新青年(1915夏-1920.1)
一若舟車之有兩輪
二春日載陽
三中國文學界的雷聲
四品學兼優
五尋找友軍
六同人刊物
七不屑與辯
八成績品
九初見毛澤東
……
第五章創立共產黨(1920.1-1923.1)
第六章全力支持國民黨(1923.1-1926.3)
第七章大革命的失敗(1926.3-1927.7)
第八章走向反對派(1927.7-1932.10)
第九章金陵獄中(1932.1-1937.8)
第十章晚年(1937.8-1942.5)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