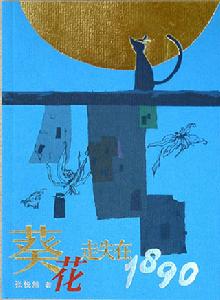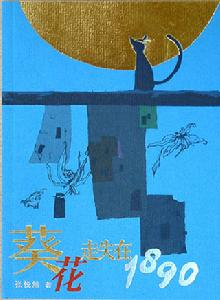 《葵花走失在1890》
《葵花走失在1890》《葵花走失在1890》由作家出版社重點推出,在封面和裝幀設計上都別出心裁,並配有多幅妙趣橫生而寓意深遠的插圖。著名作家莫言為該書作序,對這位文壇新人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一本從形式到內容都十分新穎獨特,極富視覺和心靈衝擊力的新書。
作品資料
類別:都市生活
類型:青春校園
作者:張悅然
出版:作家出版社
全文長度:85829字
作品特點
中國最具才情的年輕女作家張悅然的第一部小說集。收錄在中國青年讀者中產生廣泛影響的《陶之隕》、《黑貓不睡》、《葵花走失在1890》等短篇作品。寫過《紅高粱》的中國著名作家莫言先生為其作序,稱其小說有著“飛揚的想像和透明的憂傷”,“超凡拔俗而又高貴華麗”。作品出版後,掀起中國青少年讀者更換ID名的熱潮。網路上出現很多以其優雅而具獨特氣質的小說名命名的ID。
作者介紹
 張悅然
張悅然作品目錄
序 飛揚的想像與透明的憂傷毀 (1)
毀 (2)
黑貓不睡 (1)
黑貓不睡 (2)
黑貓不睡 (3)
黑貓不睡 (4)
白白
這些那些 (1)
這些那些 (2)
這些那些 (3)
這些那些 (4)
這些那些 (5)
霓路 (1)
霓路 (2)
霓路 (3)
霓路 (4)
霓路 (5)
霓路 (6)
霓路 (7)
霓路 (8)
桃花救贖 (1)
桃花救贖 (2)
桃花救贖 (3)
心愛 (1)
心愛 (2)
心愛 (3)
心愛 (4)
葵花走失在1890 (1)
葵花走失在1890 (2)
葵花走失在1890 (3)
葵花走失在1890 (4)
葵花走失在1890 (5)
葵花走失在1890 (6)
作品欣賞
 《葵花走失在1890》插畫版
《葵花走失在1890》插畫版那個荷蘭男人的眼睛裡有火。橙色的瞳孔。一些洶湧的火光。我親眼看到他的眼瞳吞沒了我。我覺得身軀虛無。消失在他的眼睛裡。那是一口火山溫度的井。杏色的井水漾滿了疼痛,圍繞著我。
他們說那叫做眼淚。是那個男人的眼淚。我看著它們。好奇地伸出手臂去觸摸。突然火光四射。杏色的水注入我的身體。和血液打架。一群天使在我的身上經過。飛快地踐踏過去。他們要我疼著說感謝。我倒在那裡,懇求他們告訴我那個男人的名字。
就這樣,我的青春被點燃了。
你知道嗎,我愛上那個眼瞳里有火的男人了。
他們說那團火是我。那是我的樣子。他在凝視我的時候把我畫在了眼睛裡。我喜歡自己的樣子。像我在很多黃昏看到的西邊天空上的太陽的樣子。那是我們的皈依。我相信他們的話,因為那個男人的確是個畫家。
可是真糟糕,我愛上了那個男人。
我從前也愛過前面山坡上的那棵榛樹,我還愛過早春的時候在我頭頂上釀造小雨的那塊雲彩。可是這一次不同,我愛的是一個男人。
我們沒有過什麼。他只是在很多個夕陽無比華麗的黃昏來。來到我的跟前。帶著畫板和不合季節的憂傷。帶著他眼睛裡的我。他坐下來。我們面對面。他開始畫我。其間太陽落掉了,幾隻鳥在我喜歡過的榛樹上打架。一些粉白的花瓣離別在潭水裡,啪啦啪啦。可是我們都沒有動。我們仍舊面對著面。我覺得我被他眼睛裡的鏇渦吞噬了。
我斜了一下眼睛看到自己頭重腳輕的影子。我很難過。它使我知道我仍舊是沒有走進他的眼睛的。我仍舊在原地。沒有離開分毫。他不能帶走我。他畫完了。他站起來,燒焦的棕樹葉味道的晚風繚繞在周際。是啊是啊,我們之間有輕浮的風,看熱鬧的鳥。他們說我的臉紅了。
然後他走掉了。身子背過去。啪。我覺得所有的燈都黑了。因為我看不到他的眼瞳了。我看不到那杏色水的波紋和灼灼的光輝。光和熱夭折在我和他之間的距離。掐死了我眺望的視線。我看見了月亮嘲笑的微光企圖照亮我比例不調的影子。我知道她想提醒我,我是走不掉的。我知道。我固定在這裡。
男人走了。可是我站在原地,並且愛上了他。我旁邊的朋友提醒我要昂起頭。他堅持讓我凝視微微發白的東方。昂著頭,帶著層雲狀微笑。那是我原本的形象。我環視,這是我的家園。我被固定的家園。像一枚琥珀。炫目的美麗,可是一切固定了,粘合了。我在剔透里窒息。我側目看到我的姐姐和朋友。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影子很可笑,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不能夠跳動的,走路和蹲下也做不到。
他們僅僅是幾株葵花而已。植物的頭顱和身軀,每天膜拜太陽。
我也是。葵花而已。
可是我愛上一個男人了你知道嗎。
作品評價
 張悅然是深受青少年喜愛的作家
張悅然是深受青少年喜愛的作家她的很多小說都表現了一個共同的主題:“成長就是一場疼痛”,她描寫了青少年們圍繞著“這場疼痛”所做的掙扎和妥協,所感到的歡愉和憂傷,以及對愛情親情友情的細微體會。正如莫言在該書序言中所說:“張悅然小說的價值在於:記錄了敏感而憂傷的少年們的心理成長軌跡,透射出與這個年齡的心理極為相稱的真實。他們喜歡什麼、厭惡什麼、嚮往什麼、抵制什麼,這些都能在她的小說中找到答案”。
張悅然的作品還以其細緻入微的細節、豐富新奇的意象以及淒婉動人的文筆打動著眾多讀者。她的小說中運用了很多表現力極強的細節,恰到好處地表現了人物的心理,營造出獨特的情感氛圍。她的小說還創造出很多新奇的意象,寓意豐富而深遠,諸如教堂、黑貓等等,令人回味無窮。
最為人們所稱道的是張悅然極富獨創個性的小說語言。她的小說語言整體上帶有一種淒婉動人的風格,多以短句子見長,句子之間時間和空間的轉換移動往往具有跳躍性,給人以極強的畫面感,加上充溢作品中的詩一樣的韻味,這一切都使她的小說產生出如詩如畫的藝術效果。很多讀者認為張悅然的文筆酷似法國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
張悅然於2001年遠赴新加坡學習,她的視野更加開闊,她的心靈也在經受著來自新環境的撞擊,因而她的創作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在她近期的作品裡充滿了異國情調和留學生的迷惘情緒,為她的作品增添了新的藝術感染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80年代新生代青春派作家正在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這些作家正以自己更加敏感、細緻、深刻的藝術感覺觸摸現實,寫出了與70年代作家相比明顯不同的作品,表現的正是他們這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存環境和心靈困惑。這是他們深受廣大青少年讀者群體喜愛的重要原因。作為80年代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張悅然一直在堅持不懈地進行著自己的探索,在小說創作中作了多方面的嘗試,從《葵花走失在1890》一書中,人們都可以看出她的探索、嘗試的軌跡。(文:劉 立)
 張悅然的作品風格別致
張悅然的作品風格別致《葵花走失在1890》是個標誌,讓我們看到這個耽於夢幻、沉浸在五顏六色奇想中的小作者,已從強烈的個人化情懷中跳了出來,在走向文化思考,在走向大境界。“我”的愛情所迷戀的對象也已從前衛時尚的少年,走向偏執的、極富個性色彩的成人,這是作者心力所及的範圍已有所拓展的表征。這是一個新變化,無疑也是一個新的寫作方向。不難看到,張悅然在這個方向上給自己留下的發展空間和開拓另外的發展空間的可能性。(莫言)
張悅然的小說主要是寫親情、友情和愛情。她筆下的愛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靈放飛出去的一隻只飄搖而空懸的風箏。愛情成為夢想的惟一附依。這樣的夢想在張悅然的小說中頑強而專注。比如《黑貓不睡》中“我”的“拒絕”、《毀》中天使的堅守、《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我”的獻身,等等。一個固執懷抱夢想的人必然同時也就懷抱了憂傷,因為現實要泯滅夢想,阻絆它們去飛。因而那些臆想中的愛情,開端都很美妙,發展都很艱辛,結局都很悲慘。
無論是離別、破碎還是死亡,這都絕非空穴來風,是她們感知到的部分現實。她們可以丟掉夢想嗎?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謬正在這裡:她們的夢幻大多是悲劇。張悅然的筆之所以反覆觸及到了種種的“愛情悲劇性存在”,因為夢幻和現實之間存在著永恆的巨大落差,這帶給愛幻想的她們濃濃的悲劇感。作者從小就在她的小說中透射出了這種悲劇意識,這很不簡單。
悲劇意識的確立,如人所言,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清醒,是社會整體樂觀情緒的必要補充。相對於社會整體性的樂觀情緒,這種悲觀無疑是重要而又必須的。而我們也吃驚地發現:張悅然的小說大都是悲劇。刀子一樣鋒利的語言,珠貝一樣閃閃發光的思想,她用小說來建設高於現實的生活,並向這種生活伸出豐富而茂密的心靈觸鬚,她的作品充滿了凌越現實的巨大衝動和使人警醒的批判力量。當然,在現實生活中,在別人眼裡,她可能生活得很好很貴族。但我們會聽到她斬釘截鐵地反駁說:我非悲劇,而悲劇永在我心中!(莫言)
作者影響
 張悅然的作品在青少年中有很大影響力
張悅然的作品在青少年中有很大影響力成功來自她的才情和不懈努力。當然,她的作品也有局限,比如她在小說中過於沉湎於自我,這使她的小說顯得很緊縮;她的抒情是“敞開式”的,往往顯得缺乏克制,等等。偉大的文學,從不單純停留在夢幻的層面上,它要涵蓋歷史,涵蓋廣闊的現實與責任,涵蓋瑣碎、艱難而具體的現實人生。
張悅然的寫作剛剛起步,已經取得了如此的佳績,憑藉她極具個性的語言和想像力,隨著她人生閱歷的不斷增加和對社會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我相信她會更好地處理夢境與現實的關係,更好地處理個體經驗和社會性經驗的關係,寫出既有鮮明的個性又有廣泛的涵蓋性的作品。
相關訪談
記者:你在新書《十愛》的自序中提到,這十篇小說會比你從前的短篇小說更加激烈,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平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張悅然:這是由我的寫作偏好所決定的,我喜歡比較極致的寫作狀態,這樣會感覺寫得過癮。像《葵花走失在1890》(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中那種淡淡的憂傷已經不能夠滿足我的寫作深度了,而我所理解的寫作深度,就是要讓自己的文字在讀者心中留下痕跡。
 張悅然的另外作品
張悅然的另外作品記者:看了你的《十愛》,感覺書中文字的成熟以及對感情的領悟遠遠超出了你的年齡,是什麼因素促使你的文字感覺以及對感情的認識如此成熟呢?
張悅然:我的這種成熟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從我開始寫作進入文壇,到去新加坡讀書,後來出版這幾本書,這些經歷令我飛速成長。所以我的這種成熟是這幾年的經歷決定的,甚至是被迫的。
記者:同你以前的小說相比,《十愛》里《豎琴,白骨精》、《宿水城的鬼事》等作品充滿了迷幻的超現實味道,從寫作題材到文字表達方式上已經褪去了青春文學的青澀,這種變化對你而言是自然而然還是有意為之?
張悅然:我在以往的小說中關注的其實並非校園生活,而是人的內心世界,是自由的生命狀態。《十愛》中這幾篇超現實題材的作品,誕生得特別自然,比如《宿水城的鬼事》,是源於我聽一個朋友給我講《山海經》里的傳說,這個傳說很短,幾乎沒有結尾,給人以很大的想像空間,於是我就順著這個傳說的思路演繹下去,完成了這篇小說。《豎琴,白骨精》則給人以安徒生童話《海的女兒》的感覺,是個關於愛與付出的故事。
記者:從14歲開始寫作,進而獲得“新概念”一等獎,直到今天成為年輕的女作家,你的文學之路似乎一帆風順,你自己如何理解成功的含義呢?
 張悅然曾被譽為“玉女作家”
張悅然曾被譽為“玉女作家”談到成功的含義,我非常認可父母對我出書的理解。媽媽曾經希望我能成為一個規矩體面的白領麗人,父母完全沒有想到我後來會走上出書、當作家的道路。他們對我從事寫作的關懷和期望只是基於一個原因:希望我這個在國外很寂寞的孩子能開心,是心愿的了結,而不是寫作的開始。
記者:時至今日,上個世紀8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經在文壇正式登場,成功也不再是個別現象,做為80後作家群的一員,你如何評價這一代作家?
張悅然:我們這一代作家跟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我們對外界似乎很少關心,更多的是關心自己的內心世界,更自我。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更喜歡面對外部世界來進行批判和懷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是獨生子女,我們的童年比較孤獨,因此有更強烈的傾訴欲和表達欲,一堆冷漠的玩具永遠都代替不了共同成長的兄弟姐妹。我們會格外地想說,想表達。80後的作家在狀態上會更加地分散,各寫各的,而70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會形成一個個群體。
記者:許多讀者和評論都認為,80後作家的寫作,市場意義要大於文學意義,成功很難延續和堅守,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張悅然:每個人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每一屆“新概念作文大賽”都會產生獲獎者,他們可以因此獲得比較好的物質條件和發展機會,可是並不一定所有的獲獎者都要走上文學道路,都以文為生,等待他們的其實有更廣闊的發展道路。“新概念作文大賽”已經舉行這么多屆,獲獎者一直堅持寫作、陸續出書的也不過就只有我和韓寒、郭敬明幾個。這種選擇與每個人的性格、對文學的理解都有關係。
我自己對文學創作也有過許多懷疑,擔心自己不能一直走下去,懷疑自己是否能夠以文學為職業。中間曾多次考慮放棄,可是我太喜歡寫作了,所以還是寫到了今天。所幸隨著作品的不斷出版,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讀者認可,無形當中也給我很多繼續寫下去的信心。
 讀者評價張悅然的作品細膩
讀者評價張悅然的作品細膩張悅然:《十愛》一書的責任編輯對我的寫作有個比喻,她說我是一個不會貼著地面走路的人,總是走著走著就飛了起來。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也想寫貼近這個時代的作品,然而後來我失去了寫這些的興趣,於是筆下的世界就越來越超越現實生活。文學創作的現實是,再複雜離奇的故事也都被寫過了,關鍵是看你怎么來講這個故事,細節如何表現,所謂新瓶裝舊酒,把平凡的素材變成一個嶄新的故事,這樣的寫作同樣可以非常精彩。
記者:你已經擁有眾多讀者,同時你的作品給人以極其自我,極其個性化的感覺,你在寫作的時候會考慮讀者的閱讀期望嗎?
張悅然:既然我知道有那么多讀者的存在,當然不可能完全不考慮讀者,這些考慮會給我帶來很多寫作壓力。可畢竟每個讀者的閱讀需求都不相同,他們對我的期望也不一樣,每個讀者對我的關注點也不一樣。所以很難兼顧所有人的願望,與其迎合一部分讀者,不如索性完全放開寫,順其自然。我會關注大家都關注的題材,這不是迎合,更應該是共鳴。
記者:說說對你寫作影響比較大的作家、作品吧?
張悅然:我覺得作家有兩類,一類作家的作品非常優秀,卻並不能夠深深地打動我,這是因為他和我的經歷相去甚遠。這些作品總是非常冷靜,站在高處俯視眾生,比如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另外一類作家或許作品並不完美,或許從未被那么多的讀者關注,卻格外的打動我,因為她的作品中有我特別關注或感同身受的成分,比如林白,我對她的作品相當熟悉,她的文字有非常強烈的畫面感,作品中有許多夢幻般的超現實場景,她的這種“女性寫作”說出了好多女性感受。我讀了林白去年的新書《萬物花開》,受到這本書很大的影響,寫了一篇小說,近期會發表在《上海文學》上。我非常喜歡這本書,在書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轉變,並且理解這種轉變,為此欣慰。
其他作品
 張悅然的其他作品
張悅然的其他作品《是你來檢閱我的憂傷了嗎》 2004年5月 上海譯文出版社
《紅鞋》 2004年7月 上海譯文出版社
《水仙已乘鯉魚去》 2005年1月 作家出版社
聯繫信息
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個人部落格:http://blog.sina.com.cn/adore
官方網站: http://www.underthepink.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