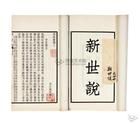基本資料
 《新世說》
《新世說》書名:新世說(筆跡雜文)
ISBN:7-308-04843-8/I·175
作者:陸春祥相關圖書
裝訂:平裝
印次:1-1開本:小16開
字數:254千字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頁數:307頁
出版日期:2006-08-18
內容簡介:
書名與內文章節借用了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而得。全書分為九個部分。作者就其所見展開討論,觀點犀利,文筆清新,語言詼諧,具有出版價值,特別是書中所配的漫畫,與內文相得益彰,集思想性、趣味性於一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陸春祥:資深雜文隨筆專欄作家,大學兼職教授。作者簡介:
陸春祥:筆名陸布衣、陸天等,新聞學研究生,做過教師,辦過報紙,現供職於杭州日報。系浙江省作協會員、浙江省雜文學會常務理事。八十年代開始寫作,單獨和合作出版語文類著作《中國語文系列表》、《語文開眼界》兩種。近年業餘主要從事雜文隨筆寫作,已出雜文集《用肚皮思考》、《魚找腳踏車》、《41℃胡話》等。有不少作品被新浪等網站及《雜文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轉載並獲獎。
陸春祥的雜文理念:
舌上生蓮固然好,因為頌言會使人醉,但現實卻有不少和我們的理想格格不入的破事爛事及惡少莠官,我們需要燭察;對不良行為的詛咒是為了懲罰我們屈從誘惑的原罪,但用一些機智的手法往往更顯效果,幾年堅持的“實驗雜文”就是這樣的努力。
精彩段落
“枕流”雜文可“漱石”——《新世說》序
陸布衣的雜文是比較好玩的。若干年前,我與陸春祥等四人聯手在某報開出“舉手發言”的專欄,皆以“布衣”為名,前頭一字不同,以示區別,於是陸春祥成了“陸布衣”,我則取了“凡布衣”,我們這是“和而不同”;我也至今還在用這個筆名,“用並滿意著”。陸布衣陸春祥的雜文集子出到第4本了,這些雜文看看書名就知道好玩:《用肚皮思考》、《魚找腳踏車》、《41℃胡話》,再就是這裡的《新世說》。我最欣賞的是那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實驗雜文《41℃胡話》,那裡是篇篇形體求異;而最新結集的這本筆記雜文《新世說》,則是全書結構出新。《世說新語》的結構模式用於雜文集,這是初見,有意思的。
陸布衣寫雜文出集子,向來愛創新出新。他說他很多年前就打算採用《世說新語》的結構模式推出一本雜文。學者余世存在《非常道》一書中已率先用上了,於是類似的書本連著出了不少,銷路似乎都不壞,看來讀者挺喜歡;其實腦筋靈動的陸布衣想在他們前頭,而且《非常道》這些書類似讀書卡片,敘而不議,段而不篇,離雜文有點遠的。所以這本《新世說》之“新”之“說”,名副其實;而且亦莊亦諧,綿里藏針,這針當然是中醫里的銀針。
因了“蓄意求新”,陸布衣的雜文就從“枕石漱流”的常態跳離,成就了“枕流漱石”的意象,而且是“枕流”雜文可“漱石”。《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小小的“乾坤顛倒”,就成就了有口皆碑的語詞,看似神妙天成,而陸布衣的雜文常有這樣的形態。今日來看“枕流漱石”,遠非“隱逸風流”了;從枕流洗耳,到漱石礪齒,不正是雜文人所最需要的嗎?而且,好的雜文本身就是讀者的礪齒之石。
陸布衣這個集子裡的多數雜文,在原初發表時我就讀過,從篇名到內涵都印象深刻,譬如《范長江是小品演員?》、《墓碑上取款》、《發現了一個找錢網站》、《名著是這樣“譯”成的?》、《被中介了的名人》、《雍正賜我兩眼鏡》等等,這些篇什讀來饒有興味,作者的深切感受就深切地切入讀者心中。陸布衣的雜文從來不故作高深,這就是一種公民寫作。或許,當初所取的“布衣”筆名,也佐證了公民寫作的姿態、百姓表達的風格。雜文作為一種公民寫作,它說出的是真話,它追求的是真理。這讓我想起哈佛大學的校訓:“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而總統哲學家哈維爾則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好的雜文,就“在真話中生活”,就“生活在真話中”,擔承了那天賦之責。
這些年來,我認為雜文的收成並不壞,因為有大批像陸布衣這樣的雜文人在孜孜以求中“手寫我心”說著真話;只是今日資訊已發達得讓人焦慮,許多好雜文成了掩映在花木之下的石頭不為人所知罷了。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的雜文大家鄢烈山先生說,“我不贊成襲用匕首投槍這類暴力喻體,以為用治病救人的銀針手術刀比雜文更合適”,我很贊同鄢先生的這一說法。可以想見的是,雜文不作為量少的“匕首投槍”而作為量大的“銀針手術刀”出現,收成就不會太薄。鄢烈山先生這樣答記者“現在雜文式微,它的前景在哪裡”的問題:“雜文式微了嗎?全國現在據說有十多種雜文刊物,吉林的《雜文選刊》每期發行20多萬冊。雜文網站也不少。有些簡訊笑話其實也是雜文的一種,即諷刺小品。今後可能有兩種樣式的雜文比現在繁榮:一是嬉笑怒罵的雜文體時評;二是余光中、董橋那種知識性、文學性強而心態從容的雜文。”我同樣也不贊成“雜文式微論”,更反對一種奇怪的“雜文大小年”論。雜文發展挺正常的,除了鄢先生所說的這兩種樣式的雜文之外,如今還有一種網文式雜文已然興起。而陸布衣的許多雜文,兼有了時評、網文和狹義雜文之所長,無論是“實驗文體”也好,還是“新世說”也好,都以奇葩的姿態繁榮了這個園地。
過去在《雜文報》上較多地看到陸布衣的這類雜文,遺憾的是近來少了,其中似乎隱藏著這樣一個問題:恰恰是《雜文報》刊登有雜文味的雜文越來越少,好看好玩的雜文影蹤難覓,版面類別儘管很多,但篇章卻不再是雜文而是時評,“雜文報”成了“時評報”。我這個“凡布衣”與陸布衣一樣,在時評之外也常常寫些很雜的雜文,但偏偏是“雜文”上不了《雜文報》,用出的多為時評;還好,像《雜文選刊》這樣的雜誌還能意識清晰地堅守著雜文、呵護著作者——這裡的“雜文”當然是“大雜文”的概念。不久前我給《雜文報》編輯發了個電子郵件,就一句話,“《雜文報》應該專門開設一個雜文版”,就是希望《雜文報》能夠一定程度上回歸雜文,儘管有位編輯在編者按語裡提到了我的這個“很雜文”的建議,但想一下子有大的改觀看來也不大可能。
雜文遠離了生活、只是去貼近新聞,確是待解的問題。真正的雜文家應該是敏感之人,善於在生活感受中發現陣地和真諦。本書中的“布衣雜文”《發現了一個找錢網站》、《范長江是小品演員?》等等,就來源於生活,這些篇章那么鮮活,這與現在一窩蜂式的時評確有很大不同。生活本來就是雜文寫作的源泉,只是現在作者們越來越“沒生活”、“不生活”了。一位從空軍飛行員“改行”過來的雜文家,最近說到自己早年首篇雜文的誕生過程,蠻讓我感慨的。作者那時壓根兒就不曉得什麼是“雜文”,而那素材恰恰是來自生活的絕佳雜文題材:五四青年節,作者所在部隊與城裡紡織廠女工聯歡,政委在冗長的講話之後宣布舞會紀律:“男的和男的跳,女的和女的跳”,於是舞會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精神折磨,大家都盼著快點結束……許多好的雜文,不是雜文家“寫”出來的,而是非雜文家從心裡流出來的,今日許多署名為“佚名”的絕佳網文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我們這些已經被冠以雜文家名頭的人得努力,否則可能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
說到今日網友跟帖評論式的網文,我以為可把90多年前的雜文短章《殺》視為“鼻祖”。只有24個字的《殺》,刊於1912年5月20日上海的《民權報》:“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作者是年僅23歲的戴天仇,戴天仇後來以戴季陶之名為世人所知,有許多犀利雜文面世。這個24字之評論,甚像今日網友之跟帖,可謂網文網語之先祖;它簡潔明了,熱血沸騰,排炮連擊,氣勢如山,充滿膽氣骨氣之張力,飽含捨我其誰之氣概。現已不大可能在平面媒體上看到這樣的匕首式雜文了,雜文報刊大約也難以刊出這樣的“投槍”,好在今日網路陣地比較巨大。從正統的雜文到好玩的網文,是一種流變嬗變;真正的雜文無論怎么變,它的精髓是不會變的,那就是風骨挺拔、識見獨到、文采粲然。我觀陸布衣之雜文,就是在變與不變中追求著。
當然,陸布衣雜文中有的觀點,我也不甚同意,比如《討厭厚報時代》。我與陸布衣同在報社幹活,同樣“厚報天天讀”。陸布衣說:“我每天必須要看的報紙論版數算至少在300百版以上,多的時候甚至超過500版。痛苦啊。”其實我們這是“工作看報”,看的是多份報紙;而一般讀者哪裡可能看這么多同質的報紙呢,他們通常只擁有一份“厚報”,多幾版並不痛苦,他們屬於“生活看報”,若有版面不喜歡看就不看,不見得會討厭厚報;所以,一個“工作看報”的人“討厭厚報”之感受,對於廣大“生活看報”者來說,就太“狹義”了。於是我想,雜文家需要多一點換位之思、為他之想。我這樣說不是想批評雜文家陸布衣同志,而是要引出哲人維根斯坦的話:“世界不是事物的總和,而是事實的總和。”作為認知意義的“事物”總是有限的,它不是整個世界,雜文也不例外。(《新世說》,陸春祥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
民國筆記小說(2)
| 民國筆記小說以鹹、同、光、宣四朝之事居多,凡朝廷、社會、京師、外省事無大小,皆據所聞所見錄之,不為鑿空之談,不作理想之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