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
I S B N :7505945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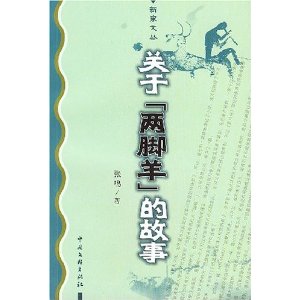 張鳴《關於兩腳羊的故事》
張鳴《關於兩腳羊的故事》作 者:張鳴
出 版 社:中國文聯
出版時間:2004-04-01
版 次:初版
開 本:大32開
內容簡介
《關於“兩腳羊”的故事》是一本隨筆集,這些隨筆作品對歷史進行了解讀,讓人們在幽默詼諧的敘述中,體味過去歲月對於現實社會揮之不去的前提性和背景負擔。
媒體推薦
書評
寫在前面的話
記得剛會看書的時候(可能是9歲左右),我最大的理想是長大以後做一個圖書館的管理員,也好隨便而且天天地看書,因為在我小時候,我們那兒的圖書管理員可以一天天地坐在那裡沒事幹,所有的書都可供他們自由地支配。那時的我有點自閉,說活口吃,很不願意跟人交流,所以,就是從當時的情景來看,做圖書管理員的確是最合適於我的職業了。
中學畢業因為犯了當時的忌,遭到批判,圖書管理員這樣的活自然輪不到我,因為那是個輕鬆的好活,於是被發配下去放豬。剛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我其實是有點高興的,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不跟或者少跟人打交道了。當時不僅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做夢也想不到最終我會做教師,然而,後來的後來,我真的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一個教書匠,而且一千就是幾十年。
在大學裡做教書匠往往被人稱為學者,但南郭先生其實也不少,我自己算不算學者,其實我自己並不是很清楚,有的時候像,有的時候又不太像。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個職業是個能說活的職業,上課可以說,下了課也可以說,還可以變成鉛字發表,讓更多的人看你想說的話。一個人看了些書,想了些事情,當然難免有話要講,活了若干年紀,經歷了若干事情,當然也難免有話要講,做教書匠的好處就是,當你有話要說的時候,有地方讓你說。
我現在的職業比起小時候想做的圖書管理員來,面上光了許多,人前人後,人家都尊你為教授什麼的。據某些社會學家的統計,這種職業的社會聲望還排在前幾位,國家和學校都在不時地往大學教師群里散點鈔票,當年勞體倒掛的牢騷,不知不覺就丟到爪哇國去了。可是,現在的教授,讀書的時間卻少了,至少比某些圖書管理員還少,然而文章卻多了很多,真不知道國家和學校花這么多錢和精力,催出這么多說不清寫了什麼,也沒有人看的文章乾什麼。從小,大人就教育我,做什麼都要對得起付你工資的人;這么多年,我也總是把這話轉給我的學生。我們這些做教師的,一不種地,二不做工,三不參加管理,做點研究,當然要研究點真問題水平實在不高的話,至少要說點實話、真話,也好對得起自己的飯碗,對得起納稅人的錢。
下面的文字,都是近年發表在《讀書》、《書城》、《隨筆》等雜誌上的一些隨筆,屬於隨時有話想說就說出來的零散玩意,攏在一起,算是對自己的一個小結。
作者簡介
張鳴,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長在北大荒,做過農工、獸醫。後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做個教書匠。在教書之餘喜歡寫點東西,發表論文、學術隨筆百餘篇。另著有《武夫治國夢》、《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變遷》等小說,有朋友將部分發表在讀書上的隨筆結集,名為《直截了當的獨白》。
目錄
寫在前面的話
讀史況彈
財富,模糊的邊界
“省官不如省事”
——教議王妥石變法的歷史教訓
有關八國聯軍與中國妓女的一點亂彈
關於辮於與革命的零碎故事
舊醫,還是中醫?
——七十年前的廢止中醫風波
“歷史另一面”的困惑
永樂皇帝的功德箱
也談“黃宗定律”
難以解開的“中國結”
教育改革視野下的鄉村世界
——由“新政”談起
映在一個普通人歷史裡的肘代
——一份50年前的入黨志願書的解讀
五十七年前的學生檔案
馬賽街頭的“革命舞者”
“綢人”的膈膜與歷艾的迷霧
關於“兩腳羊”的故事
鄉下人的革命性
“行政分權”話古今
隨感塗鴉
來自於傳統世界的NGO
——平江廟會、路公紐織的走馬觀花
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冶”
其實浪漫不起來
——答姚洋先生
當前鄉村治理結構的隨想
紅色“桃花源”的解瀆
——讀項繼權先生新作《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的隨感
衙門了+大學公司化=洋務企業
——高等教育丈躍進語境下行大學改車
讀者書與教老書
——平江私塾私訪雜記
鄉村冶理與擺平和擺平術
“義和團藥方”為何再現江湖?
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
——刑訊逼供的西個傳統今日談
另一種的信用危機
旅人文蹤
補白的補白
祭壇的殘垣
……
文摘
書摘
舊醫,還是中醫?
——七十年前的廢止中醫風波
在今天的中國甚至世界,恐怕不會有什麼人提出要廢止中醫,如果真的有人說這樣的話,那么大家即使不認為他是精神病,也只當是酒後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國,這樣的議論卻是家常便飯,時常在報刊上露面。一千“五四”精英類似的鼓譟,了解那段歷史的人,肯定有所耳聞;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點魯迅的,從他對中醫那深惡痛絕的態度,大概可以推測,在那個時代,中醫在這些精英眼裡是個什麼形象。不過,連我這個學近現代思想史專業的人,也決沒有想到,在“五四”過去十年的時候,這種廢止中醫的書生議論,居然被剛剛獲得政權的國民政府打算付諸實行,從而惹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亂子。
在1928—1929年間,剛剛定鼎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其實並不完全像我們的黨史和現代史教科書說的那樣,喪盡人心,分崩離析。至少中產階級和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對之還是充滿期待的,而這個政府也是蠻想有所作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為,依然像當年火燒趙家樓的學生小子一樣,未免有幾分毛手毛腳,廢止中醫之舉就是一例。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衛生部主持召開了一次“全國中央衛生會議”,名日全國會議,實際上參加者只限於各個通商大埠的醫院(西醫)的院長、著名醫生和少量的衛生行政人員。在1929年那個時候,中國的西醫比起“大清國”那陣來,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雖說內部派系紛亂,跟英國人學的叫英醫、德國的叫德醫、義大利的叫意(義)醫,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對付起中醫來,卻是同仇敵愾,換言之,中西醫之間的敵意甚深。在這樣的氣氛下,由清一色的西醫人士參加的中央衛生會議自然對中醫沒什麼好臉色,會上廢止中醫的呼聲甚囂塵上,結果是通過了一個“舊醫登記案”,規定所有未滿50歲從業未滿20年的舊醫(中醫)從業者,均須經衛生部門重新登記,接受補充教育,考核合格,由衛生部門給予執照,方才準許營業。而50歲以上的中醫,營業對象也有限制,且不許宣傳中醫,不許開設中醫學校。
在這裡,有四個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兩個是論戰雙方的主角,一個叫余岩,字雲岫,系當時有名的西醫,有過留日的經歷,1916年畢業於日本大阪醫科大學,回國後擔任過上海醫師公會會長,在國民政府里也有職務,曾經著書反對中醫,舊醫登記案就是他提出的。一個叫陳存仁,系當時上海的有名中醫,著名的《中國藥學大辭典》的編撰者。還有一個是幫腔的,名叫褚民誼,此公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曾經留學日本和法國,系政界學界與商界的活躍人士,時兼上海醫師公會(專屬西醫)監察委員,據說是此次會議的推動者之一,此公後來人了汪精衛的幕中一併做了漢奸,所以後來陳存仁將賬都算在了他的頭上。最後一位要算當時的衛生部長薛篤弼,此公系馮玉祥夾袋中的人物,於西醫中醫概無所知,僅僅由於北伐後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四家分肥,馮分得衛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長。他雖然也算是新學堂出身,比起前兩位來,卻土多了,不過,此公雖土,號稱於中西醫兩不相袒,但從他事件前後的言論看,屁股卻明顯地坐在了西醫或者說科學一邊。
在中西醫勢同水火的情勢下,由西醫主導的衛生部門來考核登記中醫,結果不問可知。事實上等於斷了50歲以下中醫的命脈,砸了他們的飯碗,而且,議案行文,;很明確地提出要廢
止中醫,登記只是一種廢止的過渡辦法。故而此議一出,舉國岐黃之徒為之譁然。於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風的上海中醫挑頭,全國中醫界發起了一場頗有聲勢的請願抗議活動。一時間,
滬上報館中西醫互打筆仗,南京政府機關中醫請願、請飯、遊說軍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學各界添亂式的兩下聲援,真是鬧煞了國人,喜壞了報人(報紙銷路大增)。結果是舊醫登記案不再執行,大家不了了之,中醫照舊把脈,而民(醫)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著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來,大家一起去關注戰事,看下段新武戲,將這段文戲忘了個乾淨。
跟中國所有的一時誰也吃不下誰的爭論的雙方一樣,名稱之爭是吵架的重要一環,雙方都免不了要互賜惡謚,在中西醫吵起來之前,軍閥們已經集體打了十幾年亂鬨鬨的電報仗。醫界是懸壺濟世的,故而還比較客氣,西醫稱中醫為舊醫,稱自己為新醫,而中醫則自稱國醫,不承認西醫是新醫,偏叫他們西醫甚至洋醫。跟軍閥們“官”“匪”“正”“邪”之類的互詈有
所不同的是,中西醫之間相互擲來擲去的四頂帽子,“新”“舊”“國”“西”,恰恰點明了這場風波所蘊的思想史內涵。自從國門被打開之後,中西文化之爭,隨著中學的節節敗退,不知不覺之間從華夷之爭變成中西之爭,最後又變成了新舊之爭。顯然,這不是一種簡單的此消彼長,前面“華夷”語境裡的褒貶,到了“新舊”語境中,不僅僅褒貶顛倒了過來,而且有了進化論意義的肯定與否定,對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更具有殺傷力,或者說懾服力。
我們看到,此次中醫的存廢之爭,又一次成了新文化運動時很熱鬧的“科學與迷信”之爭,只是,這次的“科學與迷信”論爭,雙方的立論卻沒有本質的不同。西醫攻擊中醫不科學,
自在情理之中,他們將中醫的陰陽二氣、五行生剋、經絡脈案等等統統打入張天師胡大仙一黨,舊醫登記案的提議者余岩乾脆稱中醫為“依神道而斂財之輩”。由於自恃有生理、解剖、化
學、物理以及藥理學做後盾,他們的氣很粗,明顯處於攻勢。奇怪的是中醫們也沒有祭起扁鵲、華佗的大旗,抬出《黃帝內經》、《王叔和脈經》的道理來反駁,在他們看來,“竊中國醫藥卻有優良治效,徒以理論上不合科學、致不得世界學者之信仰,此固醫藥之起源先有經驗而得治效,後以理想補其解釋,不克偏於哲理,治效卻是實際也。近日西人證明中藥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載符合,且廣設學會研究漢醫,而國內學者亦相率以科學方法整理髮揮,漸得中外學者之信任。”(《大公報》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緊緊抓住“效驗”兩字來做文章,似乎憑藉的也是科學與洋人。
但是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問題,由於來自農業的收入相對來說比較穩定(除了出現全國性的災荒),但增長速度卻慢,而且即使增長,由於政府稅收是依靠幾乎很難有多少變化的黃冊
和魚鱗冊來徵收的,也很難反映到稅收上。因此,那個時代的政府,基本上是量人為出,每個部門都有固定的款項,也有固定的開支;凡屬重大的事務,也都有固定的撥款,比如漕運、河
道修繕等等。國家的機動開支很少,一般只準備兩項,一是備荒,二是應付戰事。比較起來,應付饑荒的儲備還算充足,但對付戰爭的準備就顯得相當有限,一旦戰事拖得久一點,儲備
就會告罄,非得挪用它款方可。這種政府財政體制,最害怕的是兩種情況,一是突發事件以及額外的開支,二是曠日持久的戰事,兩者往往會引起一系列的拆東補西,一系列的財政緊張,
一系列的拖欠,多少年都回復不了正常。如果連拆東補西都應付不了,那么只好增加稅收,一般是在正稅之外再加攤派。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古代號稱君主專制,但皇帝大修宮苑的時候總是會遭來大批的諫章。戶部,不,整個官僚體系都緊張得了不得,皇帝意志要想貫徹下去,總是大費周章,當然緊張歸緊張,這種開支有時還是非添不可,結果最後還是在攤派上打主意了賬。
其實,引起攤派增加的因素還有一個,而且相當重要,這就是政府機構的膨脹和自身的腐敗。我這么說,有人是會有異議的,因為總的來說傳統時代,特別是明清,國家機構是比較
固定的,多少年機構不動,額員不增,引得那時候來中國的傳教士們羨慕得緊,回國就夸個沒完,害得歐洲啟蒙運動的時候,中華帝國居然是哲人們鼓吹效法的榜樣。直到現在,某些外國
學者依然認為,中國古代用最少的行政官員,管理了一個過於龐大的帝國,有著非常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實際上明清的政府機關並不像他們說的那樣精簡,那樣的有效率。政府機構雖
然正常的額員增加起來較難,新機構的設定更是不多見,但並不意味著政府機構就不膨脹,人員就不擴張。膨脹的途徑一是添設臨時機構和人員,像晚清那樣,沒完沒了地設“局”,“委”員(這裡的“委”是動詞,不過委員一詞的確也是從這裡來的)。其途徑之二,更常見的膨脹情形則是政府屬吏的增加。
現在我們有些學者一談到眼下的政府機構臃腫問題,往往會拿傳統時代作比較,說是那時候一個縣只有兩三個政府官員,而縣以下連一個都沒有。其實,這樣說是不符合實際的,縣
以下沒有政府機構無疑是實情,但縣上的政府官員絕對不可能只有兩三個。稍微了解一點中國古代制度的人都知道,明清地方基層政府除了正印官之外,還設有六房書吏和三班衙役。這
與中央政府對應的吏、戶、禮、兵、刑、工六房,每房都設定若干司吏、更多的典吏和書手。
科考的下等人,但在實際的政務操作中,農民見了他們依然怕得要死,都得尊稱他們為“捕翁”和“班翁”。所以,不能說不拿俸祿就不是政府官員。
書吏的額員雖然按理也是有定數的,但實際上遠沒有“朝廷命官”那樣嚴格,而且書吏薪俸極其微薄,收入主要依靠陋規,他們的膨脹一般不會引起上級政府財政上的問題,所以,每當一個朝代年頭久了,整個政權機器開始運轉不靈的時候,書吏就會像氣吹的一樣膨脹起來。衙役就更是如此,他們連工資都沒有,只有一點微不足道的補貼,所以人員的擴張就更方便。一般在正役之外,首先加上“幫役”,然後幫役之外再加“白役”,成十上百地加上去,很快一個縣的衙役就會逾千。雖然國家規定衙役法律地位低下,但現實卻並非如此,在一個大多數人都要靠在土裡刨食的情況下,想要不吃苦而且過得好一點,混入政府絕對是個比較好的出路。往往是越是王朝末季,吏治越腐敗,賦稅越重,因而流離人口也就越多,各種案件也就越多,所以也就有越多的理由添加衙役。而添加的衙役越多,卻只能使社會狀況更加惡化,形成了解不開的惡性循環。除了書吏和衙役之外,一個衙門裡還有正印官自己出錢雇的師爺、長隨等人員,雖然是官員自己出錢,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實際上也等於是政府開支。
明清兩代,凡這種性質的政府機構膨脹,無論中央機關還是地方政府,從表面上看都不需要增加財政的壓力,隨便添上亡萬個書吏和衙役,戶部的賬面上也沒有什麼反映。但是,這些吏和役進入政府,都是要吃飯的,而且還想著吃得比一般人更好一點,沒有利益的話,是不會有人拚命地往政府里擠。書吏和衙役吃的都是陋規,人數增加了,或者將陋規增大份額,或者是增添新的陋規,否則就難以安排。這些收入最後當然都要落到老百姓的頭上,直接刮地皮的當然是縣裡的人,然後層層孝敬,各級政府都添丁進口,皆大歡喜。
我們知道,在未能用數字管理的時代,政府的政務越是繁複,稅費徵收的環節、次數越是複雜,經手人上下其手,從中舞弊的機會就越多。這就是為什麼明朝張居正改革,實行一條鞭法之後,實際從數字上看農民交的錢糧是多了,但農民的負擔卻輕了,因為一條鞭法變繁政為簡政,從而減少了官吏的中飽。顯然,對於一個日益膨脹的政府內的成員來說,這種現象是不能長期容忍的。為他們的飯碗計,政務只能越來越多,手續必須日見煩瑣,讓皇帝和上司見了,覺得人人都在忙於公務,辛辛苦苦,勞勞碌碌,似乎只有獎賞的道理,沒有責罰的理由。所以,正稅之外的攤派和附加無論如何都是要加上去的,不加何以塞眾官之口,何以飽屬吏之欲?明代的張居正改革最後按“黃宗羲定律”演化了下去,當然首先有對後金的戰事無窮期的因素,因而引出“遼餉”(後金的女真人在遼東),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王朝末世的政府膨脹。箇中的道理,其實不是像錢穆先生說的那樣,政府把改革已經加入的攤派給忘了,然後再行攤派,實際上是政府希望農民把這一點忘了,或者裝作自己忘掉了,攤派才好理直氣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