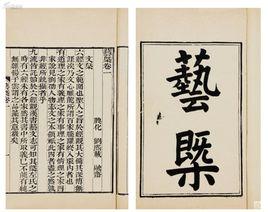作者
清代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後改授編修。同治三年(1864年)補國子監司業、廣東提學使,不久請假返回故鄉,從此離開官場。晚年寓居上海,擔任龍門書院主講,長達14年之久。他始終保持著一個學者的本色,閉門讀書、寫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所說的:“自六經、子、史外,凡天文、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尤以躬行為重。”於經學、音韻學、算學有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藝,被稱為“東方黑格爾”。著有《古桐書屋六種》、《古桐書屋續刻三種》。
六卷中,《書概》和《經義概》分別談論了書法藝術同詩與畫的關係以及治經與八股文寫作的關係,其他部分都是專門論述文藝創作的。他的寫作目的也相當明確,就是“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達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目的。
內容
《藝概》是作者平時論文談藝的彙編,成書於晚年。全書共6卷,分為《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分別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八股文等的體制流變、性質特徵、表現技巧和評論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謂談藝“好言其概(《自敘》),故以“概”名書。“概”的涵義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簡馭繁,“舉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觸類旁通。這是劉氏談藝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藝概》一書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談藝之作比較起來,廣綜約取,不蕪雜、不瑣碎,發微闡妙,不玄虛,不抽象,精簡切實。
《藝概》論文既注重文學本身的特點、藝術規律,同時又強調作品與人品、文學與現實的聯繫。劉熙載認為文學是“心學”,是作家情志即“我”與“物”相摩相盪的產物。所以論文藝貴真斥偽,肯定有個性、有獨創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對因襲模擬、夸世媚俗的作風。他注意到文學創作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按實肖像”、或“憑虛構象”。並重視藝術形象和虛構,認為“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所以對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較深刻的認識。如說莊子的文章“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乃是“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李白的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其實與杜甫“同一志在經世”。他運用辯證方法總結藝術規律,指出:“文之為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經義概》)。又說“物一無文”,但“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藝概》對物我、情景、義法種種關係的論述,就著重揭示了它們是如何辯證統一的,突出了我、情、義的主導作用。
由於把握藝術辯證法,劉氏考察創作問題、評價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層,高出一頭,有精闢獨到的見解。他強調作品是一個有機整體,論所謂“詞眼”、“詩眼”,提出“通體之眼”,“全篇之眼”。他談批判與繼承的關係,指出“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他對不同旨趣、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不“著於一偏”,強分軒輊,其長處與不足都如實指出,如說:“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他論表現手法與技巧,指明“語語微妙,便不微妙”,“竟體求奇,轉至不奇”,強調“交相為用”、“相濟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藝術範疇,如深淺、重輕、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諧拗、淡麗等等。
劉熙載認為文學“與時為訊息”,重視反映現實、作用於現實的所謂“有關係”的作品。他還把作品的價值同作家的品格聯繫起來,強調“詩品出於人品”。所以他論詞不囿於傳統見解,推崇蘇軾、辛棄疾,批評溫庭筠、周邦彥詞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約派詞為“變調”,而以蘇軾開創的豪放派詞為“正調”。他的詞論,在清亡前後有一定影響。沈曾植稱許他“涉覽既多,會心特遠”(《菌閣瑣談》);馮煦謂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論詞》);王國維《人間詞話》則對《藝概》拈出作品中詞句來概括作家風格特點的評論方式以及個別論點,都有所吸取。
《藝概》有刻於同治十三年的《古桐書屋六種》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標點本。劉氏另有《遊藝約言》,與《藝概》同類。清代光緒二十九年四川成都官書局印本《藝概》。
此書是近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優秀的理論著作。共六卷。它的廣博和慧深為後代許多學者所推崇,使得它成為一部古典美學的經典之作,而劉熙載也成為中國古典美學的最後一位思想家。
《藝概》論文既注重文學本身的特點、藝術規律,同時又強調作品與人品、文學與現實的聯繫。劉氏考察創作問題、評價作家作品,往往有精闢獨到的見解。他強調作品是一個有機整體,論所謂“詞眼”、“詩眼”,提出“通體之眼”,“全篇之眼”。談到批判與繼承的關係,認為“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並能夠正確對待不同旨趣、風格的作家作品。他論表現手法與技巧,指出“語語微妙,便不微妙”,“竟體求奇,轉至不奇”,強調“交相為用”、“相濟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藝術範疇,如深淺、重輕、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淡麗等等。《藝概》有刻於同治十三年(1874)的《古桐書屋六種》本。
特點
《藝概》的寫作缺乏完整的體系。它採取的是以三言五語論述創作上的一個問題或評論一個作家、一種文學現象。他把自己的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為“欲其詳盡,詳有極乎”?因此採取“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的辦法,以期起到觸類引申、舉一反三的作用。綜觀《藝概》全書,的確也基本上做到了這點。尤其在論文、詩、詞、賦諸部分中,對作家作品的評定,對文學形式的流變,對藝術特點的闡發等,時有卓見確論。《藝概》的寫法是傳統的詩話的寫法,用短短几句話,評論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藝術特點。但是比起傳統詩話的多部著作來,《藝概》有兩個特色:一、它評論作家、作品,主要著眼於藝術作為審美創造的特點和規律,理論性比較強,不像傳統詩話、詞話那樣,用大量篇幅記載傳聞逸事或搞史料考證。所以它更帶有美學的性質。二、它不像傳統詩話、詞話那樣,只涉及文學的一個門類,而是涉及詩、文、詞、曲、書法等藝術的各個廣泛門類,這在過去也不多見。
《藝概》最突出的特點,是對藝術創作中一系列辯證關係的探討,對於這些關係的探討比起前人來更自覺、深刻和全面。他從解剖各種藝術的具體實踐出發,概括出100多個對立統一的美學範疇,意在運用兩物相對峙的矛盾法則來揭示藝術美的構成和創作規律。可以說,矛盾法是貫穿《藝概》全書的中心思想,也是劉熙載論藝及其審美方法論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個對應 範疇,構成了藝術辯證法的一個獨特的審美體系,這既是《藝概》的一大特點,也是劉熙載在總結古代藝術辯證法方面的一大貢獻。這個審美體系的基本內容,可以從七個方面加以概括:主觀與客觀統一的本質論、真實與虛幻統一的真實論、“一”與“不一”統一的意象論、似花還似非花統一的意境論、陽剛與陰柔統一的風格論、用古與變古統一的發展論、人品與詩品統一的鑑賞論。
劉熙載是一個重視躬行實踐、力求獨善其身的儒者。他論詩話文評曲品詞,十分強調作家思想感情以及為人處世的“人品”在創作實踐中的作用和影響,提出了“詩品出於人品”的著名論斷。這也是他文藝品評的重要原則和文學評論的核心。
知人論世,是中國文藝批評和文藝理論的基本觀點,所以就有“讀其文想見其人”的評論。劉熙載的“詩品出於人品”,就是認為詩品是人品的一種反映,是詩中的人品。前者具體指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水平的高低,後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質。從這個觀點出發,在《藝概》中,對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推崇;對於品格不高者,則常有微詞。他稱屈原的《離騷》, “一往皆特立獨行之意” (《賦概》)。這就是說,屈原的《離騷》正是他高潔人格的表現。他說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文概》)。柳宗元關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夠寫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銳地對現實加以揭露,又能抒發他思想上積鬱的對現實的不滿。他認為詞也是詞品出於人品,說:“論詞莫先於品”(《詞曲概》)人品體現在作者的文品中,就連書法也不例外。他說:“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書概》)還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書概》)這就強調了人的才學、思想、性情,是書法中最重要的。
基於上述思想觀點,劉熙載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認識,往往相當深刻、明確,進而評點其價值意義。他能夠透過一些作品撲朔迷離的表面現象,發掘出作家作品深層的思想內涵,揭示作品的真實內容和藝術價值。在評論李白、杜甫的異同時,他明確指出: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有為言之也。屈子《遠遊》曰:‘悲時俗之迫厄兮, 願輕舉而遠遊。’ 使疑太白誠欲出世, 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詩概》)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經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他的一些描寫神仙境界的遊仙詩,表面上看來浪漫、超脫,可仍然是一種“有為言之”的創作。為了把問題說得更為確切,劉熙載還以屈原的《遠遊》為類比,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論杜詩,認為杜甫“志在經世”,又善於抒發真實情感,這樣的人,如果能夠得到明主的器重,為世所用,一定能夠“濟物”救世。他說:“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為看詩之法。”(《詩概》)宋代關於蘇軾、辛棄疾的詩詞,他十分推崇,《詞曲概》裡面說:“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煢。”又說:“英雄出語多本色,辛棄疾詞,於是可尚。”他對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質,又有偉大的抱負和愛國心的作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相反,對那些在創作上雖然也有很高造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內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卻表示出明顯不滿,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銳地指出那些描寫歌姬、舞女的詞作,“類不出綺怨”。(《詞曲概》)說北宋大家 周邦彥與妓女談情說愛的詞,不過是其淫情盪旨的宣洩, “當不得一個‘貞’字”。這在晚清浙江詞派與常州詞派大都推崇溫庭筠、馮延巳、柳永和周邦彥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副清涼劑。
劉熙載對於藝術創造中“天”、“人”的關係,即自然和人工的關係,有很好的論述。他提出了一個“天”、一個“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這是一個藝術創造的三段式。他說:“書當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於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書概》)所謂“肇於自然”,就是說,藝術家創造的審美意象,應該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跡。所以叫“由人復天”。他還說:“《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疏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概》) “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 (《詞曲概》) 《檀弓》的渾化、古樂府的“極煉如不煉,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於天籟”,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復天”。
評價
用古與變古的對立統一,是劉熙載對待文學遺產的基本態度。他繼承了自劉勰以來的這個進步傳統,主張在用古中變古,也就是在繼承中革新創造。何以要變古?他認為“文之道,時為大”。《文概》云:“《春秋》不同於《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為《史》,則樵殺;強《史》為《左》,則緩。惟與時為訊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就是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時代訊息和生活內容,所以文學創作應因時而異。這和劉勰所云“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何以又要用古呢?劉氏解釋是“善用古者能變古”。他把“善用古”作為“變古”的前提條件,是極有見地的。他曾以韓愈為例講用古與變古的辯證道理:“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文概》)他的這個論斷同時適用於一切有成就的文學家、藝術家。例如講李白詩說:“以莊、騷為大源,而於嗣宗之淵放,景純之雋上,明遠之驅邁,玄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詩概》)他又說:“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詩概》)顯然,他把重點還是放到“有我”的這一面。
他認為“用古”與“變古”的矛盾雙方,“有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從“有我”出發,從藝術創新出發,才能從“無所不包”到“無所不掃”,即正確吸取前人成果而不至於被古所囿,被古所化,才可能“自成一家”。所以他竭力反對“剿襲古人”,主張“務去陳言”,不落“凡近”,要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文概》),要化他神為我神:“書貴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別。入他神者,我化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為我也。”(《書概》)劉氏用古和變古的思想,鮮明地體現了他的辯證的藝術發展觀。
《藝概》在文學作品藝術性的評論中,也有許多精到的觀點。劉熙載常常用極儉省的語言,畫龍點睛般地道出作家作品的藝術特徵和風格特點,有時還能深入發掘和體會作家的內心世界。如他在談論漢代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的藝術風格時,只用了“奇創”、“醇厚”、“俊發”六字,就昭示出他們的藝術個性。談論屈原和陶淵明的辭作時,也只用寥寥數字,指出屈辭的“激”和陶辭的“平”,都具有他們各自“獨往獨來”的風格。再比如他談論《莊子》只用了一個“飛”字,概括了莊子的“無端而來,無端而去”的個性化特點。評論杜甫詩,他給了“高、大、深”三個字,說杜詩“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精闢、中肯,也表現出他在文論上的膽識與功力。在談論文藝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創新時,他很注重隨著時代變更的“獨抒己見,思力絕人”(《文概》),反對傳統的“正變論”,強調了“變”(即發展)的必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另外在許多地方,劉熙載還從繼承和創新的辯證關係上,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在談藝術表現手法方面,他的關於情景關係的論述,也有許多警拔脫俗的地方。
總的說來,劉熙載的《藝概》,是晚清的一部優秀的文藝理論著作,他的美學思想,仍然屬於中國古典美學的範疇,與同時代的梁啓超、王國維等人不同,他不是近代美學思想家,而是中國古典美學的最後一位思想家。雖然他的《藝概》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的廣博和慧深,使得它成為一部經典之作。他的用古和變古思想的辯證的藝術發展觀廣為後人所借鑑。
名句
書當造乎自然。
文之道,時為大。
法以除弊,法亦生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