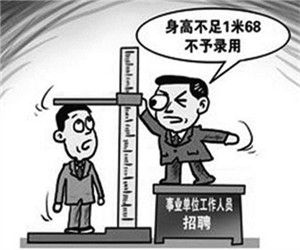基本案情
 蔣韜案
蔣韜案分歧意見
此案件涉及三大爭論焦點:1、是否存在法律缺位?一種觀點認為:此案中行政機關和公務員不是普通的勞動關係,所以不適用《勞動法》。擔任公務員按公務員管理條例來說是一種勞動權利也是一種政治權利,身高的限制侵犯了平等權,進一步侵犯的是公民擔任國家公職的政治權利,但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僅限於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平等權並不在此範圍內,按照“有權利就有救濟”的法治原則,此時只好援引憲法;另一種觀點認為:並非所有的平等權訴訟都是憲法訴訟,引用憲法條文來做判案依據,但不一定要用憲法來救濟,憲法的使命是一個的“宣告”的作用,但最後的賠償或救濟還是要依靠其它的法律,違憲審查或憲法訴訟制度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此案有下位法可循。第一是有《憲法》第33條規定;第二是有《勞動法》第12條規定,勞動者不能因性別、種族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視;第三是《公務員條例》第2條規定的公務員平等公開擇優的選拔原則;第四是《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用法律法規能得到救濟的,就不必引用憲法。2、平等是原則還是權利?一種觀點認為:平等是一個法律原則,因為平等是一切法律的基礎。另一種觀點認為,平等是一個獨立的法律權利,這種觀點認為,把平等看作是法律權利是現代社會走向法制的結果。第三種觀點認為:平等既是法律原則也是法律權利。3、憲法訴訟會泛化嗎?在有學者肯定平等權案件進入司法訴訟是我國法治的一個進步的同時,也有學者表示了擔憂,那就是擔心憲法訴訟會泛化。有學者認為:憲法訴訟案件多了,各級基層法院紛紛仿效,這就意味著一個地方的法院可以挑戰國家立法機關,所以只在兩種情況下可以引用憲法,一是立法不作為,二是出現立法危機,如立法機關公然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則,司法機關不能跳過法律法規去引用憲法。評析意見
本案中原告認為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的招錄廣告侵犯了他擔任國家公職的平等權和政治權利。在此,我們從招錄廣告的內容來展開分析。此招錄廣告的內容中包含了男女身高條件的規定,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如果公民不符合招錄廣告中的身高條件,公民將沒有資格參加考試,因此更談不上擔任國家的公務員,這樣公民平等的參政權將得不到實現。被告通過一紙廣告以男性168公分、女性166公分為界限在公民之間劃開了一條鴻溝,對身高不同的公民進行了不同的對待。這樣問題就集中在成都分行對公民設立的差別對待是屬於合理差別,還是屬於身高歧視?平等僅僅是一項起指導性的原則,還是能夠作為一項具體的權利?個人認為:此案中成都分行確實侵犯了原告的平等權,平等不僅僅是一項原則,也是一項權利。平等一直以來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特別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經為大多數的國家所採納,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一項重要的原則,大多數國家都確立了平等的原則以期在整個社會實現一種制度意義上的平等(社會正義),然而對於社會中作為個體的個人來講,一種抽象的平等原則顯然無法保證其個體平等的實現,而如果作為個體的個人的平等無法得到保障,作為制度層面上的平等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賦予個人具體的平等權來實現個體的平等是十分必要的。平等的制度性(整體性)與個體性決定了平等的原則性與權利性的同時兼具。作為一項具體權利的平等,如何界定它的內容以及如何使其獲得救濟應該成為討論的重點。
平等權的內容毫無疑問是平等,表現為個人為實現自身的平等,使自己與其它人在相等條件下能夠享受同等待遇的一種請求權。然而平等卻是很難界定的,平等自身就包含著矛盾,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平等,人人生而平等,人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權利,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一種機會上的平等,這種平等觀與自由緊密聯繫,將社會中的“人”抽象化,而全然不顧現實中的“人”由於先天與後天的因素而導致的強弱之分,只是保障人們在自由競爭中的機會平等;另一方面是實質上的平等,這種平等觀從人人生而不同出發,現存的客觀情況是“以變異性或多樣化為基石的生物學,賦予了每一個個人以一系列獨特的屬性,正是這些特性使個人擁有了他以其它方式不可能獲得的一種獨特的品格或尊嚴”,因此我們決不能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即使人們在相似甚至相同的環境下長大,個人之間的差異性決不會因此而減少,在這個基礎上如果賦予人們形式上的平等即機會平等,將會導致事實上的不平等,而要使人們在事實上達到平等只能給予差別對待,可以說,實質平等是從保護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的角度出發的;還有一種平等觀念,即結果上的平等,也就是絕對意義上的平等,這也是我們常說的平均主義。在這三種平等觀念之間確實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形式上的平等對於生而不同的人們來說,必然會導致結果上的不平等,在給予人們形式上平等下的自由競爭只會導致強者越強,而實質上的平等從人的差異性出發,給予人們差別對待,也不可能是對每個人予以糾正,將差別對待具體到每一個個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實質上的平等也不是意味著結果上的平等,給予人們差別對待也不意味著會達到絕對的平等,而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講,如果保障人們實現了結果上的平等,那么這種平等也無視了人們在過程中的努力程度以及能力差別等因素,相對來說是不是也是一種“不平等”呢?筆者認為:在這裡的關鍵問題是要界定給予什麼樣的人以及給予他們什麼樣的差別對待才是合理的,也就是合理差別的限度的問題。結果上的平等在現實條件下只能存在於理想當中,在現實中人們不僅存在先天差別,而且在勞動程度、分配條件、發展環境等方面還存在很大差別的情況下,無論使用何種方法,人們都不能預期能否實現結果上的平等,因此,在保證人們機會上平等的基礎上引入實質上的平等,予以糾正機會上的平等所會導致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是非常現實的做法,然而實質上的平等也要有一定的限度,畢竟一項制度無法針對每一個人具體的差異而給予差別對待,這正如要求結果上的平等一樣不現實。
個人認為,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引入實質平等的手段是實行合理的差別,而要界定什麼樣的差別是合理的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對什麼樣的主體給予差別對待?關於合理差別的主體,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考慮,一方面從量的角度考慮,即給予相對來說處於少數且弱勢的群體以差別對待,所謂的“少數”應該同時有一個與之嚴格對應的“多數”,比如說我國的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對應,但僅僅具備了“少數”這個要件還不能構成差別對待的理由,比如不能因為一個國家中男人比女人的數量少而給予男人以差別對待,這個“少數”的群體必須同時處於明顯弱勢的地位,如美國的黑人和婦女從歷史來看一直處於受歧視的地位,為了彌補這種長久以來的歧視,立法或行政機構於是採取了一系列的“贊助性行動”給予這些階層一定的優惠。另一方面從先天的生理的角度考慮,即給予明顯處於弱勢的個體以差別的對待,如殘疾人即存在著客觀上的生理上的弱勢,而女性在一般情況下不應被認為是弱勢,但由於其存在經期孕期哺乳期等客觀生理狀況而不易從事高強度勞動,因此我國在《勞動法》中規定了女性在“三期”中的特殊照顧;第三個方面是從經濟的角度去考慮,即給予經濟上明顯處於弱勢或無經濟來源的個體一定的生活保障,如我國規定的給予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保障費等等。第二個問題是差別對待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即給予什麼樣的差別對待才是合理的問題。差別對待總的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歧視,一種是優惠,歧視顯然是一種不平等,然而同時優惠也要有一定的限度,而不至於構成“反向歧視”,比如給予下崗工人生活保障費不能高到與本地區的平均工資水平持平等等。
經過以上的分析,讓我們回到本案中來,成都分行的招錄行員的廣告確實以“男性身高168公分,女性身高155公分”為標準,而給予了身高在這之下的公民以差別對待,但是這種差別明顯是構成了對這些公民的歧視,顯然不屬於合理差別的範圍,而成都分行的工作性質也沒有對身高有特殊的要求,因此我們可以認定成都分行確實侵犯了蔣韜的平等權。然而在我國平等權受到侵犯以後應該怎樣得到救濟呢?筆者認為:第一,此案確實存在法律的缺位。首先,此案不應該適用《勞動法》,《勞動法》第二條規定的調整對象針對的是已經與單位形成勞動關係的勞動者,並且也不調整國家機關與公務員之間的關係,蔣韜與成都分行顯然還沒有形成勞動關係,也不屬於《勞動法》所調整的勞動關係。其次,在本案中成都分行確實違反了《公務員條例》第2條規定的公務員平等公開擇優的選拔原則,但是《公務員條例》中並沒有規定具體的法律責任的規定,具體法律之於憲法的意義在於將憲法中的原則性條款具體化,並具體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而《公務員條例》第二條的規定顯然來自於《憲法》第33條第二款的規定,且同樣具有原則性,並沒有將憲法上的平等權具體化,也沒有相關的責任條款,筆者認為此條款並沒有起到具體法律的實際意義。第二,本案不應定性為憲法訴訟或違憲審查。不能把援引憲法的案件都當成憲法訴訟或違憲審查,憲法訴訟或違憲審查主要審查的應該是國會或州制定的法律以及行政機關制定的規章的合憲性,這也是憲法訴訟與行政訴訟的主要區別之一。在我國最高法院向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全國人大不僅僅是最高立法機關而且是最高權力機關,如果由最高法院審查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一來是由非民意機關審查民意機關,二來由於全國人大最高權力機關的憲法地位,導致其並不認為自己制定的法律違憲而拒絕廢止該法律,並且有可能導致最高法院的工作報告通不過,從而產生一場憲法危機。而且從憲法規定上看,我國只有全國人大有憲法解釋權,因此最高法院在審查法律的合憲性的時候往往要請求全國人大解釋憲法,實際上仍然是由全國人大在進行審查,而如果最高法院不請求全國人大解釋憲法,那么我們可以認為最高法院作出的是違憲判斷,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國的現行憲政體制下,普通法院無法受理一般意義上的憲法訴訟或者違憲審查。但是,這並不妨礙普通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引用憲法判案,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了行政訴訟的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在這裡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將憲法排除在外,同時雖然《行政訴訟法》將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局限於受理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的案件,但我們看到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應該是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如果將合法權益僅僅理解為人身權和財產權必將使公民許多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而最高法院關於執行《行政訴訟》若干問題的解釋也反映了逐步擴大行政訴訟受案範圍的意圖。在本案中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在性質上屬於行政機關,因此本案的性質是屬於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犯了公民的憲法上的平等權,從法律關係上來看其本質上屬於行政法律關係,應該屬於行政訴訟的受理的範圍,但由於侵犯的是憲法上的平等權,因此必須引用憲法而使本案顯得尤為突出,這也正如之前發生的齊玉苓案件一樣由於引用憲法而受到了過分的關注。
綜上所述,個人認為此案在我國可以通過行政訴訟得到救濟,不過法院在訴訟過程中必須引用憲法做出判斷,法院在日益複雜的形勢面前不應再恪守消極主義的理念,而應該充分發揮司法能動性,這樣才能充分而有效的保障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