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路
 深度多元論
深度多元論第二條進路由那些人採取,他們準備從自己信仰的觀點來思考宗教多樣性,不貶低其他人的靈修。一般地說,這些神學多元論者認同的是在其他傳統中得到尊重,並具有相似於他們自己傳統中那些元素特徵的東西。在基督徒中間,只要其他傳統肯定上帝的統一和上帝的力量及愛,它們就值得尊重。只要它們教導人們對待他人就像自己想要被人對待那樣,它們就值得尊重。只要它們集中在崇拜共同體或沉思默想的修道院之中,它們就值得尊重。這些神學家越加慷慨地承認他們在某些其他傳統中發現的東西,那么在他們自己傳統中那些沒有被足夠強調的元素就越加豐富地得到了發展。因此,不需任何方式為他們自己傳統中的基本缺陷或失敗讓步,神學家們依然可以承認某個其他傳統以某種有限的方式是優秀的。
例如,一個基督徒可以承認佛教的一些形式比基督教的大多數形式在克服對世間財產的執著方面做得更好。另一方面,一個佛教徒可以承認基督教的一些形式比佛教的大多數形式更加豐富地發展了社會的道義。於是,肯定自己傳統的基本圓滿和恰當不必導致一個神學家去否認其他傳統的力量。
不過,明顯的是當神學家們開始信服他們自己傳統的基本圓滿和恰當時,他們不會把自己傳統放在與其他傳統同等的水平上。他們暗中要求自己傳統的優勢地位,並且,今天許多人發現這種要求是令人討厭的。他們寧願站在一個更加中性的立場上來看待事物。這種立場典型地以哲學術語來表達。
那么,一個宗教哲學家可以審查各種傳統而不對任何一個有所推重。從這種觀點看,它們的相對強項和弱點能夠更加冷靜地得到檢驗。一個人能夠很好地宣稱,相對於那些對一個傳統有所推重的前多元論,這是一種更深度的多元論。然而,任何這樣的批評性審查需要一些標準。在這種情形下,該標準必須在哲學上被推斷出來。
實踐論證
 深度多元論
深度多元論對實踐目標多元性的論證並不牽涉任何理論問題。一些傳統的最終目標是逃脫現象世界,而其他傳統卻在於轉變那個世界。一些傳統的目標也許在於達到個體此生此世的心靈寧靜,還有一些傳統則為了整個共同體的具體歷史目標而奮鬥。應該讓每個共同體以它自己的方式描述它的目標而不是試圖識別一個總的共同的目標。
過程思想家的真正引起爭議的立場是,存在著終極的多元性。既在宗教上又在哲學上達到了這種立場。
對希克的解釋進行宗教抗議是因為這種解釋冒犯了所有它想要榮耀的那些人。說存在著某種東西要比人格的上帝更為終極,這種觀念冒犯了有神論者。說存在著某種東西要比空更為終極,這種觀念冒犯了佛教徒。
觀點討論
 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發展改變了這種狀況。物質,現在簡化為質量,被看作等價於能量。誠然,對這些科學數據比較有意義的一個解釋是,構成世界的單元是能量事件而不是物質團塊。能量事件不是被動的。它們在其自身存在中包含了活動原理。在質料因的方向上,這個終極最好被稱為“原初能量”或能量本身,而不是“原初物質”。
托馬斯不能鑑別存在本身與其最高級例證之間的差異,後者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即上帝。他十分難於令人信服地說道,兩者是相同的。邁斯特•埃克哈特跟隨托馬斯,但他清楚存在本身與那個至高無上的存在或上帝是不相同的。他使上帝從屬於存在本身,後者他稱為神性,以致對他而言,只有存在本身是終極的。在二十世紀,蒂利希追隨這一套路,只是否認了上帝的存在,而埃克哈特並沒有那樣做。海德格爾把上帝從存在本身中區分出來,並肯定後者,但不像蒂利希那樣,他還是向上帝敞開了大門。
要托馬斯把存在本身認同於原初物質是不可能的,因為物質被理解為被動的,而存在本身是純粹的活動。但既然已把原初物質轉變成能量本身,那么與存在本身的認同就容易多了。這樣能夠認識到,每一事物都是存在本身或同等意義上的能量本身的一個例證。儘管用亞里士多德術語來說,這還保留了“質料因”,即組成一切事物的東西,但已不再具有任何宗教上貶低的意蘊了。
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把所謂的存在本身或能量本身拓展為“創造性”,為的是超越前者的靜態內涵和後者與物理學的密切聯繫。他明確地把終極性歸於創造性。每一事件,造物的或神聖的,都是創造性的一個例示,就如在托馬斯傳統和海德格爾中那樣,每一存在事物都是存在本身的一個例示,又如在現代物理學中那樣,每一事件都是能量的一個例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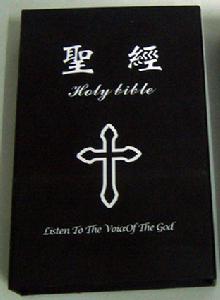 《聖經》
《聖經》實際上,這兩組終極之間的區分同樣也在聖經《創世記》第一章對創造的說明中被假設。 《聖經》當上帝開始創造時,世界是無形式的空虛。這“無形式的空虛”顯然與上帝一樣是終極的。但在希伯來人的心靈中,它沒有宗教的價值。只有形式才分有價值,而上帝顯然是形式的給予者。希臘人也這樣想。懷特海跟隨之。對於懷特海就如對於亞里士多德一樣,上帝是終極的目的因和形式因。但懷特海沒有在動力因系列中設定任何終極。
作為過程神學家,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這兩個終極上面。在那些“高級的”宗教中,它們起著主要的作用。然而,還有第三個東西同等地重要。那就是創造物的世界。沒有世界,就可能沒有創造性。沒有世界和創造性,就可能沒有上帝。當然,說沒有創造性和上帝就可能沒有世界同樣也是真的。上帝、世界和創造性都各有它們相互依賴的實在。它們不可能從相對終極性按等級排列起來。
無宇宙論宗教從現實具體性的世界轉向這個世界的基礎、實體或基本原理。後者被理解為處於世界之下或超越世界之外。這些宗教傾向於把已形成的世界構想成現象而不是實在本身,並尋求更深度的實在。
有神論傳統把這個世界理解為體現了一定的目的和意義,因為它與一種至高無上的宇宙精神相關聯。這種精神通常被想像成創造了這個世界並照料著這些創造物。正確地與這種精神相關聯對一種生活得好的人生來說是決定性的。
宗教關係
 耶穌
耶穌事實上,最近幾十年這一直以一種相當大的規模在發生。現在成千上萬的基督徒以一種持續不變的方式從事於佛教的靜觀實踐。如果一個人把佛教徒定義為追求佛教之覺悟目標的人,那么現在許多基督徒就是佛教徒,但他們作為耶穌的門徒並沒有中斷對上帝的信任和崇拜。
誠然,佛教關於每個人和所有其他存在物都是緣起的例證,這種認識應該導向對每個人和所有存在物的親密關照,並就其特色欣賞他們。事實上,有許多關於佛教聖人的故事,他們在很大範圍內拯救同伴存在物脫離苦難,無論是人類的還是非人類的存在物。從佛教的無宇宙論傾向到對這個世界的深度欣賞並致力於實際的拯救,這個轉變是佛教的一種實行,而不是其信息的丟失。
類似地,基督教對上帝的崇拜與把整個創造秩序置於宗教生活中心,這兩者之間實際上沒什麼差別。崇拜上帝必須表現在服務於上帝之中。但人們如何能夠服務於上帝?他們能夠服務於上帝的事情只是有益於上帝喜愛的造物。
作為一個基督徒的信念是,聖經信仰的上帝越加充分地開放自己,將對其他人所學到的東西越加開放。這些東西是他們通過對世界的開放和對其中發現的到處起作用的無宇宙論原理的開放所學到的。向其他人學習並將學到的東西整合於生活和思考,這並不把人與基督相分離。相反,人達到了對自己、上帝和世界更好的理解,並感激在基督中經驗到的自由。
一些猶太人、一些穆斯林、一些佛教徒、一些印度教徒和一些中國傳統生活方式的追隨者都有相似的經驗。對些具有宇宙論定位的人們而言,向無宇宙論和有神論的思想家們學習不必使他們與和諧相處的宇宙力量相左。誠然,這種學習可以導向對這些力量更有深度的理解,並對他們的宗教生活提供另外的維度。對那些具有無宇宙論定位的人們而言,也有可能豐富和充實對他們自己傳統的理解。
並非在暗示,就每個單獨意義上的人而言,目標是把所有這些宗教生活的維度同等地表現出來。那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原則上的可能已足於顯示一個傳統的開業者們不必把其他傳統想像成必然是錯誤的、脅迫的或低劣的。人們也許認識到,其他人所做的東西補充了人們所做的東西,即使沒有嘗試採取他們所有的實踐。如果大多數人強調一種或另一種精神實踐形式,那么這種互補性將變得更加豐富。但是,如果一條道路的跟隨者不能實現其他互補的道路的價值,那么它不會更加豐富。
這種對定位和目標上差別的認識相比於過去一般所謂多元論的東西,是一種更有深度的多元論。人們還認為,這種深度多元論鼓勵人們大家深深紮根於人們自己的傳統中,正是為了人們能夠欣賞和學習其他傳統。深度的信仰和深度的多元論互相調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