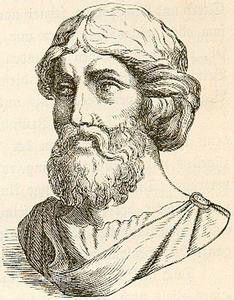引言
模仿說是從 古希臘時期審美活動“和諧說”發展而來的。
前 蘇格拉底時期,即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中葉,成熟的“邏各斯”衝出史詩和神話的外殼,成長為一種獨立的思想,古希臘精神世界由此產生了一幅理性的哲學新圖畫。前蘇格拉底 哲學家對自然本體論表現出特殊的偏好,他們感興趣的是自然事物的抽象原則與規律,文學活動還沒有被他們納入專門的興趣範圍,在他們的著述中幾乎看不到任何當時文學活動的評價;他們偶爾評價文學現象時,使用的也往往是非文學的標準。這個時期的文學思想從整體特徵來看是形式主義的。
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在事物的運動中發現了節奏:青春年老、日夜晨昏、上升下降、歡樂痛苦、幸福災難,並在節奏中發現,事物在流轉與變化中始終保持著深刻的連續性與統一性,即整體的和諧狀態,於是他們嘗試用“和諧”解釋一切藝術現象。
畢達哥拉斯
畢達哥拉斯嘗試用“數的和諧”解釋萬物美的根源, 赫拉克利特則把藝術的產生歸因於“對立的和諧”。畢達哥拉斯把和諧視為事物數量關係的形式化表現,“沒有一門藝術的產生不與比例有關,而比例正存在於數之中。所以一切藝術都產生於數”,文藝作品中都存在著“某種比例。由於這種比例,它們達到了完美的和諧”1。這種哲學形式的研究模式,給文學研究走向科學化和形式主義提供了最初的參照藍本。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前蘇格拉底時期詩學匱乏的原因:美在和諧與形式,既然研究事物本身的形式關係就能獲得美,那又何必捨近求遠,去研究事物以外的東西如文學呢?
“和諧”說在邏輯上暗含著對感官經驗的否定,其必然的推論是形式高於經驗、抽象美高於具象美,這是赫拉克利特貶低肉體快感,推崇“看不見的和諧比看得見的和諧更好”的原因2,也是 柏拉圖以後文學中的神秘主義、表現主義最初的理論根據。
和諧說雖然不是專對文學現象而發,但是它作為一個基本的審美原則,對其後文學的發展卻有著深遠的影響,20世紀的 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以前,西方文學精神基本上隸屬於“和諧”這一範疇。
審美“和諧說”給“模仿說”這一文學創作原則提供了內在的理論根據。不過,前蘇格拉底時期,模仿說難以跳出自然哲學的窠臼,所謂“模仿”,系指對自然物構成形式和功能的學步。赫拉克利特認為,“和諧”是自然物存在的特徵,藝術活動是對自然物構造方式的模仿,“自然……是從對立的東西產生和諧,而不是從相同的東西產生和諧。例如自然便是將雌和雄配合起來,而不是將雌配雌,將雄配雄……藝術也是這樣造成和諧的,顯然是由於模仿自然。繪畫在畫面上混合著白色和黑色、黃色和紅色的部分,從而造成與原物相似的形相。音樂混合不同音調的高音和低音、長音和短音,從而造成一個和諧的曲調。書法混合元音和輔音,從而構成整個這種藝術”3。 德謨克里特視模仿為人在藝術活動中對事物自然功能的學步,“在許多重要的事情上,我們是模仿禽獸……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唱歌”4。
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400年)的出現標誌著西方思想史的轉折。蘇格拉底反對一切不關心人的本質和生存的實證科學,宣稱自己和物理學的探索毫無緣分,他拒絕討論諸如宇宙的性質、宇宙秩序和天體產生的原因,卻熱衷於討論各種人文問題,從來不感到厭倦5。自此以後,古希臘思想的重心由自然本體轉向人類本體。
蘇格拉底徹底貫徹了智者的文化哲學思想,卻又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智者宣稱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則認為只有思維著的人才有資格作為萬物的尺度。思維著的人具有自我決定的能力,這是人作為道德主體的本質所在。因此,蘇格拉底把哲學認識的目標定位在人類自身,並以一生的活動躬行了“認識你自己”這一哲學信念。 黑格爾認為,蘇格拉底的人類學主體“原則造成了整個世界史的改變,這個改變的轉折點便是:個人精神的證明代替了神諭,主體自己來從事決定”6。
蘇格拉底認為,在主體的生存中,善本身就是目的。哲學的最高目標不是建立一個理論體系,而是幫助人們明辨是非善惡,揭示生活的意義和目的,使人們能夠合理地選擇行動,安排生活。因此,他沒有留下任何形式的著作,而是把哲學化為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倫理學,後人看到的他的思想材料只是其學生保存下來的一些對話記錄,如柏拉圖的《申辯篇》、 色諾芬的《 回憶蘇格拉底》。不過,蘇格拉底把人生問題歸結為善的問題,並把善歸結為知識(美德即知識),最終把西方哲學引向了認識論和科學主義的軌道,偏離了人生意義的探究。真箇是“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千年以後,成為 尼采生命哲學的第一個攻擊目標。
蘇格拉底把他對人的哲學思考運用於文藝領域,引起了文藝創作原則與批評標準的根本變化。蘇格拉底的文學思想大體保持在文藝倫理學的範圍內。
首先,就文學創作來說,人自身一旦成為世界的中心,自然對象作為模仿的根基就發生了動搖,模仿的方向不得不發生偏離和移動。蘇格拉底認為,人應當成為文藝模仿的對象,不僅人的外部形體動作可以模仿,就是人的“精神方面的特質”也可以“模仿”7,不論這種特質是善的還是惡的;例如人的性格,美的善的可愛的如高尚、慷慨、謙虛、聰慧等可以模仿,惡的醜的可憎的如下賤、卑吝、驕傲、愚蠢等同樣可以模仿。蘇格拉底指出,從模仿的效果來看,如果能“把人在各種活動中的情感也描繪出來”,尤其是把那些美和善的情感描繪出來,更能引起“觀眾的快感”,因此,他認為文藝模仿的目標應該是“通過形式表現心理活動”8。這樣,文藝美的研究就從形式領域轉到了人的精神領域,人的精神領域成了文藝表現的最高目標。
這樣,蘇格拉底的道德哲學觀幫助他實現了模仿從自然向精神領域的過渡,使文藝創作的原則發生了更新,這一新的創作原則經由柏拉圖的中介,在 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體系中得到完善,成為西方歷史上牢不可破的文藝本質觀念,直到19世紀才被動搖。
其次,模仿說的變化必然引起文學批評標準的轉移。既然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文藝模仿的目標,那么,在評價文藝作品的效果時,人們就不應當再著眼於事物的形式關係,而應當著眼於事物與人之間的效用或目的關係,這也就是蘇格拉底所謂“每一件東西對於它的目的服務得很好,就是善的和美的,服務得不好,則是惡的和醜的”9。蘇格拉底以前,在文藝欣賞領域,事物因其真而美;到蘇格拉底時期,事物因其善而美。換言之,蘇格拉底時期,文藝批評的標準已經由真置換為善。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雕塑師的兒子蘇格拉底何以在論述藝術時,竟是一個十足的道學家的口吻:“即使修克西斯給我看他親手畫的漂亮女人的肖像,它所給我的快樂,也抵不上我默想眼前一個女人的美德時所得到的快樂的一半”10。
蘇格拉底對文藝創作具體問題的論述只不過是他的模仿原則的引伸。他曾提出文藝創造理想性的特徵:“當你們描繪美的人物形象的時候,由於在一個人的身上不容易在各方面都很完善,你們就從許多人物形象中把那些最美的部分提煉出來,從而使所創造的整個形象顯得極其美麗”11。蘇格拉底在這裡談論的正是智者所說的使人“愉悅”的藝術與普通技術製作如工藝製作不同的地方:工藝製作在形式上並不刻意追求超出原物,“描繪美的人物形象”的藝術卻必須如此。換言之,塑造形象的藝術對自然的模仿不是照描,而是選擇中的變化與超越,這樣一來,藝術創作的界限就突破了前蘇格拉底時期自然模仿說的局限。這一思想為亞里斯多德所繼承,並在古希臘以後的文學思想史上不斷得到補充和發展,成為 現實主義文學典型化理論的前奏。
蘇格拉底畢竟只是一個過渡人物,他雖然扭轉了 古希臘文學研究的方向,但對一般文藝問題缺乏思考,對具體文藝問題的研究更嫌單薄,這與古希臘人豐富的文藝實踐是不相稱的。他未竟的事業是由柏拉圖接續,並由亞里斯多德最後完成的。
柏拉圖
柏拉圖全部思想奠基於“理念”這一核心概念之上,他認為文藝在本質上是對理念的模仿。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模仿說的精神,承認“詩的模仿術模仿行為著——或被迫或自願地——的人,以及,作為這些行為的後果,他們交了好運或惡運(構想的),並感受到了苦或樂。除此而外”“別無其它了”12。但他又從理念論的角度對蘇格拉底的模仿理論進行了改造。他認為“理念”是世界的最終根源,自然萬物的存在是模仿理念的結果,文藝又是模仿自然世界的結果,因此,文藝就像影子的影子,和理念的“真實隔著兩層”13。柏拉圖排斥文藝的認識論方面的原因,就是文藝在本體上離理念太遠,在實存上是對自然物的複製和抄錄,是比自然實體還要等而下之的東西。柏拉圖以精神實體理念作為藝術的最終根源,並把文藝貶低為比現實世界低一等的東西,顛倒了物質和意識之間的因果關係,這是其理論錯誤性的一面;但在這一“錯誤”的理論中卻又蘊含著兩個方面的“正確”的認識。第一,柏拉圖強調文藝是對實在之物的模仿時,他沒有意識到他在從發生學的角度論證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產生的直接根源;第二,當他堅持理念中心論,堅持文藝理念創造文藝現實時,實際上是在強調理想性高於現實性,藝術世界是人類在物質世界以外創造的第二自然,這又從價值論的角度抬高了文藝活動的意義。
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原則也是建立在“模仿說”基礎上的,只是其含義和性質與乃師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亞里斯多德確立了文藝模仿的本體地位,並使模仿說的性質發生了轉變。亞里斯多德指出,“詩的起源……出於人的天性。人從孩提的時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獸的分別之一,就在於人最善於模仿,他們最初的知識就是從模仿得來的)”14亞里斯多德這一認識是對柏拉圖文藝觀念的發展,它把文學創作活動歸結為人類先天具有的稟賦,從發生學的角度肯定了藝術創造是每個人類個體都具有的能力,這就給“人人都是藝術家”提供了明確的理論支持。在此意義上,亞里斯多德的模仿說是一種徹底平民化的藝術哲學。亞里斯多德這一認識使模仿說在性質上發生了根本轉變,模仿既是一種先天的創造能力,它就不再是一種偶然的自然行為( 德謨克利特),也不是複製自然對象的機械行為(柏拉圖),而是一種積極的創造活動,是人類知識(不是與真理隔了兩層的“影像”)的來源和文明的開端,這是對模仿說的最高肯定和讚賞。
第二,亞里斯多德明確限定了文學模仿的對象範圍,亦即文學作品的題材範圍。“詩人……必須模仿下列三種對象之一:過去有的或現在有的事、傳說中的或人們相信的事、應當有的事”15。“過去有的或現在有的事”,是指歷史或現實題材;“傳說中的或人們相信的事”,是指神話或寓言題材;“應當有的事”,是指理想的虛構題材。
第三,亞里斯多德指出了藝術模仿的審美心理效果,認為模仿是人產生快感的源泉。所謂“快感”,亞里斯多德認為“快感可以假定為靈魂的一種運動——使靈魂迅速地、可以感覺到地恢復到它的自然狀態的運動……凡是能造成上述狀態的事物,都是使人愉快的;凡是能破壞上述狀態的或造成相反狀態的事物,都是使人苦惱的。所以,一般說來,恢復自然狀態,必然是使人愉快的”16。模仿之所以能使人獲得快感,是基於亞里斯多德的知識觀。亞里斯多德認為,對周圍事物的茫然無知會讓人感到困惑和不安,從而導致靈魂失去自然狀態,對事物的認識則能解除這種不安的心理,使靈魂恢復自然狀態,從而使人感到心理的滿足和愉快。藝術模仿之所以會讓人產生愉快感,是因為人們在欣賞藝術品的過程中,從藝術品本身產生一種認知感,“即使所模仿的對象並不使人愉快……欣賞者經過推論,認出‘這就是那個事物’,從而有所認識”,從而使人產生愉快感,亞里斯多德據此推論,“繪畫、雕像、詩,以及一切模仿得很好的作品,也必然是使人愉快的”17。據此,我們不難理解,亞里斯多德為什麼會提出這種認識:某些對象本身(例如屍首或最可鄙的動物形象)看上去雖然令人感到討厭,產生不舒服的感覺,但是它們在藝術中得到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卻會引起人們的快感。18
第四,亞里斯多德揭示了藝術模仿的創造特質。亞里斯多德認為,藝術創造就是把事物的存在從一種形式轉換為另一種形式,例如詩人把事物的實體存在轉換為語言符號的存在。因此,藝術模仿不只是對實在世界進行複製和抄錄,而是在自然事物基礎上的自由創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偏離自然。
亞里斯多德的“模仿說”在西方文學史上影響深遠, 文藝復興時期的文藝家在同神學文藝觀作鬥爭時,就是以亞里斯多德的模仿說為武器的;18世紀,啟蒙思想家在與新古典主義文藝觀作鬥爭時,同樣利用了亞里斯多德的模仿說。
從學理的層面說,模仿說與古希臘哲學觀念的發展休戚相關。
總結
蘇格拉底之前,二元論的觀念尚未形成,各種事物都是同質的,這類似中國人所謂的“天人合一”觀念,這是早期人類思維尚未分化的共同特徵, 神人同形同性,神是人的肖像,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們沒有那種對於不可見的世界的神秘感覺,一切都是遷移和流轉,因而藝術毋須進行解釋性的創造,只需再現性的模仿即可。關於這一點,亞里斯多德在《物理學》中指出,藝術所以模仿自然,其根據在於萬物的起源都是互相關聯的,從而它們的活動和結果也是如此的。如果藝術能夠造成自然事物,它就一定要象自然那樣來活動。19因此,古 希臘人對任何不能用可見方式加以模仿的事物都不相信,在他們看來,文藝所再現的只不過是日常生活中的現實事物而已,而這些藝術所表現的日常現實事物同人的關係,也正是普通知覺對象同人的關係。因此,藝術的本質即在於它同日常經驗範圍內事物的關係是一種模仿關係,說白了,藝術是對自然實在的複製。模仿不過是人對他喜愛的東西想接近而進行的一種努力。柏拉圖雖然超越了自然本體論的一元認識模式,由於他把理念設定為世界的最高本體,是萬物產生之源,藝術不過是理念的映象和再現,因此,對藝術本質的認識仍然不得不用模仿說進行解釋。模仿說的流行,使得希臘時期的哲人們對藝術與實在的關係都擁有一種樸素的認識,因而他們都對創造性或想像性的藝術抱有一種敵視的態度,這種情形直到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中才得以改變。
模仿說,是最古老的藝術學說,認為藝術的本質在於模仿或者展現現實世界的事物,在浪漫主義興起之前一直占主導地位。“模仿”一詞源自古希臘語mimesis,自亞里斯多德始成為了美學和文學理論的核心用語。一個文學作品被理解為對——外在現實或者任何被描述為mimesis的方面——的再現。然而,亞里斯多德關於“模仿”的定義卻融合了如下兩重含義:其一,文學作品是現存現實的呈現;其二,作品本身就是一實體,並非僅僅是對事物的反應。前一種意義的模仿說竟主宰了西方近兩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