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桐城故里
桐城故里早期形態
明代方以智父子,以數衍易,醫易會通,從“質測即藏通幾”“立象極數,總謂踐形”的觀點出發,把律歷、象數、醫藥、占候……等都看作是“聖人通神明,類萬物,藏立之《易》”的“數理”(方以智:《通雅自序》);其“核物究理”、“探求其故”的易學思想,也可以說是走出中世紀的近代“科學易”的先聲。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當然,“科學易”的研究有一個理論和方法的導向問題。首先,在理論原則上,應當承認《易》之為書的原始形態,雖是人類智慧創造的一株奇葩,但畢竟是古老中華文化發蒙時期的產物。它本身必然是在科學思維的萌芽中充斥著宗教巫術的迷信,即使經過晚周時期《易傳》作者們的哲學加工,改變著其中科學思維、人文意識與神物迷信的比重成份,但仍然是原始科學與神物迷信的某種結合。因而,“科學易”作為現代形態的知識體系,必須將這種固有的科學與迷信的結合加以剝離,必須將傳統易學中某些固有的神秘性(各種拜物教意識、神物迷信等等)加以揚棄。這是十分繁難的任務。因為歷史地把握科學與迷信二者的區別和聯繫,了解二者既互相對立、排斥,又互相寄生、轉化的機制,以及二者能夠共生或實現轉化的思想文化條件和社會經濟根源,並非易事;且在實驗科學所憑依的工具理性範圍內得不到解決。其次,在文化心態上,應當看到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苦難和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衝突,在人們思想上曾造成各種困惑和畸變心理。諸如,面對西方科技新成就,希望“古己有之”的“西學中源”說,幻想“移花接木”的“中體西用”說,都是曾經流行過的思想範式,並在中國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歷程中一再把人們引向歧途。顯然,“科學易”的研究,應當避免再陷入這樣的思想範式及其種種變形,應當跳出中西文化觀中的“西方中心”、“華夏優越”、或“浮淺認同”、或“籠統立異”、或“拉雜比附”等等誤區,而在傳統易學與現代科學之間發現真正的歷史接合點,從中國“科學易”三百年來具體的歷史發展中去總結經驗教訓,提煉研究方法,開拓未來的前景。這一未來前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科學易”與“人文易”必須相輔而行,成為易學研究中互補的兩個主流學派。
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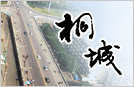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淵源
“桐城派”的淵源,其實質是桐城地方氏族,對中國文化的家族式貢獻。桐城東鄉的方、阮等氏,或自明至清,或自唐至明,累世簪纓。家族中歷世的文化傳承,最終才出現學術大家方以智,詩文(戲劇)大家阮大鋮。桐城方氏對中國文化家族式的貢獻,在中國歷史上除孔氏家族外,其他氏族無出其右。“桐城派”源流中的桐城姚、劉、吳等氏中的諸經典作家,或為當時方氏世戚,或因文章、學問為方氏至友。這些辰星般四處閃爍的“桐城派”成員,向心點仍在浮山方氏。從這個意思上講,方苞無論生活、成名於何處,綱目關係沒有改變,他都是浮山方氏氏族文化上的一顆新果實。而學派中的其他重要成員,或利益於這種直接傳承,或利益於這種氛圍薰陶。至於今天流傳的何處“出人”、何處“出名”之說,未免流於膚淺。
流派特徵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主要代表
除創業者方學漸,代表者方以智及中間人物方大智、方孔火外,桐城方氏學派的主要人物尚有:吳應賓、三宣、錢澄志以及方以智的三個兒子中德、中通、中履和方以智的學生揭喧、遊藝等人。這些人物,或是師生同學關係,或是血緣關係、或是連婚關係,凝聚力極強,因而這個學派比明末清初其它學派更有內部的穩定性。
方以智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方以智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方以智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又號鹿起、浮山愚者等,兼有別號多種,是明末清初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方以智是安慶府桐城縣鳳儀里(今屬安徽省樅陽縣)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方大鎮,曾任萬曆朝大理寺左少卿,治《易經》、《禮記》,著述宏富。父親方孔炤,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崇禎朝官至湖廣巡撫,通醫學、地理、軍事,有《全邊略記》、《周易時論》等著作,《明史》有傳。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學,接受儒家傳統教育,曾隨父宦遊,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寧、河北、京師等地,見名山大川,歷京華勝地,閱西洋之書,頗長見識。成年後,載書泛游江淮吳越間,遍訪藏書大家,博覽群書,交友結社。曾與陳貞慧、吳應箕、侯方域等主盟復社,裁量人物,諷議朝局,人稱“四公子”,以文章譽望動天下。
方學漸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