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忘卻魚鱗原名林偉奇,出生於廣東沿海,水瓶座。主修工業設計專業並擁有多項國家技術發明專利。
 忘卻魚鱗
忘卻魚鱗主要作品
著有長篇小說《關於彼岸的一切》、《絲絨公路》、《昨夜何處安眠》、《蜥蜴》、《再見,彼得潘》、《最後一個新朋友》等作品。
《關於彼岸的一切》
主要內容作品借2003年“火星沖”事件講述了幾個關於愛、關於孤獨、關於流浪、理想以及宿命的故事。講述了主
 《關於彼岸的一切》封面
《關於彼岸的一切》封面“火星年”來臨時,他們被宿命般不可知的力量推動下開始分裂,有人深入塔克拉馬乾沙漠尋找所謂的“時間的終極”,有人選擇了逃避,只有對火星的關注成為了彼此共同的精神寄託。
在整個世界生生不息的循環面前,在瘋狂與毀滅的洗禮過後,他們都必須在各自迷惘和孤獨的道路中重獲生活的勇氣。全書寫法新穎,結構精緻靈活,以略帶使命感的筆調,描述了當代青年光怪陸離的生活圖景。在對自身審視和追尋的呼喊背後,更是年輕一代孤獨且堅韌的內心寫照。
編輯推薦
這是一封長長的信,一次久違的感動。
這也是新生代新銳作家忘卻魚鱗的處女作,一出手即形成強烈的氣場。拋棄了技巧和陳規陋習的寫法讀起來清新質樸,卻散發著激動,傷感的味道,將奇幻與現實,明亮與灰暗,微妙地交織在一起,編成一張疏密有致的網,於是有光有影,帶著豐沛的神采。
“住在孤獨又腫脹的地球之上,遙望並嚮往安靜的火星。” 帶著淡淡的奇幻意味,故事由此展開,只有一個作者靠著純粹的情緒和真誠態度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外表是層出不窮的意象和顏色,核心卻蘊涵著巨大力量,它試圖走出一般青春小說的範疇,去探究更廣闊更深刻的世界。
為了給讀者更多驚喜,作者更是親自設計全書的裝幀,收錄了“SKY的沙漠來信”以及其他相關花絮。
如果您想全新的閱讀體驗。
那么,享受它吧!
“我們生活在一個硝煙無處釋放,刀箭任意生鏽的時代。”
這是我在海珠區一間小書店裡面讀到的一句話。那一年夏天的天氣無比炎熱,高達40攝氏度。太陽以暴君般猛烈的姿態呈現在整個城市的上空,散發出令人灼痛的巨大能量。然而廣州街頭的人群依然浪潮湧動,人們因為高溫而變得焦躁不安,擁簇著互相碰撞。這是有史以來最熱的夏天,所有的一切官能感知都失去了敏銳,變得滾燙而遲鈍。
在這個鋒刃遲鈍的年代,或者說至少是一個令人遲鈍的年代,我曾經渴望投入某種無可救藥的戰鬥中去。但不得不承認在頭部撞到冰冷牆壁的時候內心有過叫囂,那一刻,破裂的腦殼中噴湧出滾燙的鮮血,我才明白真相還在無法觸及的地方,它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告訴我什麼是冷酷生活。而且僅此而已,再無他意。
山火蔓延過側嶺,是暮色猙獰到最濃烈的時候,空氣中充滿不安的味道,漫天飄來無數零散黑色的灰燼,隨風飛舞。我先是看到遠處天空被曖昧的猩紅染透,後來藉助帶虹膜的軍用望遠鏡在7公里外看到那座山。現場附近的景物已經在熱浪中扭曲變形,成為一面凹凸不平的鏡子。樹木開始痙攣,散發出濃煙。
晚風吹來,浩劫真正開始了。樹冠上慢慢形成了巨大的火球,騰空飛起,猶如長了翅膀的魔鬼一樣跨過未點燃的區域。在通紅的夜空下,整個森林被洞穿出一個巨大裂縫,其中洶湧出濃郁的毒液,致命的刺痛在叢林中迅速蔓延。一切生物的意志都在濃煙和焦躁的氣味中沉淪崩塌。
我站立的窗戶正臨街,遠處黑暗的山下,警笛呼嘯,灰燼隨風飄灑,飛舞著飄落在我的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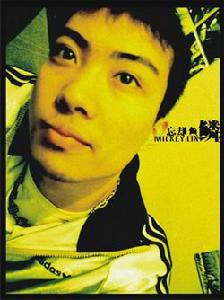
我無法看清楚他的面容。他的臉沉沒在薄薄的熱氣流中,需要非常仔細地辨認,才能隱約感覺到他臉上輕微的笑容,在黑色的齊肩長發中若隱若現。
火滾動著爬上他的牆壁,被短暫地擋在木板門外,他相鄰的棚寮已經在煙霧中倒塌。門漸漸被燒穿,在漸漸明亮的光線中,我終於可以一點點辨認出他的樣子,他的額頭,眼睛,嘴唇,下巴,肩膀和腿的形狀,直至全部輪廓。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形象,他始終帶著含糊的笑容,在一個抽屜模樣的台面拿出一堆雜物,就著牆壁上的火點燃。書籍,信箋,各種各樣的東西被他一件件點燃。動作利落,態度從容,絲毫沒有想要慌張逃離的
……
《絲絨公路》
書摘| 親愛的,路還很長 不要睡去,不要 不要靠近森林的誘惑 不要失掉希望 請用冰涼的雪水 把地址寫在手上 或是靠著我的肩膀 度過朦朧的晨光 撩開透明的暴風雨 我們就會到達 |
去年秋天,我在一個嘴角有一道疤的小個子傢伙被子底下偷過一本書,書名叫《深淵書簡》。聽那名字很容易讓我以為是那種讀了能讓人為之激動的書,所以我就偷了。在這裡要解釋一下,我太他媽的想看點讓人激動的東西了,因為我一直過著令人沮喪的生活,我聽不到喜歡的音樂,看不到想看的電影,我只能逮住點機會,到處弄點書看看。
但事實是,這書看起來並沒有像他的名字那么牛,是一個莫名其妙蹲監獄的傢伙寫的信。在書的最後兩頁我看到他的照片,長得不怎么討人喜歡,太陽光了,女的倒是無所謂,我最討厭長得很陽光的男人,名字倒是起得不錯,叫奧斯卡.王爾德。
我能記得他,是因為他說了一句非常牛逼的話:人的真正生活常常不在現實中。這話說的太他媽對了,比瓦西里還準確,一擊即中。是的,我的真正生活應該是在工人體育場,紅堪體育場,發白金唱片,或者說至少是在錄音棚,在排練房,在全國巡迴演出里度過,而不是過我現在這種日子。
我十八歲了,浪費了太多的時間。約翰列儂十八歲已經認識了辛西婭並開始做他的“甲克蟲”了。蕭邦十八歲已經是波蘭公認的鋼琴和作曲家了。而我十八歲生日卻是在這個烏龜都不拉屎的地方度過的。我父親把我送進了這個破地方——在一片不毛之地的郊野上用舊廠房改造成的學校。有一個很讓人鄙視的名字,叫“東亞教育培訓學校”。聽起來像日本軍國主義搞的某種卑鄙的實驗,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一個更加愚蠢的項目,叫“擇差教育”。
OK,嘲笑我吧,沒什麼。來這裡的人都被貼了標籤打了烙印,我們比王爾德同學還冤,送到這裡來是因為有網癮、厭學、早戀等等,叫問題學生。這學校大放厥詞稱其是通過軍事化管理來鍛鍊學生的意志,規範學生的行為。
在我看來這當然是狗屎,腦袋變成未來水世界的人想出來的勾當,有網癮的傢伙可能成為比爾蓋茨,他也厭學不是嗎?早戀的傢伙就更牛比了,莎士比亞就是這么出來的。而我的理由更加可笑,我身上紋了文身,我長頭髮,打了釘子,我是和學校幾個白痴打了一架,我還反抗了一個侮辱我的老師,我們內部稱這個為“拒捕”,但我的行為高一個級別,叫“襲警”,對方進了醫院,教務主任生氣了,後果很嚴重。SO,我被開除了。
 《絲絨公路》封面
《絲絨公路》封面我被送進這裡,這裡沒有和平,只有衝突。這裡沒有老師,帶我們的叫“教官”。也沒有同學,我們不叫名字,我們像他媽的伊夫堡監獄裡的犯人一樣,都用編號來代替名字。我靠,你不相信吧,但是事實就是這么可笑,我的編號是8746,哈,我猜我要是叫47的話,我也會像復仇的伯爵唐太斯那樣臉色蒼白的。
因為我是以“愛打架的壞學生”名義送進來的,所以我第一個星期就被教官指導了一頓,他用的是他的皮帶,我的釘子被拆了,頭髮被剃光了,穿著統一的工人服一樣的校服,他讓我脫光了外衣,對著我的文身猛抽。每天教官會檢查我有沒有用砂紙把我身上的紋身一點點磨掉,我必須每天讓他看看我塗著紅藥水的手臂,一開始傷口一直化膿,現在上面的紋身已經成了一塊塊疤。
“就是要磨磨你的銳氣。”教官很滿意地說,他說這話的時候很自豪,以為自己說了一句很有內涵的話。一般情況下他不會講這么裝逼的話,他會坐下來讓我做伏地挺身:“現在十點,做到十二點。”接著他就開始翻我宿舍的東西,我總會做半小時之後就裝出快死了的表情,他最開心的就是看到我痛苦的樣子,一直看到他覺得開心夠了,才會像一個滿足的婊子一樣挪動他的大屁股走人。
這裡的讓我們幹的大概就幾種:半夜跑步、伏地挺身、用拳頭打樹幹。文化課是自習,心理課是看《鐵道游擊隊》和《開國大典》。責罰人是用皮帶抽、電線抽、洗廁所。如果抽菸被抓到,就要把剩下的煙都生吃掉,沒錯,像嚼樹根一樣把菸草吞進肚子,這些雜種什麼辦法都想得出來,他們聲稱這叫“內部消化”。我作為一個打架的學員,對於他們來說反而是受尊敬的,除了挨打之外不會對我做太侮辱人的事情。而那些可憐的莎士比亞和比爾蓋茨們可就苦了,教官最看不起這樣的學員,我就親眼看到一個莎士比亞被逼喝下了一刷牙杯馬桶里舀上來的水,那個傢伙喝完之後哇哇大哭。
“你不是人!”號碼是3986的莎士比亞大喊一聲,說時遲那時快,啪!他臉上就結結實實被教官摑了一巴掌。
我說不清楚自己多少次看到他們這樣打人,像一個來自中東的激進分子。也許他會對我持同樣的意見,可是在我的記憶里,我始終是個和平主義者,我寫過很多宣揚愛的歌曲,我只是偶爾陷入暴力,在我看來這學校里的教官們才是戰爭販子,他們才是真正勞動人民的敵人。當然他們也經常對我進行武鬥,可能是我剛來的時候留給他們的印象太深刻了,長頭髮,打著釘子紋著文身,異教徒落到掌握權利的衛道士手裡總是沒有好下場的,哥白尼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他們揍過我之後,了解到我是一個因為打架被送進來的而不是要成為莎翁和比爾蓋茨那樣的傢伙,就對我有了片刻的理解,我想他們也許感到微小的認同,猶如故友重聚,昔日重來……
評論(之一)
這是一本幽默風趣又不禁讓人心酸的作品,通篇調侃的語氣,輕快的筆鋒,即使對於不大喜歡讀書的人來說,也很容易就進入文中的氣氛,給你帶來的閱讀快感。當然,作者所闡述的卻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話題——成長,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生命中總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它們會等到你人生的某一個特定階段才突然跳出來,像觸電一樣把你的心一次次擊穿,看《絲絨公路》就是一個被擊穿的過程。
《再見,彼得潘》
書摘我一點點遠離它
Never-Never-land
那片永遠無法到達的大陸
在我離開很遠之後.
時光燃成灰燼.嘩嘩作響.
在陰暗的天空下.
它終究要枯萎.
獻給消失的Never-land
 《再見,彼得潘》封面
《再見,彼得潘》封面很久以前的一個冬天夜晚,漆黑空曠的街道上飄起毛毛細雨。我與一個女孩做最後的送別。她在進入捷運口之前,留給我一把傘。離開她之後,我撐開她給我的傘正準備朝相反的方向獨自回家,這時候一個站不遠處避雨的陌生老太太,她向我走來,用非常緩慢的語速問我,是否可以順路遮著她送她回家。
她穿著一身黑色的衣服,眼神溫和但是嘴角卻有著僵化的線條,額上刻滿了深深的裂痕。我看著她,接著又看著馬路上潮濕陰沉的景象,她背後的天空隱約飄來一片片濃厚的黑雲。我答應了她,將傘舉在我們中間,緩慢地走出去。
那是一個平靜的夜晚。至今我依然記得那一切,那個猶如蒙克畫中陰鬱的背景般的夜裡,我與那個陌生的老太太並肩走在冷洌的雨中,離別帶來的惆悵籠罩著我,虛無和失落感在我的心裡慢慢膨脹,瀰漫在四周黯淡的空氣中。我們安靜地走到她的家門口。在即將離開的時候,這個陌生的老太太抬起頭注視著我,她對我說:年輕人,謝謝你。我想對你說,不要輕易去看女人離去的背影,除非萬不得以,因為只要你看了,你就會很難忘記她。
我本就沉浸在離愁別緒之中,只有側著頭微笑著看她,無言以對。
她轉過身去,說:沒什麼,你只要再回頭看一次,就會有些東西被帶走的。
她隨後隱沒在黑暗的房子中,許多年過去了,我依然在回味她給我的忠告。也許她說的對,有些東西被帶走了,但是我也知道,有些東西留了下來,在我的心裡深處,那會是一個形象,我從來不曾試圖描述過那種形象,但是我希望它能一直留在我的心中,無論我走到哪裡,經歷過什麼,只有它在那裡,我就可以找到我自己,找到那些被帶走的東西的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