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況
作品原文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預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燈罩很昏暗。鞭爆的繁響在四近,菸草的煙霧在身邊:是昏沉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著《初學記》的手擱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著,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仿佛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著的衣裳,和尚,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著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並水裡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於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著日光,發出水銀色焰。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裡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如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著。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里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仿佛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剩著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里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作品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1925年《語絲》周刊第十三期。本文本據新版《魯迅全集》修改,即“……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一句,據多方考訂應為:“……忽而碎散,拉長了,如縷縷的胭脂水”。②《初學記》,類書名,唐代徐堅等輯,共三十卷。取材於群經、諸子、歷代詩賦及唐初諸家作品。③山陰道指紹興縣城西南一帶風景優美的地方。《世說新語,言語》里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④伽藍,梵語“僧伽藍摩”的略稱,意思是僧眾所住的園林,後泛指寺廟。⑤一丈紅即蜀葵,莖高六七尺,六月開花,形大,有紅、紫、白、黃等顏色。
作品鑑賞
在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中,有幾十處寫到夢境,大多數夢境都是描寫惡夢,而《好的故事》則於昏沉的背景之中,為我們打開了一種帶著明亮的暖色和淡淡的溫馨的回憶畫卷,表達了魯迅思想深處的那種執著的美好追求。
文章起於昏沉的夜,結於昏沉的夜。而在這起結之中,以漸漸地縮小了的燈火,燃起了一種美好的希望,展開了一幅美好的回憶圖景。
《好的故事》一如它的篇名,呈現出一種非常美好而又明快的美學意境,作者讓我們“看見一個好的故事”中“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著,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文章開頭就為全篇奠定了明快美麗的感情基調,而“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以至於無窮”一句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文眼。
在展開的過程中,作者將那些帶有明快色調的意象一一攝入:烏桕,新禾,野花,叢樹,天,雲,竹,閃爍的日光……而且,“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著日光,發出水銀色焰”。這些意象的鋪敘與描寫,引領讀者進入到一種賞心悅目的明朗意境之中。
接著魯迅仍然以明快的筆調,寫到暖色調的事物:水中的青天的底子,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剌奔進的紅錦帶……
在這幅“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的畫卷中,作者的思想感情也產生著一種層次性的變化:先是於昏沉的夜裡懨懨欲睡,再接著,“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然後,感受著“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以及“我就要凝視他們”都在表達“我”的感情漸向高峰與高潮狀態掘進的過程。於是,即使“雲錦也已皺蹙。凌亂……眼前還剩著幾點虹霓色的碎影”,“我”還要“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去記下它們,最終則是:“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伴隨著感情的層次性變化,背景同樣存在著一種層次性的改變。
一開始處在昏沉的夜,是在燈火漸漸地縮小了的灰暗背景中,然後漸漸明亮起來,次第寫到“蒙嚨”、“閃爍的日光”、“清楚起來”、“分明”、“皺蹙”、“凌亂”、“影子撕成片片”、“碎影還在”,最後又回到那“昏沉的夜”里的凝視與沉醉,完成了一個美好故事的迴環。
作者在極短的篇幅中,從多個角度,且每個角度都從多個層次來展開那種超現實的想像,這就使得《好的故事》中暖色的想像和回憶具有了一種明快清晰的美學風格。
文章中視覺形象的奇特和豐富令人驚異,而且這些視覺形象令人應接不暇地互相疊印、融合。超現實想像賦予了文章本身以詩的美學表征,而夢中美的境界又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難得的閱讀記憶。在這美好的故事中,所有的形象都在表達諸多抽象的觀念,這就使《好的故事》永遠呈現出開放的、多層次的審美境界。而這樣的審美境界,散文名家方令孺在其名作《在山陰道中》認為,魯迅先生的《好的故事》,正是魯迅先生所想望的好的生活。
熟悉魯迅生平的人應該知道,《好的故事》是以從紹興西南偏門出城,經鑑湖、婁宮而到蘭亭那條路上的風光及歷史為背景而寫成的。1913年6月24日,魯迅在長住北京後第一次返鄉省親,6月26日,他“同三弟至大路浙東旅館偕伍仲文乘舟游蘭亭,又游禹陵。歸路經東郭門登入,步歸。”(見《魯迅日記》)魯迅之弟周建人後來也曾回憶起那天的情景:他們在蘭亭逗留的時間較長,他們乘一隻烏篷船,出偏門經鑑湖到婁宮上岸,到蘭亭還要走十里旱路。兄弟凡人觀看王羲之手書的“鵝池”石碑。遊覽右軍祠、墨池、御碑亭、流觴亭和亭前的流觴曲水,遙想著晉朝的丈人墨客在這裡飲酒、吟詩作賦,讓酒杯隨著曲水徐徐流動的閒情選致。
魯迅在1919年12月24日最後一次離鄉返京之後,再也沒有機會踏上他所熱愛的故土。然而,在1925年寫就的這篇名文里,我們分明感受到他與著名的山陰道在精神血脈上一直保持著須臾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對家鄉風物刻骨的追憶,就這樣化為一個永無止境的“好的故事”,烙在了魯迅審美精神的空間。
嚴格地說,魯迅從十七歲便離開了故鄉。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和民族的希望。離開三味書屋,是他不悔的選擇;但棄醫從文,卻是他無奈的追尋。然而,在那時“狹小而黑暗的隧道中”,他始終相信並堅守自己的信仰與追求,因而,在這狹小而黑暗的隧道中除了有“狹小而黑暗”,有沿途的崎嶇與辛酸,同時也有著非常濃重、濃厚的故園情懷與明亮記憶,一直閃爍在魯迅的精神空間。關於這一點,《故鄉》中的少年閏土,《社戲》、《阿長與山海經》、《藥》(特別是瑜兒墳上的花環這一細節)等均可為證。
魯迅先生用如此暖色的筆觸來描寫他的想像世界和回憶中遙遠的故鄉,不僅是一種精神慰藉,更是一種美好的人生信仰和堅執的人生追求,因為,這裡仍然有著魯迅的另一種韌性:“好的故事”就在明天。
因此,像“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這些表達抒情主人公執著追求美好境界的句子,也就成為我們深入理解這篇散文詩的通道。
作者簡介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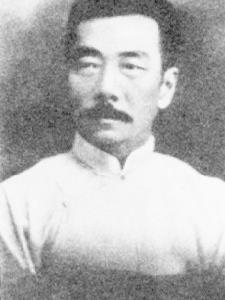 魯迅
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