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夾邊溝,地名,
位於中國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這裡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 這是一個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想像的“右派”苦難史。
這個位於甘肅酒泉戈壁灘里的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凍間,一場罕見的大饑荒很快將這裡變成了人間煉獄。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在吃盡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倖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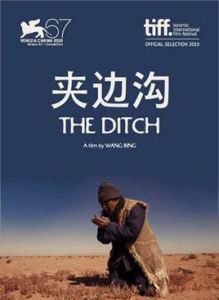 夾邊溝
夾邊溝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據天津作家、《夾邊溝記事》作者楊顯惠的調查和當事人回憶,夾邊溝農場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說,甘肅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
當1961年初夾邊溝倖存的“右派”被分批釋放回家時,一位醫生留下來負責給2000餘名死者編寫病歷。他們被貼以各種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臟病復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均死於飢餓。
“右派”們的遺骨被1969年後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里。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中國作家楊顯惠根據自己的文學生活積累進行創作,著有《夾邊溝記事》中篇小說一書,專題用文學的手法描述這段歷史。在他的文學敘述中,夾邊溝農場那段塵封的歷史,從1957年開始,這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幹部、知識分子在這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數人在此期間被活活餓死,其慘烈程度超越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三千名右派活著出去的只有四百多人。
事件真相
夾邊溝農場
夾邊溝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這個位於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昔日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 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么多人。 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後,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飢餓。 管教人員大多出身行伍,他們對西北地區的農業生產知識不甚了了,於是一年四季里,幾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體能的農活,同時輔以生產競賽,讓那些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12小時甚至16小時。
 夾邊溝的窩棚
夾邊溝的窩棚1957年7月,甘肅省委決定,把本省部分開除公職的右派分子集中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由張掖地委管理。
夾邊溝農場的前身是甘肅省勞改總局於1954年開辦的一個勞改農場,位於酒泉縣東北,夾山之南,長城之北,面積200多平方公里,因附近有夾邊溝村而得名。1957年已開墾耕地9000畝,初具規模。省委決定改為右派勞教農場後,1957年9月便把勞改犯人全部遷出,11月勞教右派開始往夾邊溝集中,至1958年3月已近2900人,到10月更增加至3056人,概稱“夾右三千”。“夾右”一詞由此而來。(“夾右”指右派)
1958年正常勞動生產,生活較好。1959年農場建立二周年,有政策說要給勞動好、改造好的人摘帽子,所以勞教人員熱情很高,積極勞動,認真改造,對摘掉帽子繼續為黨為人民工作抱有很大希望。
 茫茫夾邊溝
茫茫夾邊溝但是由於受極左路線由上而下的干涉,農場領導在1959年5月1日的“三千人大會”上只宣布了三人摘帽。按兩年摘三個帽子的速度推算,全場三千人帽子摘完要兩千年!(這就是《詩抄》中“摘帽兩千年”著名詩句的來由!)夾右的情緒一下跌落至最低點。到8月底,全場死亡110多人,死因是憂鬱、氣憤、想不開。
1959年8月,張掖地委第一書記安振仿效省上“引洮上山”工程,決定修建迎豐渠,把黑河(發源於祁連山,是張掖也是河西第一大河流)水引到明水灘,開辦一個50萬畝地的大農場。“引洮上山”和“迎豐渠”工程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脫離實際、脫離科學的產物。
安振左傾蠻幹,一意孤行。一方面徵調高台民工12000人上馬迎豐渠;一方面把夾邊溝農場遷址明水灘,放火開荒,建“50萬畝大農場”。
1959年10月底一場特大暴風雪,凍死迎豐渠工地民工1200人,工程被迫停建。
飢餓
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飢餓。 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他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藉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7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他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在死神面前,人們開始了求生本能的掙扎。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下一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他們只能煮乾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一天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掉,它的內臟被飢餓的右派偷吃了。
 夾邊溝
夾邊溝在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人,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裡。他們使勁兒攪動人頭,使得嘴裡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裡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咽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瀉,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顧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學美國的博士,水利專家。他是由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叫回來報效祖國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後來被借調到甘肅進行規劃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內向,不善言談。在反右運動中,別人開的玩笑話“引洮工程是銀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沒有治出來,共產黨能治出來嗎?”硬栽到他頭上。傅作恭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
就在這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后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乾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夾邊溝
夾邊溝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在書中寫了這樣一個場景:“……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
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蹟: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裡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蒐集獸骨……”
人吃人
他什麼都吃,到處偷著吃。在荒灘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窩裡的存糧。運氣好時,他能從一個耗子洞里挖出四五升糧食。 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死神面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勞動停止了,所有人在夾邊溝存在的惟一意義,只在於活下去。人們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無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後活活被鼓脹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死者的遺體被餓得發狂的人們從沙地里扒出來,開腸破肚掏出內臟,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後面用乾草燒著吃,也有悄悄焙乾了存著慢慢吃的。俞兆遠也吃過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後他已完全記不得是何種滋味。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中記載,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
 夾邊溝
夾邊溝被場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裝貨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水溝里的地窩子和窯洞裡。
更慘明水灘
 地窩子
地窩子明水灘在高台縣境,東西長30公里,南北寬10公里,面積300平方公里。這一片荒原,因中間有一條季節性小河——明水河而得名明水灘。明水灘雖有廣袤的土地資源,但當時卻沒有任何生活和生存條件。三千夾右委身荒野,只好打土洞存身。迎豐渠被迫停工了,明水灘的三千夾右卻被安振棄而不顧。加之全國、全省和張掖地區經濟形勢嚴重惡化,夾右糧食定量一減再減,到了59年11月已經降至每人每月14斤。明水灘上每日都有人凍餒而死,一天死幾人、十幾人、最多一日連死30人。
到了明水之後,這些人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死神無情地降臨到他們頭上。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誰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幾個犯人怕什麼?乾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
由於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埋人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人們稱之為“鑽沙包”。
事件改正
1960年11月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中央工作組來甘徹查左傾錯誤路線問題,11月11日到明水了解右派情況。錢英慰問夾右說:“同志們受委屈了!”並當即決定提高其糧食定量標準,標誌著解救夾右的開始。
錢瑛(女)湖北鹹寧人,1927年參加革命,1931年在洪湖地區建立游擊隊,系歌劇《洪湖赤衛隊》主角韓英的創作原型。建國後一直在黨和國家的檢查、監察機關擔任領導要職。
 夾邊溝倖存者
夾邊溝倖存者960年12月3日至5日,西北局在蘭州召開了書記處會議(西蘭會議),清算了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左傾蠻幹的錯誤路線,在這以前,安振也已經被停職檢查。1960年12月23日,西北局工作組在張掖與張掖地委常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明水灘上還活著的700多名右派解救休養。12月25日,地委組織部派遣車輛去明水把倖存者接出。在明水灘上,短短的時間內,餓死右派人員2100多人,釀成震驚中外的夾邊溝(明水灘)事件。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了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了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夾邊溝農場被撤銷。
1957年7月,甘肅省委決定,把本省部分開除公職的右派分子集中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由張掖地委管理。
同名電影
 夾邊溝
夾邊溝《夾邊溝》,電影名稱。根據楊顯惠小說《告別夾邊溝》改編,中國導演王兵拍攝的首部故事片,根據楊顯惠小說《告別夾邊溝》改編,由中國、中國香港、法國和比利時四地聯合製片。
編劇:王兵
導演:王兵
主演:徐岑子
製片國家/地區:中國大陸/法國/香港/比利時
上映時間:2010-09-06
語言:國語/國語
又名:告別夾邊溝/再見夾邊溝/ilfossato
劇情簡介
改編自紀實文學、由王兵執導的《夾邊溝》以驚喜片的身份入圍第67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而本片也將與徐克的《狄仁傑之通天帝國》一起,代表華語勢力爭奪本屆金獅大獎。
 夾邊溝
夾邊溝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夾邊溝》,是一部冷峻、直接的電影,幾乎沒有任何迴避地回顧了那段歷史。王兵將紀錄片創作的美學引到故事片中,用獨特、自信的視聽語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後,人間地獄一般的夾邊溝勞改農場發生的故事。
《夾邊溝》根據楊顯惠小說《告別夾邊溝》改編,原著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礎,但由於事件的隱蔽性,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地揭示真相。王兵在創作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和資料,他之前拍攝的長達三個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就是以夾邊溝事件的倖存者和鳳鳴口述作為載體,記錄了個體數十年的人生經歷。
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夾邊溝》,是一部冷峻、直接的電影,幾乎沒有任何迴避地回顧了那段歷史。王兵將紀錄片創作的美學引到故事片中,用獨特、自信的視聽語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後,人間地獄一般的夾邊溝勞改農場發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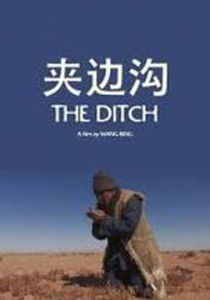 夾邊溝
夾邊溝 王兵自幼喪父,看楊顯惠《夾邊溝紀事》後,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不知道這是不是他創作該片的動機。影片在2008年10月開始拍攝,2009年1月完成,歷時75天,積累了130小時的素材。
儘管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飢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寫實的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
電影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地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犯人極度麻木,在這裡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犯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裡死去,在這裡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夾邊溝
夾邊溝拍攝紀錄片存留下的長鏡頭美學,在《夾邊溝》中也得到了切實的體現。王兵關注聲音的空間層次,從頭至尾沒有音樂,關注畫面景深的處理,關注空間、景別、用光的變化和節奏,有條不紊地鋪陳故事。雖然採用手持攝影,但畫面的運動保存了強烈節奏感和控制力,幾乎每一個鏡頭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調度。但由於某些原因,一些鏡頭的剪輯和創作還是有不是那么嚴謹的處理,但瑕不掩瑜。
《夾邊溝》最大的意義在於,用電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歷史。也許這不是事實的全部,但足以讓人難以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