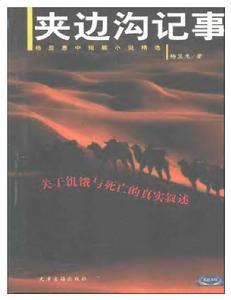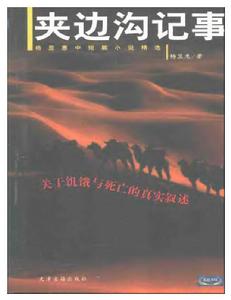 《夾邊溝紀事》
《夾邊溝紀事》簡介
夾邊溝,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多年來,默默無聞,不為人知。但是,40年前這裡發生的一場人間慘劇,使它注定不能被歷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遺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裡,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記。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屍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連續發表20多篇紀實作品,一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夾邊溝農場從1957年4月開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搶救人命”,三年半時間裡,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
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 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 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后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乾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甘肅省勞改局的計畫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高台縣明水那片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面積50萬畝。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倉促上馬,其它農場沒有按計畫調人,只有一向“表現積極”、“寧左勿右”的夾邊溝農場調過去了1500多人。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山水溝里的地窩子和窯洞裡。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云:死幾個犯人怕什麼?乾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據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里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
“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就在右派被遣返後,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飢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作者簡介
楊顯惠是甘肅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農建十一師當農工,也就是早期的知青,他還當過售貨員,會計,民辦教
 楊顯惠
楊顯惠有一種近乎天生的酷厲而蒼涼的美。九十年代以來,他沉寂了很久,近年《夾邊溝紀事》系列發表。
《夾邊溝記事》之不同於某些同類型的反思作品,它遲至新世紀之初才公諸於世卻不覺其過時,反倒有種振聾發聵的新鮮感,首先因為它的高度的真實性——不僅是人物、環境、事件的真實,更是心靈的甚至潛意識的真實。前此的某些作品,總叫人覺得經過作者的處理與調和,使嚴酷的歷史變味了,或美化了,或鈍化了,總之是變得“好接受了”,儘管作者也在大聲疾呼,但總覺隱去了一些什麼。《夾邊溝記事》不是這樣,它有一種中國史家傳統的“不虛美,不隱惡”的秉筆真書精神。從它發表後的一些反映,不難看出其力度。然而,我們且不可忘記,《夾邊溝記事》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的基礎,但它們畢竟是藝術品。
發表意義
事實上,《夾邊溝記事》之所以不同凡響,是因為它完成了一種超越和提升:它在高度忠實於歷史事實的真實的基礎上,通過對許許多多飢餓與死亡的慘烈場景的刻骨描繪,通過對眾多受難者命運的來龍去脈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過對他們在絕境中人性常態與變態的出色狀繪,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張力和罕見的概括力,不但表現事實本身的駭人聽聞性,而且表現這一歷史悲劇的精神本質和沉重教訓。
說它有超越性,是因為夾邊溝雖屬荒漠絕塞的禁地,但在作者筆下,它與整個社會的神經還是息息相通的,它的教訓是全社會的,只是更極端而已;說它有所提升,是因為發生在夾邊溝的慘劇,無疑是極左政治路線的產物,但在作者筆下,突出的是精神化、人性化的悲劇。在紀實外衣之下,作者完成了由外化到內化,由事件化到心靈化的位移,而這是更具有人性內涵和文學意味的。
作為一種藝術創作,由於事件本身長期的隱蔽性和一朝揭開真相帶來的震驚,由於素材來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這部以夾邊溝事件為原型的作品很難不採取紀實小說的方式,它甚至也無法擺脫採訪體和轉述體等等新聞手法的運用。應該承認,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來自基本事實的驚人,但是,倘若沒有作家主體的創造性重構,也絕不可能擁有現在這樣強烈的震撼力。
《夾邊溝記事》最大的特點還在於對生命的珍重,對人的權利和尊嚴受到深重傷害的深層次表現——主要不是從政治的層面,而是從文化的和人性的層面。作者筆下的人是複雜的,兼具感性與理性,意識與潛意識的豐富人。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對丈夫的一腔忠貞,她完全不明白這場橫禍,怎么來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螻蟻一樣說餓死即餓死了,死後拋屍荒野無人收。她帶來的食物分給諸難友的爭搶場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現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嬌弱,越是顯現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與荒涼的夾邊溝形成強烈反差,她幾千里尋夫、哭夫、直至堅持背回丈夫遺骨的行為就越是讓人肅然起敬,作品悲劇性的控訴力量也就越強。小說的結尾很妙,多年後,小說的敘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尋覓這位上海女人終又放棄了尋找,上海女人遂從作品中徹底逝去,給讀者一個悵惘的遐想空間,可謂餘味無窮。事實上,《逃亡》、《飽餐一頓》、《賊骨頭》《夾農》《李祥年的愛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淚下之作?
曾有多位死難者家屬告訴作家,雖然他們身處偏遠的西部,還是發現了《上海文學》上的文章,他們一頁頁地讀,一頁頁地哭,將文章收集起來,清明節上墳時焚化以告慰冤魂。從夾邊溝九死一生逃出來的八十二歲的裴天字老人說,他的一位在大學裡當教授的學生給他寄來了四本《上海文學》,他用了半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傷心得讀不下去呀!沒有充分的真實性是不可能具備這樣的效力的。
|楊顯惠為了寫好這本書,每年數次往返於天津和甘肅之間,耗去了整整五年時光。他居然不可思議的、大海撈針般的搜尋到了近百個當事人。採訪老人是需要特別的耐心的;作者還須查閱大量資料和進行實地考察。這一切基本都是在自費的情況下進行的。可以想見,要完成這樣一次漫長的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效益可言的寫作,需要具備怎樣頑強的意志和持久的韌性啊。這必然是懷抱著良知,信念的寫作,這必然是懷抱著深刻揭示歷史之謎和人性之謎的激情寫作。真所謂: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