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的由來和涵義

土爾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們自古就生息在我國北部西部的森林和草原,是一個勤勞、勇敢,有著光榮歷史的部落。每一個民族都由部落形成,每一個部落都有他的名稱和涵義,弄清他的名稱和涵義的由來,有利於闡述部落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的歷史。
早在唐朝時期我國的史籍上就有漠西蒙古族的記載,元朝又有了“西蒙古的記載,史稱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明朝又稱“瓦剌”,清朝稱“厄魯特”、“額魯特”、“衛拉特”,外文書籍又稱為“卡爾梅克”、“克爾梅克”、“哥爾梅克”。
“斡亦剌惕”(Oira或oirai)是蒙古語,它最早的含義比較普遍的解釋有兩種:一種含有蒙古語“衛拉”(Oira)即“近親”“鄰親”的意思,有“近親者”、“鄰近者”、“同盟者”的含義(《元朝秘史》卷十);一種含有“林中百姓”“林中人”“林中民”之意(《亞細亞歷史字典》卷二)。後一種說法比較可信,這不僅從語義上來解釋,語源“oi”作“森林”解釋。Ara作“民”解釋,合成語為“林中百姓”“林中人”“林中民”。更主要的是根據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經濟類型來稱謂的。他們曾經過著林中採集漁獵的生活,草原上的牧民稱他們為“槐園亦兒堅”(《元末譯文證補》四)。也就是林中百姓的意思。隨著歷史的變遷,明代西蒙古出現了“大小四衛拉特聯盟”,衛拉特一詞更具有“親近者”“同盟者”“聯盟者”的實際意義和詞源意義,尤其是18、19世紀帕拉斯、施密特等外國史學家認為“聯盟說”更合理。從四衛拉特聯盟角度分析,前一種說法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俄國的布里亞特蒙古學者多爾濟班扎羅夫則認為衛拉特是由“衛”(Oi)——“林木森林”——加“阿拉特”(ara)——“百姓”組成的,即“林中百姓”。人們普遍認為,多爾濟班扎羅夫的解釋更接近事實,理由較充分,頗具權威性。

土爾扈特部落是我國衛拉特蒙古中其中的一個部落。
歷史的記載中,土爾扈特部落的先祖是王罕,亦稱翁罕。據波斯歷史學家拉施特《史集》記載,王罕所率領的是克列特部((《史集》第297頁。第一卷,第一分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克列特”一詞,蒙古語古老的形式是erle(客列亦惕)現在發音為ere。土爾扈特一詞與克列特有著密切的聯繫,“克列特”有“包圍”、“警衛”的意思,因為王罕家族中的克列特人確曾充任過成吉思汗的護衛。而土爾扈特方言中“護衛軍”亦稱土爾扈特(ougu),因此,克列特便稱為土爾扈特。從古老的族源學考證,“克列特”原是土爾扈特部落的一個姓氏,王罕的姓就為“克列特”,以後發展成為一個氏族。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設立的烏納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南路盟,其中最大的一個旗就是“克列特”旗,也就是汗旗,各代汗王均屬此旗。其分布地域最廣,人數最多,文化素質最高,權力最大,歷史最悠久。在西蒙古專門使用的一種蒙古文字托忒文中,“土爾扈特”一詞的詞根中還有“強大、強盛”的意思,在蒙古族普遍使用的胡都木文中,客列亦惕一詞的詞根中也有“強大”、“強盛”之意。土爾扈特一詞從客列亦惕一詞演變而來,土爾扈特無論從哪一種蒙古文字中,都能找到“強大”、“強盛”之意的詞根。還有的史學家認為,土爾扈特人善於騎馬作戰,繳獲俘虜較多,並融合於自己的部落,逐步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部落,部落實屬強大,因而有了“強大、強盛”的名稱((巴德利著《俄國、蒙古、中國》上卷,第一冊,第97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漢文原來翻譯“土爾扈特”一詞還有“剩人”、“餘人”或“剩下的部落”、“餘下的部落”的意思,意為剩餘在俄國的最後一批人、一個部落。對“土爾扈特”一詞還有一些其他的解釋,但第一種說法學術界認為,有一定的理由,更接近事實。
外文書籍中稱“土爾扈特部落”或總稱1628年西遷至俄國土爾扈特部落為首的衛拉特各部為“卡爾梅克”、“克爾梅克”、“哥爾梅克”、“禹爾梅克”,這些都是漢語的音譯。“卡爾梅克”這一名稱,是巴什基爾人看到伏爾加河沿岸來了一群遊牧民,驚呼為卡爾梅克,按巴什基爾語(alm.almn),其意為“遷移者”、“遷涉者”、“流浪者”、“西遷者”。這一詞意,均被漢、俄、蒙文史學者直譯。據帕拉斯的說法,是“留下”“留下來的人”之意,是根據民族詞源學(動詞)卡爾馬克(ma)即留下之意,它似乎表示那些留下的信仰佛教的土爾扈特人,以區別於那些皈依東正教的土爾扈特人((東方文獻編輯部主編《巴托爾德文集》第五卷,第538頁,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8年版。))。還有一層意思是:1628年後和鄂爾勒克領導土爾扈特部落西遷至伏爾加河沿岸定居,一些人思鄉心重,暫時回了準噶爾盆地。“留下”、“留下的人”就是指當時定居的土爾扈特部落,而沒有回準噶爾的部落人。據伯希和《卡爾梅克歷史評註》第一節《給卡爾梅克人起的各種名稱》一文中費舍爾的看法,卡爾梅克是“高帽子”的意思;文森認為,之所以如此稱呼卡爾梅克人,是因為他的頭上的帽子高高隆起,有高帽子的意思。

對於“卡爾梅克”一詞的使用範圍,科特維奇在他寫的《有關17—18世紀對土爾扈特人關係的俄國檔案資料》中提出:在俄國和外國的檔案材料中,常使用三個術語來表示俄國的衛拉特人:“土爾扈特”出自蒙文史料;“卡爾梅克”出自俄文史料;“客列亦惕衛拉特”出自中國漢文史料。據布萊特耐德爾的說法:“卡爾梅克”一詞,在1398年已為人知曉,“留下”、“留下的人”的詞意,似乎是表示那些異教徒衛拉特人,以區別於皈依伊斯蘭教的東乾人。而“卡爾梅克”這個詞以後表示那批住在伏爾加河、頓河、烏拉爾河一帶的衛拉特人,已習慣於“卡爾梅克”這個名稱,而遺忘了古名——衛拉特、客列亦惕、土爾扈特(伊·亞·茲特拉金著《準噶爾汗國史》第5頁,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4年版。)
土爾扈特一詞的語源、含義,蒙古史的學者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都在努力發掘充足的歷史涵義和語言依據,因此,“土爾扈特”一詞的確切含義有待於深入研究。
早期的歷史
大約在公元7世紀,祖國北方的森林中,克列特部的祖先,就有生產和生活的蹤跡。她的人種、語言、民族和哲學文化都屬東胡和蒙古系統,與我國許多古老的民族鮮卑、契丹相近。
公元9至10世紀,克列特部生活和生產活動詳盡的記載,保留在《蒙古秘史》中。當克列特部走出森林,和蒙兀室韋部——蒙古部落一起進入了水草豐盛的克魯連、土拉、斡難河流域。
克列特部有一個傳說。BFP1克列特部有一個君主,他有7個兒子,膚色全部是黑紅的,因此他們被稱為克列特部,後來這7個兒子的後代逐漸獲得了專門的名號,最後克列特部就用來稱呼其中的一個君主的那個部落,其餘的兄弟都做了那個兄弟的僕從,他們都不是君主。這個傳說符合人類發展的規律,由無階級的氏族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的一般歷史軌跡。

克列特部逐漸成為肯特山和杭愛山中間的草原上一個人數眾多、畜群成片的畜牧部落
(內蒙古蒙語文史研究所編《蒙古族簡史》第3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史集》列舉了克列特部屬下的只爾斤、董合亦惕、撒合亦惕、土別亦惕、阿勒巴惕等6個部落。1092年克列特部首領馬兒忽思(王罕的祖父)反抗遼朝對部落的壓迫,擊殺了遼朝的西北路招討使耶律達卜也於鎮州之地。1110年馬兒忽思的起義被遼朝契丹人所鎮壓,馬兒忽思被塔塔爾首領納兀兒—不亦魯黑汗所俘虜,送到契丹首領處,契丹首領將馬兒忽思釘在木驢上殺害了。
克列特部和草原上其它部落一樣,都被遼朝統治,遼王朝是一個以契丹族為主,聯合一部分漢族地主和其它各族上層分子組成的政權,在草原畜牧部落中曾經設政權機構進行管理,並且派遣官吏對部落人民進行統領。但遭到了草原部落人民的反抗,到1115年,遼王朝就滅亡了。
◦馬兒忽思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忽兒札忽思—不亦魯黑(王罕的父親),一個叫古兒汗。忽兒札忽思—不亦魯黑有6個兒子:
◦脫斡鄰勒,就是王罕額兒客—合剌
◦台—貼木兒太師木花—貼木兒
◦亦勒合—桑昆客列亦台
忽兒札忽思—不亦魯黑死後,古兒汗與王罕之間,王罕兄弟之間為爭奪克列特部的統治權發生了內訌和戰爭。王罕作為長子,按氏族社會秩序應有當然的繼承權。而且王罕7歲時被米兒乞人捉去舂米,13歲又被塔塔兒人抓去放牧駱駝(《元朝秘史》卷二、卷七),幾經輾轉,靠機智和勇敢才回到部落。他因為受過生活的磨難,對部落的下層人民艱難的生活比較同情,並且經常接近和了解下層人民,深受下層人民的擁護和愛戴。還得到了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改巴阿禿兒的幫助。王罕從而戰勝了他的叔叔和弟弟,取得了克列特部的統治權,因而他和成吉思汗的父親結義為兄弟。以後成吉思汗的妻子被三姓蔑兒乞奴隸主搶去,成吉思汗聯合王罕和札答蘭部落的首領札木合薛禪消滅了三姓蔑兒乞奴隸主。口口聲聲稱王罕為罕父,建立異常親密的安答父子關係,並且將三姓蔑兒乞部眾掠奪為奴隸送給王罕。

乃蠻部不亦魯黑汗派軍隊洗劫了王罕部和他弟弟亦勒合—桑昆部,王罕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派孛斡兒諾顏、才華麗國王和赤老罕巴阿禿兒,援助王罕和王罕兩個弟弟,並取得了勝利。
1201年奴隸主們看出了成吉思汗野心勃勃,推舉札木合(古兒汗)為天下之主,聯合合答斤部、撒勒只兀部、豁羅剌恩部、朵兒邊、塔塔兒部、翁吉剌部、蔑兒乞部、斡亦剌惕部、泰赤烏部,在阿勒灰地方聚會,組織征伐成吉思汗及王罕(《蒙古秘史》141—144節)。成吉思汗和王罕聯合迎戰於闊于田的地方,蒙兀室韋部和克列特部兩個部落緊密配合,奮勇反擊,打敗了奴隸主們的聯合進攻。王罕沿額爾古納河追趕札木合等,成吉思汗沿著斡難河追趕泰赤烏部。把有的奴隸主部落給擊潰了,有的給殺掉了,並俘虜這些部落的屬民充實自己的部落,兩個部落更加強大起來。
早期的居住地
大約在公元7世紀,在唐朝望建河的地方,即現今我國版圖內的額爾古納河南岸的森林中,土爾扈特蒙古的先民,便留下了活動的蹤跡。他們當時和《舊唐書》稱之為“蒙兀室韋”蒙古族部落,過著相同或相似的生活。
大漠南北廣闊的草原,一些遊牧部落民族的統治者,為了拓展領土,發展畜牧業,他們征伐森林部落。而森林中的民族部落,他們也不斷和草原畜牧部落交易,並認識到畜牧業較他們先進的生產力。他們開始向草原部落拓展,森林民族走向了草原。
根據《蒙古秘史》記載,公元7世紀,蒙古族的先祖帶領各部落離開額爾古納河向西遷移,渡騰汲思海(即呼倫湖。騰汲思,蒙古語,湖泊的通稱),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兒罕山(大肯特山)駐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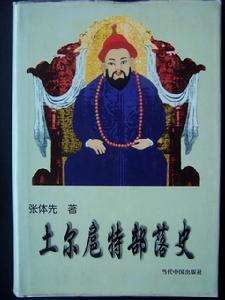
這個大漠南北草原的歷史舞台上,遠在石器時代,這裡就有人類生存。公元前3世紀末,匈奴統一了草原,第一次把這塊牧地上不同種族,不同部落,不同生產方式,不同的發展水平的各部,置於一個奴隸制政權之下,成為統一的匈奴族。公元1世紀末,匈奴分裂,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入塞,鮮卑貴族入主草原,柔然族又興起主政。公元6世紀,突厥奴隸主又控制大漠南北。主要的統治者先後更迭不已,原來的統治者領著一些臣民先走了,相當一部分臣民留在故地接受新來的奴隸主統治。在這塊草地上,匈奴、柔然、鮮卑、突厥、蒙古在不斷地接近、交往、融合。
唐王朝統一全中國以後,北方各少數民族部落,受唐中央政權管轄。唐朝在今北京市的蒙古各部落中設燕然都護府、瀚海都護府。在遼代,即公元10世紀,土爾扈特部落最早的史稱“克列特部落”出現於文獻記載中。據《蒙古秘史》載:“克列特部的居住地在杭愛山和肯特山之間,是人口眾多的部落(內蒙古蒙語文史研究所編《蒙古族簡史》第3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遼王朝曾在克列特部設定官吏統治部落,蒙古族其它部落也都在史籍中有所記載,她們和土爾扈特部落一起,在今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的上游廣闊的草原上駐牧。在土爾扈特部西邊靠近阿爾泰山的地方,是文化較為發達的乃蠻部,往西北的在葉尼塞河下游的是斡亦剌惕部。
12世紀,女真貴族取代了契丹貴族對克列特、蒙兀室韋等部落的統治,建金朝,克列特部屬東北招討使管轄,還在部落設立猛安謀克制統治部落。這時蒙古各部落進入克魯連、土拉、斡難河流域之後,畜牧業迅速獲得發展。據《史集》載:當時蒙古各部馬匹牲畜不計其數,每當這些牲畜站立起來的時候,從山腳大河邊到山頂,大片的草地全被腳蹄覆蓋。經濟的發展,使蒙兀室韋、克列特等部落強大起來,有了和金朝女真奴隸主抗衡的能力。12世紀初,金朝8萬女真攻蒙古,歷盡8年不能取勝,只好納貢求和。封建社會由奴隸社會轉換的歷史中,往往容不下兩個強大勢力並存的局面。1203年成吉思汗領導的蒙兀室韋部落打敗了王罕領導的克列特部落,王罕被殺,其部向西遷移到離乃蠻部和斡亦剌惕部不遠的察乞兒馬兀惕的地方。
1204年克列特部的一個那顏,聯合乃蠻部的塔陽汗、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別乞等十多個部落,準備聯合進攻成吉思汗部。被成吉思汗知道訊息,由1204年4月16日用主動出兵、遠道迂迴突然襲擊、先發制人的戰略戰術,“打敗了諸部進攻,使諸部投降了成吉思汗(內蒙古蒙語文史研究所編《蒙古族簡史》,第17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克列特部又向西遷至失黑失惕的地方。
1207年成吉思汗派長子朮赤率領右翼軍,由投降了成吉思汗的忽都合別乞帶路,向斡亦剌惕餘部前進,到達失黑失惕的地方,忽都合別乞又重新招降了斡亦剌惕部等十餘個部落。以後,斡亦剌惕又向西北遷移,這些是原斡亦剌惕部的禹兒惕部的駐地——八河之地,原斡亦剌惕部餘部、克列特部餘部也來到了這裡。在古代,禿馬惕部就住在這兒,八河從這個地方流出,匯成一條叫謙河的河。

克列特餘部和斡亦剌惕餘部為什麼要向西遷移到這個地方呢?原因是成吉思汗部與禿馬惕部的一次戰爭。成吉思汗曾允許巴阿鄰的豁兒赤那顏娶30個妻子,巴阿鄰的豁兒赤那顏聽說禿馬惕部落的女子長得美,便去禿馬惕部挑選美女,激起了禿馬惕人民的反抗,被禿馬惕人抓住。成吉思汗知道後,因忽都合別乞熟悉林中情況,便派他去鎮壓,忽都合別乞也被抓住。1217年成吉思汗派四傑之一的右翼第二千戶孛羅忽勒去征討,這時禿馬惕部的首領歹都禿勒已死,其妻孛脫渾塔兒渾領導部眾進行反抗,殺了孛羅忽勒。成吉思汗大怒,準備親征,被人勸阻,命令朵兒伯朵黑申再去征討,其採取抄小徑放大批軍隊,而正面放小股部隊迷惑禿馬惕部的戰略戰術,等正面禿馬惕部大部隊一出去迎擊正面部隊。小路的朵兒伯朵黑申在後邊突然襲擊占領了部落,禿馬惕部猝不及防,朵兒伯朵黑申出奇制勝。禿馬惕大敗。
乃蠻部不亦魯黑汗派軍隊洗劫了王罕部和他弟弟亦勒合—桑昆部,王罕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派孛斡兒諾顏、才華麗國王和赤老罕巴阿禿兒,援助王罕和王罕兩個弟弟,並取得了勝利。
1201年奴隸主們看出了成吉思汗野心勃勃,推舉札木合(古兒汗)為天下之主,聯合合答斤部、撒勒只兀部、豁羅剌恩部、朵兒邊、塔塔兒部、翁吉剌部、蔑兒乞部、斡亦剌惕部、泰赤烏部,在阿勒灰地方聚會,組織征伐成吉思汗及王罕(《蒙古秘史》141—144節)。成吉思汗和王罕聯合迎戰於闊于田的地方,蒙兀室韋部和克列特部兩個部落緊密配合,奮勇反擊,打敗了奴隸主們的聯合進攻。王罕沿額爾古納河追趕札木合等,成吉思汗沿著斡難河追趕泰赤烏部。把有的奴隸主部落給擊潰了,有的給殺掉了,並俘虜這些部落的屬民充實自己的部落,兩個部落更加強大起來。
1203年,成吉思汗領導的蒙兀室韋部落日益強大,尋求藉口消滅克列特部落。一是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向王罕的女兒求婚,王罕未準,王罕的孫子向成吉思汗的女兒求婚,王罕沒答應。二是札木合聽說成吉思汗當了蒙古部的首領,就組織兵力3萬攻打成吉思汗,王罕沒有及時出兵援助成吉思汗。三是成吉思汗聽到兩個奴隸巴歹和乞失黑的告密,說王罕準備聯合札木合、阿勒坦汗、忽豁兒赤汗部要進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乘機去進攻王罕,經過兩次激戰,打敗了王罕,將克列特部的一些部眾向西派遣給了自己的屬下。另一些部眾做了成吉思汗的護衛軍。
蒙兀室韋原來也是草原上的一個部落,以後又叫蒙古部落,其統一草原後,蒙古這一名稱就成為草原各部落的通稱(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三冊,第91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克列特部被蒙兀室韋部戰敗後,成了蒙室韋部的一部分 。
早期的社會生活
土爾扈特部落的先民生活在我國額爾古納河南岸的森林中的時候,森林、草原、高山和河岸棲息著眾多的野獸猛禽,其中有虎、狼、豹、野豬、隼、鷹、鷂等。野獸雖然是“林中人”獲取食物的一種重要來源;但森林部落的人民隨時都會受到這些野獸猛禽的侵襲和騷擾,甚至被當作食物吞噬。所以部落的人們必須結合成群,否則就無法生活,這種自動結合的原始群落,是部落最早的社會結構組織。

公元7世紀,蒙兀室韋和土爾扈特部落的祖先領著部落的人們來到草原後,因各部落戰亂較多,他們隨時都可能被其它的部落打垮而被奴役,去做奴隸。為了保護部落不受侵害,部落人推選酋長,一是作為軍事統帥,二是擔任主祭(祭天地兩種),三是定期召開部落小酋長的會議,或不定期召開緊急會議,四是由此選出部落的總的酋長。一切都聽命於部落酋長會議。這就是氏族部落軍事民主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徵。
公元10世紀,史書對部落酋長世襲制度,“在克列特部有了較詳盡的記載”。
馬兒忽思(王罕的祖父)傳位給忽兒札忽思—不亦魯黑((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第214—216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王罕父親),之後又傳位給脫斡鄰勒(王罕)。酋長之位原來傳給賢才改為傳給子孫,古老的民族部落制度被奴隸制所取代。酋長之位世襲制的確立,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變革。它是家庭、私有制、階級和階級剝削已經存在的標誌,從此以天下為公的原始社會走向天下為家的階級社會。
王罕即位酋長時,正是遼王朝統治土爾扈特部落時期。遼朝在部落內設州、縣,置衛、司政權管理機構,並且派遣刺史、縣令、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對部落人民進行統治。
13世紀初,女真貴族取代契丹,建立了金王朝,土爾扈特部落屬東北招討使統轄,一些部落的貴族在部落內擔任詳穩、令穩之類的官職,並在部落內推行統治基層牧民組織猛安謀克制“即一百戶或三百戶組成一個謀克,設百夫長一人,每十個謀克組成一個猛安,設千夫長一人。猛安謀克都是部落的壯丁,平時從事放牧,戰時應徵作戰。這個基層組織既是軍事組織,又是基層政權的編制((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三冊,第71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這是所有朝代在部落中設立的最早的基層政權組織,1234年金朝滅亡後,這種制度在很長時期內還在部落中實行。
由於遊牧部落畜牧業經濟分散性和脆弱性的特點,以及歷史形成的特殊環境,土爾扈特部落形成的部落奴隸制中的奴隸,其來源有4個方面:1戰俘奴隸,即戰爭勝利後獲得的奴隸;2買賣奴隸,即奴隸主在市場或在其它奴隸主手中買來的奴隸;3贈賜奴隸,即奴隸主為了友誼和利益互相贈送的奴隸;4世襲奴隸,奴隸未獲自由前,其子女繼續為奴,這是奴隸代代不息的來源。
土爾扈特部落的奴隸制,是由下述奴隸主和奴隸以及自由民的階級關係構成的。
奴隸主分為4種:
①“汗”(王),②“額氈”(主人),③“那顏”(官吏),④“別乞”(長老親王)。
自由民分為3種:

①“薛禪”(賢者、謀士、知識分子),②“巴特爾”(勇士),③“都里因古溫”(平民)。平時獨立生產為己,戰時騎馬禦敵為部落。
奴隸分為4種:
①“合蘭”(室內奴隸,即奴婢),②“札剌兀”(世襲奴隸,做長年工役),③“引者”(陪嫁奴隸,即贈賜奴隸),④“兀貼古孛斡勒”(戰時俘虜為奴,這種奴隸處於社會最低層,往往平時給主人放牧,戰時為部落作戰(內蒙古蒙語文史研究所編《蒙古族簡史》第6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牧業經濟的條件下,奴隸主不可能將大批奴隸集中起來管理,只能是讓奴隸一家一戶跟著畜群走。在這種情況下,氏族的血緣關係對奴隸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氏族的血緣紐帶在土爾扈特部落中保留了很長時間,而且極其牢固,不論是奴隸主、自由民、奴隸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出身的家庭,每個人從記事起,要向祖父遺留的小刀磕頭,吻小刀的刀背,舔小刀的刀刃並向小刀宣誓:牢記先祖的業績,背誦氏族的系譜,弄通親族之間的血緣關係。氏族中的長支受人尊敬,老人也受到尊重,同部落的人有互相援助的義務。這些掩蓋著奴隸主統治的實質,維護著奴隸主階級的利益,有力地起著把奴隸束縛在奴隸主統治下的作用。奴隸主把自由民做為本部落的人來統領。有了氏族組織,奴隸主還可以把被打敗的氏族部落的頭目當做奴隸主的代理人來使用。像土爾扈特部落和斡亦剌惕部落被成吉思汗打敗了,部落的牧民都成了成吉思汗的奴隸,但部落奴隸主忽都合別乞、王罕的子孫,仍然承襲部落,替成吉思汗管理奴隸,並使土爾扈特部落承襲制度綿延不息。因奴隸主們竭力要保持這種世襲制,如一位部落的奴隸主被擒後,給成吉思汗帶口信:“烏鴉擒鴨子,奴隸擒主子,我們可汗安答(大王父親)請不要這樣做;小鳥抓野鴨,奴隸害主子,我們可汗安答請不要這樣做((內蒙古蒙語文史研究所編《蒙古族簡史》第10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奴隸主看來,奴隸主神聖的世襲制是不可侵犯的,奴隸主只能世世代代世襲,仿佛這是永遠不能改變的天條。
部落奴隸主憑藉自己手中無上的權力,對外掠奪,對內鎮壓,如果奴隸敢於反抗奴隸主,就把他們的“腳筋挑了,心肝割了,性命斷了”。
但是,廣大的奴隸和自由民,強烈反對奴隸主的壓迫和奴役,反抗對內鎮壓,對外掠奪的政策。奴隸們大批逃亡,或殺死奴隸主,自由民衝破氏族血緣紐帶離開同族奴隸主。
一些有新思想的奴隸主主張用新的方式來統治部落,他們往往是以保護奴隸和自由民的形象出現,收留保護這些逃亡和反抗的奴隸,這部分人和部落首領間的關係就成了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關係。部落的首領得到了屬民,擴大了部落,而被保護者,也不再是奴隸,而是部落中的“合剌除”(屬民),室內奴隸也成了那可(伴當、朋友)。部落奴隸主統治分崩離析,由此,部落為走向封建社會準備了條件。
早期的經濟生活
關於土爾扈特部落早期的物質生活,歷史文獻中沒有什麼直接的記載,只能通過史詩、傳說、神話,間接地了解土爾扈特部落人早期經濟生活的情況。人們從流行於我國西北邊疆土爾扈特部落民族史詩《江格爾》中,可以看到土爾扈特部落“林中百姓”的早期生活和部落人為了生存,勤勞勇敢地蒐集食物的情形。
從其它蒙古族部落林中生活的傳說中,也可以看到部落早期林中生活的情形。一個獵人在森林中狩獵時,發現了一個嬰兒躺在樹下,那棵樹的形狀像一個弓形的管子,從中流出樹汁哺養嬰兒,旁邊有號鳥守護,於是傳說弓形樹就是嬰兒的母親,號鳥就是他的父親,他們認為這孩子是天的外甥。喝樹汁,樹為母,號鳥為父,這則傳說可以看出林中人從母系社會走向父系氏族社會的生活蹤跡。

《蒙古秘史》中說:“林中百姓的狩獵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符拉基米爾佐夫說:“森林居民主要從事狩獵,但也沒有放棄漁撈,他們住在用樺樹皮和其它木料搭成的簡便棚子裡……‘森林居民’馴養野生動物,特別是西伯利亞鹿和小鹿,吃他們的肉和乳,雖然他們在森林遊動時用西伯利亞的鹿來馱載日用器具,但他們也知道使用馬,馬似乎曾被森林居民用於狩獵,而酋長、富裕者和貴族更可能是使用馬的……森林的蒙古族部落縫獸皮做衣服,使用滑雪板,喝樹汁(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俊譯《蒙古社會制度史》第54—5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這位史學家描述的林中人,他們已經學會了馴養動物,使用馬匹,搭建棚屋。已經在和林外民族的接觸中,逐漸地踏上了歷史文明的腳步。但也看到了他們生活物資極其匱乏,穿獸皮衣服,喝樹汁。
一些原始部族的文明進步的歷史,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向前發展,他們永遠不會在原地踏步。土爾扈特部落史前的原始祖先,隨著和其它民族的交往、貿易、融合、碰撞中,已經有了工具、武器、服裝、建築、畜牧、語言、符號、藝術、原始的宗教和森林的文化。土爾扈特部落有著不應小看的歷史文明和社會進步。
由於草原人經濟發展,畜群增多,而勞動力嚴重不足,不得不向森林民族掠奪生產力。隨著草原人不斷進攻林中人,一部分林中人做了俘虜,不得不隨著走向了草原。另一部分森林居民,通過對外界的接觸、交往中,得到了林外生活的文明和進步,再也不願意過著那種食不果腹、獵不充飢的生活,也走向草原。當然大部分林中人不願放棄原來的森林生活,父母親往往對不聽話的女兒說,你如果不聽話,就把你嫁給那些放牧牛羊的草原人。姑娘們聽說要離開定居的小木棚,要丟棄取之不盡的木柴森林,要孤零零地一家人到遙遠的草原上放牧,要撿拾動物的糞便來取暖做飯,要住永不固定的蒙古包。聽後一想就大哭起來。整個部落經過極其複雜的思想鬥爭的歷程才走向了草原。
進入了草原,土爾扈特人由採集漁獵生活改變為草原的畜牧生活,是土爾扈特部落的一大進步,從此整個部落由氏族社會走向了奴隸制社會,捲入了草原上階級歷史的大漩渦。
10世紀的歷史文獻中,土爾扈特人祖先的畜牧經濟發展迅速,擁有的馬匹和牲畜不計其數(中華書局標點本《新唐書》217卷,下冊,6140頁),他們已經學會了選育牲畜的良種,來促進生產的進步。他們的食物主要以牛、羊肉為主,喝的是牛、羊、馬乳汁,住的是三角形狀毯做的、以木桿為支架,以毯氈圍起的大約十多平方米左右古蒙古包。已經有了製造皮革、氈毯、弓弦、箭鏃之類手工業的基礎,又出現了鍛冶業和木作業,專業的手工匠已從牧民中分工出來,擔任製造幌車、帳幕、家俱、槍矛、刀劍和胄甲等器具。家庭手工業也出現了分工,男人們則以製造鬃繩、馬鞍、挽具、弓箭、帳幕、木器、馬車為主,婦女們則以擀氈、揉皮、縫衣、製鞋為主。“冶鐵術已經有了歷史,部落有著傑出的鐵匠、木匠和皮匠(內蒙古蒙語文史研究所編《蒙古族簡史》第3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已有文獻記載和內地商人進行互市貿易的情形。草原牧人用毛皮、牲畜換取平原內地商人的錦帛、鐵器和麵粉。後來還和祖國西北地區的畏兀兒族(今新疆維吾爾族)、西夏党項族(藏族的一支)貿易往來,用畜產品換取維吾爾、党項族商人的乾果、金屬品和糧食。由於經濟的發展,土爾扈特部落發展成為蒙古草原上一個強大的部落。
生產力大大提高,各部落經濟的發展,生活的互相滲透甚至融合,而舊有奴隸制的生產關係,已經變成了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桎梏,腐朽的奴隸主階級更加反動,他們互相攻擊,殺伐不止,使草原陷入了天下大亂、互相攻劫、民不聊生的狀態,這給社會的經濟生產和部落人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