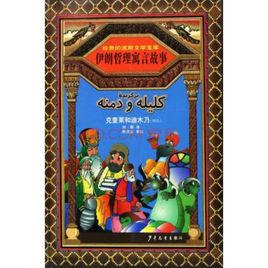創作時期
中古時期
 波斯語
波斯語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在伊朗通用的語言是古波斯語(楔形文學)。公元前330年亞歷山大征服伊朗,阿契美尼法王朝覆滅,古波斯語也隨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中古波斯語,即帕列維語。伊朗歷史上的兩個著名王朝,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和薩珊王朝(224-651)時期通行的語言就是帕列維語。薩珊帕列維語的文化古籍一直保留至今。薩珊王朝的伊朗是高度發展的奴隸制大帝國,伊朗的農業和手工業都很發達,在對外關係上和中國、印度、羅馬等古國廣泛開展了海陸貿易,牢牢地控制著中印通往西方的海陸商道。與此相適應,科學文化也有高度的發展,宮殿建築遺蹟和浮雕石刻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都表明古代波斯人民已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
七世紀六十年代初阿拉伯人占領伊朗,薩珊王朝覆滅。這次入侵改變了伊朗的歷史和文化發展的進程,伊朗人民由信奉襖教轉而信奉伊斯蘭教,獨立的伊朗喪失了原來的政治地位。被異族統治的伊朗人民要求民族獨立,於是,產生了“舒畢主義”思潮。舒畢主義者主張非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宣傳伊朗文明高於阿拉伯文明。“舒畢主義”是伊朗文學興起和發展的政治因素。
由於伊朗人民不斷舉行起義和伊朗上層統治集團日益擴大其政治勢力,九世紀末,阿拉伯人的統治實際上已名存實亡,在伊朗建立了許多地方政權。十世紀初,一種在伊朗東方流行的方言法爾斯語(即達麗語)開始廣泛傳播,並逐漸取代帕列維語而成為伊朗的通用語言,這就是流傳至今的波斯語。當時,伊朗是定都於巴格達的哈里發國家的一個行省,因此阿拉伯語在伊朗也曾經是官方語言,但是阿拉伯語僅限於在官方文書、宗教及科學領域使用。雖然有些波斯詩人也曾用阿拉伯語寫作,但阿拉伯語從未成為伊朗的通用語。伊朗古代詩人正是用波斯語創造了光輝的波斯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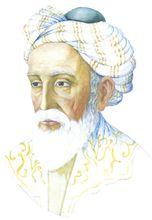 海亞姆
海亞姆據記載波斯語詩歌早在亞古伯·列斯國王時期(卒於878年)就已出現。伊朗文學史上第一位著名詩人是魯達吉(卒於940年)。魯達吉生於撒馬爾罕。他曾作過薩曼國家的宮廷詩人,後被逐出宮廷,晚年窮困潦倒,以行乞度日。魯達吉熟悉民間創作,他善於從民間創作中汲取營養,創作出多種體裁的波斯詩歌(如頌詩,四行詩,抒情詩等)。他曾把從印度傳入的故事集《卡里來和笛木乃》改寫成故事詩。魯達吉的詩是波斯詩歌從民間創作過渡到文人創作的標誌,他的作品為以後伊朗詩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後人稱他是伊朗的“詩歌之父”。
從十世紀到十五世紀是伊朗文學史上詩人輩出、優秀作品不斷湧現的黃金時代。
約在魯達吉逝世的時候,在伊朗古代文學發祥地霍拉桑的圖斯誕生了伊朗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長篇英雄史詩《王書》的作者菲爾多西。《王書》不僅是伊朗古典文學的高峰,而且也是世界文學中的珍寶。
在菲爾多西逝世後的三十年,在霍拉桑的尼沙浦爾誕生了另一位世界聞名的波斯詩人,這就是哲理詩人歐瑪爾·海亞姆。
歐瑪爾·海亞姆(約1048-1122年)是一位科學家和哲學家。他精通數學和曆法,也研究過天文學和醫學。在數學上他有很深的造詣,曾寫過代數學論文,並曾奉國王之命修訂曆法,籌建天文台。他在生前已經是知名的學者,但是,在他去世後的五十年內人們並不知道他是一位詩人。1173年才有人在一本歷史著作中提到他的詩。
海亞姆在世時,統治伊朗的是突厥人建立的塞爾柱王朝。塞爾柱王朝是一個軍事封建制的政權,這個政權在發展科學文化方面遠比素稱開明的薩曼王朝遜色,瀰漫在科學和文化領域裡的宗教勢力使文人和學者感到壓抑和窒息。對這些,詩人海亞姆是有切身體會的,他曾在一篇文章里這樣記述道:“我們目睹許多學者離開了人世,現在學者已經剩下寥寥可數的一小部分人了。他們人數雖少,但卻苦難深重,正是這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在這艱難的日子裡,為了科學的進步與發展而奮力獻身。但是大多數學者卻弄虛作假,擺脫不掉詭詐和做作的風氣,他們利用自己取得的知識去追求庸俗和卑鄙的目的。要是有人去尋求真理,播揚正義,鄙棄庸俗利益和虛偽的騙局,他就立即會遭到嘲笑和非議……”。這就是海亞姆的生活環境,這是一個政治上受到異族統治,思想上受到宗教毒害,科學文化上受到摧殘的時期。海亞姆的四行詩就是這個波斯人民苦難深重時代的痛苦的回聲。
海亞姆是一位中世紀的勇敢的叛逆詩人。他的詩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迷信的色彩,統治階級稱他的詩是“吞噬教義的彩色斑斕的毒蛇”。從他的詩里我們看到的是嚴肅的思索,執著的自信和深沉的痛苦。人們一接觸到他的詩就立刻被那深刻的思想和優美的形式所吸引。他的語言是質樸平實的,他的心是火熱的。
海亞姆雖然是當時社會中的傑出人物,但是他的思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時代的局限。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學者,他自然感到無力與孤獨,他的詩里充滿哲理的思索,但是缺乏理想與希望,有時甚至流露出悲觀厭世的思想,他甚至也宣揚過冥冥中存在著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絕對的命運。這樣,海亞姆就陷入唯心主義泥沼,否認神的存在的海亞姆又為我們製造了一尊新神。
以魯達吉和菲爾多西為代表的霍拉桑的詩人們在創作風格上有共同的特色。這就是語言樸實平易,不尚雕琢,敘事簡練,明白曉暢,儘量避免使用阿拉伯語和科學名詞,文學史上稱這種風格為“霍拉桑體”。
從十一世紀初開始,伊朗的詩歌創作中心自東向西轉移。十一世紀以後霍拉桑地區的詩文化創作相應地衰落,代之而起的首先是阿賽拜疆,繼之是伊斯法罕和法爾斯。阿賽拜疆詩歌創作的繁榮是與塞爾柱王朝及西南地方政權的統治者的扶植和提倡分不開的。隨著詩歌中心向西轉移,詩歌的風格和形式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一時期詩歌的用語帶有濃厚的西南地方色彩,敘事更多使用比擬手法,描寫更加委婉細膩。阿拉伯語辭彙和科學術語更多入詩。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表達手段較前一時期豐富,但也開始向艱深晦澀的方向發展。在伊朗文學史上把這個時期的創作風格稱為“伊拉克體”。
這一時期,西南地區產生的許多詩人的傑出代表是內扎米·甘賈維(1141-1203)。內扎米是繼菲爾多西之後最優秀的敘事詩人。如果說菲爾多西的英雄史詩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那么,內扎米的創作則明顯地走向了現實,雖然他不可能完全擺脫神話的影響,但是他更多地描寫了人間的愛恨,塵世的悲歡。他的筆下已經出現了封建制度壓迫下的不幸的男女,描寫了他們的理想和希望與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的矛盾和衝突,展示了他們的悲慘命運。
內扎米在作品裡還常提到中國。在長詩《霍斯陸與西琳》中,他描寫的石匠法爾哈德的高超技藝就是在中國學的。在《七美人》里,內扎米還提到一個中國城市,他說這個城市象天堂一樣風景如畫。在古代波斯人心目中,中國是一片神奇而美妙的大地。這點,在內扎米的作品裡得到證實。
在這裡還應該提到另一位波斯詩人,這就是哈珠·克爾曼尼(1290-1352)。哈珠生於波斯東部克爾曼省,和著名抒情詩人哈菲茲是同時代人並與哈菲茲有過交往。他創作了許多詩歌,其中敘事詩《胡馬和胡馬雲》寫的是一位伊朗王子和一個中國公主的愛情故事。一次胡馬在夢中遇到了中國公主胡馬雲,從此,他就不願繼承王位,並不顧旅途險阻,一心到中國尋找胡馬雲。他們的愛情經歷了許多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難,最後,胡馬雲隨胡馬去波斯。這個故事完全是詩人哈珠虛構的,但也反映了當時中伊人民的深厚情誼。
十三世紀下半葉,伊朗詩歌創作中心由西向南轉移。十三世紀初,伊斯法罕已經成為文化中心,蒙古人的入侵加速了這種文化中心轉移的過程。蒙古鐵騎從波斯北部及東部入侵,位於東北部的霍拉桑地區遭到徹底破壞。霍拉桑文人紛紛內逃。波斯中南部如伊斯法罕及設刺子就成了他們的避難所。
南遷的文人只是助長了文壇的聲勢,真正代表這一時代的兩位著名詩人薩迪和哈菲茲都誕生在南方城市設刺子。在文學史上與這兩位詩人齊名的蘇菲派詩人莫拉維則生於巴爾赫(今阿富汗境內),他是在蒙人入侵之初躲避到小亞去的。
蘇菲主義從九世紀初傳入伊朗。這種思潮首先在城鄉手工業者中間傳播。手工業者遭受封建統治階級的沉重壓迫,生活非常困苦。他們要求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但卻不能達到目的,失望之中便容易產生消極思想。蘇菲分子否認人世幸福,提倡禁慾主義,要求思想自由,追求抽象真理。他們表面上不否定伊斯蘭教的教義,但有人卻對其教義任意加以解釋。這實際上是對宗教桎梏的一種反抗形式。蘇菲派不僅具有共同的思想觀點,而且有類似幫會的組織形式。他們有自己的傳道場所和自己的領袖,在組織之內對領袖絕對服從。蒙古人入侵後,一些蘇菲分子由於對宗教勢力和封建勢力的譴責進而對蒙古人的野蠻掠奪和屠殺表示反抗。
雖然蘇菲主義一開始就具有反封建的傾向,但在其發展過程中一批上層蘇菲分子為統治者所拉攏,蘇菲主義的神秘觀點也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以致變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詩人莫拉維,和他的父親、他的兒子三代人就是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在果尼葉城設壇講學的蘇菲派領袖人物。
莫拉維(扎拉丁·盧密,1207-1273)的父親是巴爾赫著名神學學者,蘇菲派領袖。他們父子在蒙古人入侵之初從東部躲到小亞細亞,並應地方政權的統治者之命傳道講學。莫拉維早年見過蘇菲派詩人阿塔爾(卒於1229年)。阿塔爾對莫拉維極為稱讚,把自己的詩集贈送給他。在果尼葉時期莫拉維深受蘇菲派領袖沙姆斯爾丁·大不里茲的賞識,此人對莫拉維的思想發展有很大影響。莫拉維後來把自己的抒情詩集題名為《沙姆斯丁·大不里茲集》。
莫拉維和薩迪是同時代人。這兩位大詩人逝世不久,在設刺子誕生了伊朗文學史上另一位世界聞名的詩人,即抒情詩人哈菲茲。
哈菲茲(1300?-1389)自幼聰敏過人,他的筆名哈菲茲的含意就是“能熟背可蘭經的人”。此外,他還有許多綽號如“神舌”、“天意表達者”等。使用波斯語的人們認為哈菲茲的詩有一種神奇的魅力;至今仍有不少人以哈菲茲的詩句占卜凶吉。
哈菲茲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定的年代。他出生的時候,蒙古人的政權旭烈兀王朝已經走下坡路,這時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尖銳。詩人晚年又趕上鐵木耳對波斯的征伐(鐵木耳於1380-1393占領波斯全境)。哈菲茲出生在伊斯法罕,父親是一個商人,後全家移居設刺子。他由於父親去世,幼年生活困苦,年紀很小就去謀生;他把掙得的錢分出一部分拜師求學,所以他受到很好的教育。
波斯的抒情詩有固定的形式,通常由七至十餘個對句組成(有時可達二十餘對句)。一首抒情詩不一定有完整的情節,完全是詩人抒情自己主觀的感受或描寫客觀景物。往往在最後一個對句中出現詩人的名字。哈菲茲的抒情詩是他以前的詩人創作的繼承和發展。伊朗著名的文學家阿里·達什提說哈菲茲有海亞姆的思想,莫拉維的靈魂,薩迪的語言。這主要是指在哈菲茲的詩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海亞姆的反封建、反伊斯蘭教的思想影響,莫拉維的蘇菲主義的神秘色彩和薩迪的質樸流暢的文學語言。哈菲茲是一位不倦地追求自由的詩人。他是伊斯蘭教的反對者,他歌唱現世幸福,讚美人與人之間的真摯感情。他反對宗教人士的偽善做作,否定他們宣揚的渺茫的彼世和虛幻的天堂。他放歌豪飲,寫下了許多頌酒的動人的詩句。他對宗教人士的譴責是激烈而無情的。正是在這些方面,他擺脫了神秘色彩。
哈菲茲生活在一個“鮮血淋淋的”時代,當時波斯與入侵民族的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十四世紀末,鐵木耳對波期的征伐給波斯帶來了又一次大動亂。生活在這樣嚴酷的年代裡的哈菲茲所創作的抒情詩自然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語句也多含蓄隱晦。
以薩迪和哈菲茲為代表的南方詩人對波斯文學語言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他們的語言擺脫了伊拉克體的傳統的艱澀文風而走向平易曉暢。他們的創作特點之一就是廣泛吸取人民民眾的活的語言,經過藝術加工,而表達深刻的思想內容。尤其是哈菲茲的語言樸實含蓄,細膩精練、有很強的表現力,標誌著波斯文學語言已經高度成熟。恩格斯就是通過哈菲茲的詩句而學習波斯語的;他在一封信里說,“讀放蕩不羈的老哈菲茲的音調十分優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註:《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2卷,第104頁。)
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南方詩人的創作風格逐漸發展而形成“印度體”。“印度體”詩人們的創作立意平庸,用語俚俗,比起“霍拉桑體”及“伊拉克體”兩個時期的創作水平相差甚遠。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以伊斯法罕文人為中心興起了一個“復古運動”,要求詩人的創作恢復“伊拉克體”或“霍拉桑體”。在哈菲茲以後,只是在十五世紀出現一個有影響的大詩人賈米(註:賈米(1414-1492)是學者、詩人,蘇菲派領袖人物。著有“七卷詩”(又稱“大熊座七星”),其中四卷是關於神學及哲學問題的,三卷是敘事詩,此外還有抒情詩一卷和一些散文著作。賈米在世時名聲很大,統治者對他十分尊敬,但在文學成就上不如薩迪、內扎米。);此後,一直到近代史的開端(十八世紀末)在伊朗文學史上再沒有產生象薩迪和哈菲茲這樣世界聞名的大詩人了。
伊朗現代著名學者和文學家伏路基在談到波斯文學的成就時,列舉了四位詩人,這就是菲爾多西、薩迪、莫拉維和哈菲茲。他認為這四位詩人是波斯文學的“柱石”。的確,這四位詩人各是伊朗文學史上一個方面的傑出代表人物。除這四位詩人以外,海亞姆和內扎米也都在他們各自的創作領域得了光輝的成就。對東方文學頗有興趣的德國大詩人歌德也曾對波斯文學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他說:“據說波斯人認為他們在五百年間產生的眾多詩人中,只有七位是出眾的。但是,就是他們所不取的其餘詩人中,仍然有許多人是我所不及的”。(註:有的學者列舉的七位波斯詩人是:菲爾多西、海亞姆、昂瓦里、內扎米、薩迪、莫拉維和哈菲茲。參看列查·扎迪·沙法格著《伊朗文學史》,450-451頁。)這段話不僅說明了這位德國大詩人的謙遜,同時也表明了高度發展的中世紀波斯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
近現代時期
19世紀初葉,隨著外國商品和資本的侵入,伊朗逐漸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人為了抵禦外國侵略和緩和人民的不滿,企圖實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力主改良的是密爾扎·阿卜杜勒(卡埃姆·瑪岡姆,1779~1836)和密爾扎·塔吉(1805~1852)。前者不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開一代新風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內容充實,語言明快,擺脫了“印度體”的隱晦文風。
19世紀下半葉,文學上的啟蒙者密爾扎·法塔赫·阿里·阿洪德扎德(阿洪道夫,1812~1878)和密爾扎·瑪利庫姆(1833~1908)二人,認為《薔薇園》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在新時代應該創作適合人民要求的戲劇和小說。
同一時期的著名作家還有密爾扎·阿卡·克爾曼尼(1853~1896)、澤因爾·阿別金·莫拉基(1837~1910)以及塔里波夫(1855~1910)等。阿卡寫過許多反對封建主義的政論文章,還寫過一本模仿《薔薇園》的故事集。塔里波夫的主要著作是《阿赫麥德集》,這是一部批判當時社會弊病的作品。澤因爾·阿別金·莫拉基的《易卜拉欣·貝克遊記》是一部影響較大的作品,作者通過主人公對伊朗和外國的對比,揭露了伊朗社會的種種弊端。這一時期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廣泛傳播,文學創作也比以前更加真實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
1905至1911年伊朗爆發了資產階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史稱“立憲運動”。它的基本目標是實行君主立憲,進行民主改革。隨著革命形勢不斷高漲,文學創作也出現了繁榮景象。著名詩人巴哈爾稱這一時期為革命時期,他認為“標誌著這一時期特點的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學”。
巴哈爾(1886~1951)生於伊朗東部馬什哈德市,早年以詩聞名,曾獲“詩人之王”的稱號。他是霍拉桑省立憲運動中的活躍人物,曾參加地下報紙《霍拉桑》的編輯工作。1909年主持出版伊朗民主黨刊物《新春》(後更名為《早春》)。巴哈爾的詩充滿了愛國主義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戰鬥精神,在形式和語言方面繼承了波斯詩歌的優秀傳統。
這一時期另一位著名詩人是阿卜杜勒·卡賽姆·拉胡蒂(1887~1957),他生於西部城市克爾曼沙赫。在他的早期詩歌中反映了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在他的立憲運動時期的作品中,出現了為人民利益而戰鬥的民主戰士的形象。
立憲運動時期興起一種短小精悍、尖銳潑辣的雜文,代表作家有阿里·阿克巴爾·德胡達(1879~1956)。他在詩文兩方面都有所創新。他的雜文內容充實,形式活潑,具有強烈的戰鬥。 立憲運動時期具有廣泛影響的刊物是《天使號角》和《北風》。德胡達是《天使號角》的主編。這份刊物的發行人是賈杭吉爾。《北風》的主編及撰稿人是賽義德·阿什拉芙爾丁,主要刊載政治諷刺詩。
伊朗文學在立憲運動時期,在反映人民的生活與鬥爭、譴責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等方面,其深度和廣度是空前的,同時,文學語言也更加接近人民大眾的口頭語。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是伊朗現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時期。巴列維王朝的禮薩國王執行高壓政策,取締進步書刊,有影響的詩人和作家或被監禁流放,或逃亡國外。巴哈爾、 阿列夫·卡茲文尼(1882~1934)、 埃什基(1893~1924)以及法羅西·耶茲迪(1889~1939)等是這一時期伊朗現代詩歌戰鬥傳統的優秀代表,他們在黑暗的年代裡頑強地進行創作,堅持鬥爭,遭到各種迫害。
同時期另外一批詩人的作品哀傷多於憤怒。他們筆下雖然不乏人間的不幸和痛苦,但缺少抗爭的勇氣和戰鬥的呼喚。他們的詩講究音律和詞藻,更多地從形式上繼承波斯古典詩歌的傳統。這類詩人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治·密爾扎 (1874~1924)和帕爾溫·埃特薩米(1906~1941) 。尼瑪·尤什吉(1897~1960)是立憲運動以後文學革新派的代表,他主張用人民的語言表現人民的生活,在詩歌形式上提倡自由體詩。
1921年,作家賈瑪爾扎德(1895~ )發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故事集》。在《故事集》問世前後,伊朗出版了不少歷史小說和社會小說,歷史小說多寫帝王或英雄的文治武功,往往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美化歷史人物(如胡斯拉維的《閃姆斯和突格拉》);社會小說多寫社會黑暗面,大多表現婦女的悲慘命運,有自然主義傾向(如莫沙菲格·卡澤米的《恐怖的德黑蘭》,1924)。《故事集》與這兩類小說不同之處在於著重描寫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並自覺地運用人民大眾的日常用語。
30年代初,在德黑蘭出現了一個青年文學家團體,稱為“拉貝”(即“四人會”)。它最初的成員有薩迪克·赫達亞特(1903~1951)、伯佐爾格·阿拉維(1904~ )、馬斯烏德·法爾扎德(1906~ )和密努。薩迪克·赫達亞特是伊朗現代著名作家,他以創作短篇小說為主。早期創作受西方頹廢派的影響,帶有感傷色彩;後期創作(1941年後)明顯走向現實主義。他的兩部中篇小說《盲梟》和《哈吉老爺》獲得了世界聲譽。
伯佐爾格·阿拉維是伊朗共產黨員,1937年被捕入獄,在獄中堅持寫作,著有短篇小說集《獄中札記》及《五十三人》。他的長篇小說《她的眼睛》(1952)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伊朗進步人士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穆罕默德·赫加澤(1900~1970)的主要作品有《胡瑪》、《帕里切哈爾》、《淚》、《帕爾旺尼》、《澤巴》以及文學小品集《鏡子》、《沉思》、《微風》和《旋律》等。他的小說主要描寫上層社會婦女形象,主要思想傾向是宣揚在逆境中要退避忍讓,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的語言優美流暢,是規範化的現代波斯語。作家阿路·阿赫邁德(1920~1971)與赫加澤的風格迥然不同,他對城鄉生活中的落後現象持批判態度,主要作品有《互訪》、《我們遭受的苦難》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伊朗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浪潮高漲,50年代初發展為聲勢浩大的石油國有化運動。1946年,在德黑蘭召開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有著名詩人和作家巴哈爾、尼瑪·尤什吉、薩迪克·赫達亞特、伯佐爾格·阿拉維、薩迪克·秋巴克、赫加澤等。大會從詩歌、散文和文藝批評等方面探討了伊朗現代文學發展問題。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相繼出現了一批優秀的短篇小說,如薩迪克·赫達亞特的《明天》(1946),阿赫瑪德·薩迪克的《同志》(1952),奧密德的《白色地平線》,達里亞的《反叛》(1952),伯佐爾格·阿拉維的《一個吉蘭農民》(1951)、《書簡及其他故事》(1952)和《水》(1952)等。
1953年伊朗大資產階級和大封建主的代表穆罕默德·禮薩國王推翻了民族主義者摩薩台的政府,鎮壓蓬勃開展的人民革命運動,出版事業和文學創作又一次遭到沉重打擊。1953年以後,西方偵探小說和色情作品開始在伊朗泛濫。
60年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現了一批反映現實的長篇小說。這類作品如穆罕默德·阿里·阿富尼的《阿胡夫人的丈夫》(1961)、賈瑪爾·米爾·薩迪基的《長夜漫漫》、薩迪克·秋巴克的《坦格斯坦人》和《頑石》等,特別是《阿胡夫人的丈夫》反映了伊朗婦女的不幸和宗法制的家庭關係,出版後獲得廣泛注意和很高的評價,被認為是伊朗現代文學創作中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
作品賞析
我們來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見淵源,下不見盡頭,
沒有人能說清楚,
我們自何方而來,向何方而走?
看呵!蒼穹就象我們傴僂的軀身,
阿姆河水,那是我們晶瑩的淚珠滾滾,
陰森的地府是我們無謂的憂慮,
天堂,只不過是我們悠然的一瞬。(歐瑪爾 海亞姆)
當我的生命悄然逝去,
悄然逝去,離開我的親人,
給我描眉修鬢要用朋友的一路風塵,
著素戴孝要用朋友的一顆痴心。
灑頭的香水要用他的兩行熱淚,
薰香的香料要的是他滿懷悲辛。
成殮時我的身體要覆蓋著鮮花,
防腐的樟腦,那是他的嘆息深深。
我為理想而死,屍布要染成大紅,
讓它象我的喜期一樣,彩色馥濃,
你要把我打扮得象出嫁的新娘,
入土時,蓋頭要罩在頭上。
那為我而流浪的人聽到訊息,
他會滿腹悲戚地趕來,
趕到這裡奔喪,
當他俯身撲到我的墳丘,
心想尋求皎月,眼前卻見黃沙茫茫。(內扎米)
有位語法學家乘船出遊,
他得意洋洋,向船夫開口:
“你可曾學過語法?”船夫說:“沒有。”
他說:“你的半生豈不虛度空拋!”
船夫的心被刺痛,悶悶不樂,
不再回答,從此不願開口。
一陣狂風起處,船兒陷入漩渦,
船夫問那高貴的語法學家,
“你可會游泳,請快告訴我?”
他回答說:“講游泳你可不能找我。”
船夫說:“如今小船陷入漩渦,
看來,你整個生命就要被淹沒。
我們需要的不是語法,而是游泳,
會游泳,你就能化險為夷,死裡逃生。”
送了命的,大海把他漂到海面,
被捲入波濤的,豈得生還,
當你辭別人世,一旦死去,
大海就吞沒了你的一切隱秘。
你視世人如驢樣愚蠢,
可你也如驢困在水上不得脫身。(莫拉維)
 伊朗文學作品
伊朗文學作品你高潔的聖徒不要把酒徒妄加指責,
別人的罪過,算不成你的罪過。
我行善作惡,與你何乾?
誰播下什麼種子,就收穫什麼。
既然現世的天堂近在眼前,
何必輕信聖徒虛妄的諾言?
哈菲茲自稱“酒徒”。他詩中的“酒徒”是指心口如一、潔身自好、不與權貴同流合污的高尚的人。他驕傲地歌 唱:
我們可不象那些信徒,終日拜功懺悔,
和我們交往,要的是清酒一杯。
哈菲茲呵,來世的功德不過是開懷暢飲。
來啊!讓我們虔誠地把功德積累。
有時,他在頌酒的詩里,筆鋒一轉也涉及到當時的政治:
酒能提神,但狂風把花兒掃蕩,
切莫貪杯,即使是琴聲飄蕩悠揚,
小心狡黠的密探,把酒杯藏在長衫袖裡,
這時代也鮮血淋淋,和盛著紅酒的杯兒一樣。
歌唱愛情也是哈菲茲的抒情詩的另一重要主題。他的愛情詩多為年輕時所作,寫得感情熾烈,真摯感人。有 愛情詩里也含著反宗教的詩句、有時他把愛情抽象化,玩世不恭地和宗教人士開起玩笑:
是醉是醒,人人都把真情嚮往,
清真寺、修道院,處處都是愛的殿堂。 (哈菲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