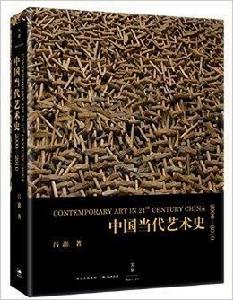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當代藝術史:2000—2010》以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社會現實為大背景,記錄了中國當代藝術最新十年的風雲激盪。我們需要在何種背景之上,才能真正理解十年來的當代藝術現實?如何理解無數碎片化現實之間的斷裂?藝術史家呂澎以宏大的歷史感和真誠無偽的性情,在劇烈變革的大時代中,書寫藝術家的工作,並透過這十年的藝術發展歷程,窺見社會在時代浪潮下的變革。把握當代藝術的現在,也就理解了中國社會的未來。
作者簡介
呂澎,藝術史家、批評家、策展人。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成都當代美術館館長。著有《溪山清遠:兩宋時期山水畫的歷史與趣味轉型》《中國現代藝術史:1979—1989》(合著)《中國當代藝術史:1990—1999》《20世紀中國藝術史》等書。策展有威尼斯雙年展特別邀請展“給馬可波羅的禮物”與“歷史之路”,以及“溪山清遠”系列等。
圖書目錄
序言
上篇 藝術生態
第一章 藝術體制與意識形態控制的式微
社會斷裂與意識形態控制的式微
“上海雙年展”與“首屆廣州當代藝術三年展”
策展人及其問題
第二章 藝術空間的興起
過渡時期的“實驗空間”
798:背景與新空間
藝術空間與美術館問題
宋莊及其象徵
第三章 市場、資本突進與體制問題
畫廊、博覽會與拍賣
爭議
藝術體制問題
下篇 藝術與藝術家
第四章 行為與暴力:美學的徹底退位
價值標準混亂的國際語境與個人主義的歷史回顧
“後感性”:“觀念藝術”之後
“感性”的蔓延
批評與爭論
第五章 觀念藝術與綜合藝術
觀念藝術問題
影像藝術與藝術家
綜合藝術與藝術家
新雕塑與雕塑家
第六章 新繪畫與畫家
1978年後的藝術史背景
語言流變與重要成員
個人主義新趨勢
早期新繪畫畫家的變化與綿延
最新傾向及其與傳統繪畫歷史的關係
尾聲 進入第二個十年的背景
注釋
人名索引
文摘
節選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國批評家和藝術家之間不斷討論的“國際接軌”問題,在有二十多位中國當代藝術家參加的20世紀最後一屆“威尼斯雙年展”(1999)這一事件中似乎有了結論性的回答。儘管中國當代藝術家早於1993年就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不過,由史澤曼(Harald Szeemann,1933—2005)策劃的本屆展覽在國內當代藝術圈子裡仍然獲得了影響,原因之一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當代藝術家之前已經成為烏利· 希克(Uli Sigg,1946— )這類更早關心中國當代藝術的西方人收藏的對象。與1993年的那一次相比,藝術家的興奮不再具有浪漫主義色彩。對於大多數藝術家來說,國際展覽既是自己的藝術得到證明的充分憑據,也是獲得國際銷售機會的平台。參加這種國際性的展覽,在1990年代初意味著“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欣喜,可是到了1990年代末,這種欣喜則已經轉化為一種見慣不驚的例行演出。同時,這種“國際接軌”始終受到批評家的質疑,這類越來越頻繁發生的“國際接軌”被認為更多的是西方標準的結果,參加了這次展覽的上海藝術家周鐵海(1966— )有一個啞劇腳本(以後他將其拍攝出來),對中國1990年代的藝術家的狀態作了有趣的報告,在這個短片裡,藝術家嘲諷了中國藝術家對國際策展人的那種可笑的依賴。
“國際接軌”的進程的確以一種超乎尋常的速度在加快。2000年的第三屆上海雙年展的策展人之一清水敏男乾脆用“滄海桑田”來表述上海或中國的變化,他將上海放在了國際化的都市“東京、紐約、香港、巴黎、倫敦、法蘭克福、曼谷、馬尼拉、新加坡、台北、首爾”這樣一個水平線上。他很明確地說:“今天的上海已經完全跟世界性的網路連線了。在這個城市舉辦第三屆上海雙年展,邀請世界各地的當代藝術家,標誌著上海的巨大變化。這次展覽可以說是上海變化理所當然的成果。”
第三屆上海雙年展於2000年11月在上海美術館裡舉辦,展覽的公告表明:“經文化部批准,由上海美術館主辦、上海有線電視台協辦的2000上海雙年展將於2000年11月6日-2001年1月6日在上海美術館舉行,並被定為第二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的主要展覽項目之一。”顯然,上海雙年展作為一個政府項目已經確定無疑。然而,在政府美術館裡舉辦有裝置藝術、錄像藝術、攝影藝術、媒體藝術作品參加的展覽,這意味著無論這個國家的藝術制度有無改變,而事實上為更為自由的藝術開啟了空間。這個展覽的國際化不僅僅體現在有亞洲、澳洲、歐洲、非洲、美洲18個國家和地區的67名藝術家(中國36名,外國31名)參加,更重要的是,“本屆雙年展嘗試按照國際通行的由策劃人推選藝術家的方式,成立了策劃人小組,負責推選參展藝術家及其作品,並最終由雙年展藝術委員會審定通過”。這個由不同國家的策展人組成的策展人小組開啟了上海雙年展的未來策展制度,也為其他城市的美術館提供了操作提示。
這屆上海雙年展的主題是“上海精神”。策展人侯瀚如(1963— )為此也寫了一篇可以看成是展覽主題闡釋的文章《從海上到上海—— 一種特殊的現代性》。他試圖將這次展覽放在一個超越性的層面上,他強調了“雙年展”應該“從全球視野的高度,觀察和判斷當代藝術在特定地區的發展狀態並對其實驗的、創造差異性的方面加以鼓勵”。由於侯瀚如文章通篇充滿著全球化問題和期望目標,因而不太關注涉及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城市所具有的特殊制度背景,結果,“上海精神”成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個假設的對象。
“通過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中國藝術家一起在‘海上·上海’(或英文Shanghai Spirit,即‘上海精神’)這一題目下同台展出,雙年展的主辦者和策劃人都希望從上海的現實條件出發,來探討當代藝術在上海這樣一個處於高速現代化進程中的‘東方大都市’中生存和發展的可能性,並推而廣之,使之成為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發展當代藝術的實驗場所。”
這位在法國生活多年的中國策展人似乎有意識地想擺脫中國的特殊背景,通過展覽創造出一個超越國度的藝術實驗平台。侯瀚如當然注意到了上海的“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性,他對上海自19世紀開埠以來的歷史給予了閃爍其詞的描述,還把上海描述為“為種種豐富多彩、迥然相異的文化創造提供了溫床”的城市,並且“衍生了一種以多元交融為基礎的獨特的現代性”。儘管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中斷了40年,可是在今天,“上海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城市”。
侯瀚如最後還是為他的“上海精神”作出了解釋:“如果有什麼可以被我們稱之為‘上海精神’的,無疑,上面描述的文化開放性、多元性、混合性和積極的創新態度,應該說就是它的核心。”他甚至用來自不同國家的藝術家和作品的差異性來證明這種精神的實在性。
第三屆上海雙年展的“國際化”似乎有基本的依據。批評家顧振清(1964— )認為本屆雙年展“是中國第一個真正國際化的雙年展”,這類樂觀主義者的依據是,展覽的策展人除了有中國批評家張晴(1964— )、李旭(1967— )以外,還有國際策展人清水敏男、侯瀚如,參展藝術家有基弗爾(Anselm Kiefer,1945— )、李禹煥(Lee Ufan,1936— )、馬修·巴尼(Matthew Barney,1967— )、森萬里子(1967— )以及哈尼·多諾( Heri Dono,1960— ),同時,參加展覽的還有在1980年代末或者1990年代初出國到西方國家從事藝術實驗的中國藝術家蔡國強(1957— )、黃永(1954— )、嚴培明(1960— ),這些中國藝術家的身份在國內人們的談論中似乎已經“國際化”了。展覽的“國際化”特徵最為重要的依據還有展覽中的作品。在之前的兩屆上海雙年展,觀眾只能見到繪畫(主要是油畫與水墨畫),而本屆上海雙年展包括攝影、錄像和裝置。事實上,人們沒有太多地關心展覽中的作品,而是關心這個在中國的展覽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國際化”的局面,在這樣的局面里,中國藝術處於什麼樣的位置。批評界更關心的是展覽所涉及的另外的問題,並且很快就有人對“上海”是否具有“開放性、多元性”的特徵表示質疑。
畫家兼批評家徐虹(1957— )在她的《選擇和被選擇——2000年上海雙年展》中說:
“2000上海雙年展為國際‘策展機器’開了綠燈,有人為此歡呼雀躍。但國際‘策
展機器’能不能為我們完成‘中國藝術走向世界’或者‘中國選擇世界’的任務?我對此表示懷疑。因為這種機器根本沒有設定我們心裡想像的那些程式。”
徐虹表達了對這個展覽當代藝術的上海雙年展取得的“合法性”的讚賞,卻懷疑遭受西方標準的限制,這樣的現實是否與“多元性”相匹配。
……
序言
對那些天生熱愛“歷史”的人來說,只要“歷史”這個詞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種能量無盡的興奮劑,無論“歷史”在時髦的思想家那裡被視為“舊的”、“新的”,抑或是根本就不存在。
在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家們遭受了哲學家們的嘲笑,前者被告知:“歷史學的秋天到來了。”在藝術史學科領域,早在1987年,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1935— )就寫出了一本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里才讓中國藝術家、批評家以及藝術史家開始重視的著作《藝術史終結了嗎?》(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Art?)。基於西方國家的藝術現實和藝術史學科的狀況,貝爾廷提醒藝術史家們:一種線性的、貌似有規律的歷史記錄方式應該終止了,因為人們遭遇的藝術現實已經處在交錯發生並缺乏分類學意義的狀況:沒有邊界,沒有邏輯,甚至沒有時間,因而也就沒有歷史。從2006年開始,漢斯·貝爾廷以“全球藝術”(Global Art)這個概念,來分析1989年“冷戰”結束之後發生在全球範圍內的藝術狀況,他與他的同仁試圖對發生在不同國家、地區、時間、文化、經濟、政治背景下的藝術進行更加富於開放性的觀察。
但是,如果我們共同使用的文字(無論是中文、英文,或是別的文字)繼續保持著文明的基本慣性,繼續保持著使用它們時所給出的知識語境以及對語境本身的警惕立場,我們都會在開放性地了解新知的同時,堅定自己的個人判斷與知識書寫。事實上,類似貝爾廷的觀點提供了對藝術史“開放”、“流動”以及“多重解讀”的理解空間,而不是讓人們始終飄浮在相對主義的白雲之上。
在一個網路的、多種媒體複合傳遞信息的時代,我們自然可以去利用所有的方式與路徑傳播我們的思想,書寫歷史同樣如此。我當然知道,對於那些需要通過現場進行觀察的藝術現象,傳統書寫方式已變得非常困難:我們如何去描述和分析在時間中呈現的一件通過綜合手段完成的作品?那些沒有經歷過現場的觀眾將對我們書寫歷史的文字如何進行閱讀和給予判斷?新技術正在以每分每秒的速度呈現出它不斷翻新的面貌,於是,當處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通過不同的手段操縱虛擬平台與技術載體的藝術家和合作者在共同創作新藝術的時候,我們能夠如何有效地去描述那些新的藝術生產過程與成果?
每一個藝術史家接受著他自己的知識背景的影響,接受著他所感知到的語境(社會、環境以及個人經驗)的影響,當然,也接受著不斷變動的藝術現象的影響。知識——如果有的話——本身因其特性而沒有限度。可是,文明的衍生要求我們必須去完成的判斷卻是有限度的。這就意味著,作為藝術史的寫作者,一旦確立了寫作的目標(“歷史”是我的興奮劑),我就不得不去確定書寫的結構與體例。於是,一個屬於個人眼中的藝術史就這樣開始塑形。
與大多數批評家和歷史研究者一樣,我對 2000—2010 年之間的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狀況,面臨著困惑與難題。像之前《中國現代藝術史:1979—1989》(與易丹合著,1992)、《中國當代藝術史:1990—1999》(2000)以及《20 世紀中國藝術史》(2006)所使用的體例不再完全適用於對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藝術史的寫作,我注意到,新世紀十年的藝術是伴隨著影響藝術變化和發展的環境生態同時進行的,其關聯密切的程度,使得我們不得不將整個藝術生態的變化和發展看成是十年藝術史的一部分。在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去書寫藝術家的工作?如何在書寫中去把握不同城市與地區的藝術家工作之間的關係?我們該如何使那些直接和間接影響藝術家工作的具體問題——體制對藝術家的制約和放鬆,藝術空間的需求和變化,作品的展覽以及去處,畫廊和拍賣行與藝術家的關係,等等——與我們理解的歷史發生關係?基於這十年藝術生態變化在當代藝術家的工作的重要性與創作上給予影響的性質,同時也基於對藝術家的工作進行有利於敘述的分類,我將本書的結構與體例分為“上篇 藝術生態”和“下篇 藝術與藝術家”。通過這兩個部分的安排,讀者可以對這十年的藝術有一個符合多重視角的整體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