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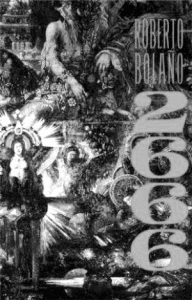
《2666》全書總計1125頁,相當於中文100萬字,分5部,講述了五個獨立又彼此呼應的故事。
第一部《文學評論家》,講述4位評論家分別生活和工作在英國、西班牙、法國和義大利,都在研究德國作家阿琴波爾迪的作品和生平。四人在國際研討會上相識,由於學術觀點一致而成為朋友和情人。最後,他們在墨西哥開會時聽說了殺害婦女的事情。但是,四人都不敢站出來揭露罪行,而是紛紛“合情合理”地開了小差。英國人飛回了倫敦;義大利人根本沒敢露面;法國人整天埋頭讀書;西班牙人帶著墨西哥小姑娘跳舞和做愛,最後回馬德里去了。
第二部《阿瑪爾菲塔諾》,講述智利教授攜全家來到墨西哥避難的故事。他顛沛流離,歷盡磨難,最後,妻子離他而去,女兒也被黑社會綁架。面對苦難,教授顯得憤怒而無奈,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拉美小知識分子情緒的代表,尤其是被獨裁政權迫害的典型人物。
第三部《法特》,講述美國記者法特去墨西哥採訪拳擊賽的遭遇。法特也聽說了連續發生的婦女被殺案件,經過採訪和調查,發現了大量駭人聽聞的故事。法特是敢於面對殘酷現實的知識分子,但終因勢單力薄而無所作為。他尖銳地指出,人性惡的膨脹會成為人類毀滅的死神。
第四部《罪行》是全書的高潮,集中描寫了墨西哥北方婦女連續慘遭殺害的事。具體講述了近200個案例。其中,除了揭露犯罪集團的殘暴、瘋狂和兇狠的嘴臉之外,作者還用了大量筆墨描寫政府的腐敗無能,有些官員甚至與犯罪集團沆瀣一氣、同流合污,造成販毒、走私和殺人、強姦案件的急劇增加。作者也塑造了一些勇於鬥爭的婦女形象,但邪惡勢力太強大了,她們的奮力掙扎收效甚微。
第五部《阿琴波爾迪》講述德國作家阿琴波爾迪複雜曲折的人生道路。阿琴波爾迪是貫穿全書的主線。起初,他是英、德、法、西文學研究界研究和追蹤的目標,他到墨西哥之後,又成為他妹妹和朋友們尋找的對象,由此構成全書最大的懸念。阿琴波爾迪的人生道路坎坷,他與德國貴族有過交往,親眼看到了貴族們糜爛的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無意間發現了一位蘇聯猶太人的手記,因此得以了解史達林對作家的迫害情況。在戰爭中,阿琴波爾迪最為慘烈的是耳聞或者目睹了屠殺戰俘和猶太人的活動。戰後他開始寫小說的主要動因與表達內疚和懺悔罪孽有關。聽說墨西哥有殺害婦女的罪行,他秘密去墨西哥調查,但行蹤十分神秘,讓人無法找到他的下落。
作者介紹
羅伯特·波拉諾(RobertoBolaño,1953—2003)出生於智利,父親是卡車司機和業餘拳擊手,母親在學校教授數學和統計學。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諾再次
 羅伯特·波拉諾
羅伯特·波拉諾回到智利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卻遭到逮捕,差點被殺害。逃回墨西哥後他和好友推動了融合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以及街頭劇場的“現實以下主義”(Infrarrealism)運動,意圖激發拉丁美洲年輕人對生活與文學的熱愛。1977年他前往歐洲,最後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結婚定居。2003年因為肝臟功能損壞,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隆納去世,年僅五十歲。
波拉諾四十歲才開始寫小說,作品數量卻十分驚人,身後留下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三部詩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偵探》在拉美文壇引起的轟動,不亞於三十年前《百年孤獨》出版時的盛況。而其身後出版的《2666》更是引發歐美輿論壓倒性好評,均致以傑作、偉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讚譽。蘇珊·桑塔格、約翰·班維爾、科爾姆·托賓、史蒂芬·金等眾多作家對波拉尼奧讚賞有加,更有評論認為此書的出版自此將作者帶至塞萬提斯,斯特恩,梅爾維爾,普魯斯特,穆齊爾與品欽的同一佇列。
小說榮譽
《2666》獲美國國家圖書批評家獎小說獎(2009年)
《紐約時報書評周刊》2008年十佳圖書
名家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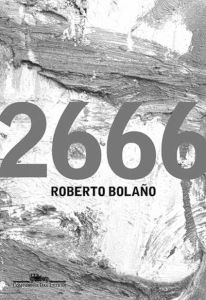
西班牙著名女作家阿娜·瑪利亞·莫伊斯在西班牙《國家報》上說:“《2666》是小說中的長篇小說,毫無疑問,是一座豐碑,是波拉尼奧全部創作的最佳之作。”
評論家羅德里戈·富雷桑說:“《2666》是全景小說,它不僅是作者的封頂之作,而且是給長篇小說重新定性的作品,同時,它把長篇小說提高到一個令人感到眩暈的全新高度。”
伊格納西奧·埃切維里亞說:“《2666》是波拉諾的代表作,是一部滔滔大河般的巨著。作為全景小說,它的能力是既連結和統一起以前的全部作品又大大超越前輩。”
讀書評論
《2666》從整個人類的發展過程中揭示出人類貪婪、自私和兇殘的本性在當代迅速膨脹,愈演愈烈,不可遏制。危及人類生存的痼疾,例如瘋狂地發展物質生產,全然不顧生存環境;惡性的市場競爭;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道德淪喪;官場腐敗……種種倒行逆施,都源於自私和貪婪。高科技迅猛的發展非但沒有改善人性,反而推動人類社會像高速列車一樣駛向萬丈深淵。作者認為,自私和貪婪之心人皆有之,一旦有了滋生的條件就會發作。在經濟社會裡,權貴集團依靠金錢實力統治底層的人們,他們不僅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還壟斷著一切輿論工具,甚至企圖鉗制和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底層的人們由於無權無勢往往是受害者。這樣的制度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取向:驅動人們追求金錢、攀附權貴,充當物慾的奴隸。書中也有少數清醒的知識分子,但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要么無可奈何,要么悲觀失望,要么甘心充當權貴的智囊和喉舌。總之,四分五裂,形不成團結一致的理性力量去扭轉向惡的趨勢。受壓迫的底層人們,也有自己的問題:由於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愚昧、無知是必不可免的,狀態是一盤散沙。對金錢、暴力和權力的信仰在人們心裡產生的要么是貪婪,要么是恐懼,要么是無奈,要么是絕望。書中也有善良的人們,也有見義勇為者,也有冷靜思考者,但面對著強大的權貴勢力和黑惡團伙,他們只有犧牲。作品第三部《法特》中有這樣的看法:“人類的瘋狂和殘忍都不是當代人發明的,而是咱們老祖宗的創造。可以說,古希臘人發明了人性惡,發現了人人心裡有邪惡。但是,到了今天,咱們對典型的邪惡已經司空見慣,其典型事例已經微不足道。正是希臘人開啟了一系列邪惡變異的可能性。可是,至今咱們對這些變異並沒有清醒的意識。也許您會說,時代在變,一切在變。是的,當然在變,可是犯罪的事實沒變,因為人性惡沒變。”進入21世紀,人性惡更加膨脹了。以公平、正義的名義進行的殺戮,以和平發展、“互利”名義進行的資源掠奪,在高科技的幫助下,規模大、程度激烈、手段狡猾的大量犯罪事實,都一一證明了人類的貪婪、瘋狂和殘忍已經上了一個新台階,達到了自我毀滅的新高度。嚴重的是,人類還沒覺醒,還對紙醉金迷的生活津津樂道。《2666》的作者俯瞰人間,看到的是一片荒漠,人性惡的膨脹則是這荒漠中“恐怖的綠洲”。

在第四部《罪行》里,作者用大量的事實揭露出墨西哥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大權統統掌握在權貴集團手中。犯罪團伙、販毒、走私等黑社會組織有政治保護傘。有良知的人們感到悲觀和絕望,只能憤憤罵權貴勢力是“卑鄙骯髒的野獸”。橫行霸道的權勢人物受到“制度保護”,窮苦百姓的求告無門也是社會制度造成的。因此,書中的人物罵道:“這是墨西哥的一個特色啊!是拉美特色啊!”
在《2666》中,中產階級普遍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真正做事情的不多”,得過且過、敷衍塞責成風。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為政府工作的。政府養活他們,暗中注視著他們的動向”,因此這是一個附庸在權貴集團身上的寄生物,沒有獨立生存的基礎。從思想上說,他們看不到制度改善的希望,只看見了官場腐敗的醜惡表現,因此處於悲觀絕望之中;要么就趨炎附勢,按照潛規則行事。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經過了打擊之後,也處於悲觀狀態。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後連續發生經濟危機,他們尤其不相信什麼政黨政治的能力。《2666》中充滿了“不信任感”,因為“一切都是欺騙”,大家“只能苟延殘喘地活著”。在第一部《文學評論家》里,分別來自英國、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教授兼文學評論家面對連環殺人案的表現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四位教授全都放棄了自己的理想,更不要說揭露和批評社會犯罪現象了。這樣的結局是意味深長的——想得多、做得少的讀書人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往往當逃兵。
在敘事藝術方面,作者用了十分冷峻的手法,讓大量事實說話,例如,戰爭中對戰俘和猶太人的殺戮、墨西哥在短短几年裡發生的婦女被強暴和殺害的案件、瘋狂奢侈的消費和浪費、狂歡縱慾的聚會……讓鐵的事實佐證人性惡發展的趨向。在寫實的同時,作者也巧妙地描繪心理活動,如夢幻、聯想、直覺等。在作品結構上,5個組成部分可以獨立成章,又有枝蔓開來的大量枝杈形成蓬蓬勃勃的巨型華蓋,與巧妙的內在聯繫和統一軸心一起,構成一棵參天大樹。作者把情愛、性愛、兇殺、戰爭、文學研究和創作以及懸疑諸多小說元素自然地糅成一體,尤其是對大舞台和小細節的巧妙結合更令人拍案叫絕。大舞台包括地理上的描述和對社會眾生相的描繪;小細節則滴水不漏地涉及到穿衣吃飯等生活場景的細部、複雜的心理糾結、情感的微妙變化。《2666》的敘述藝術既是對20世紀下半葉各類小說技巧的高度概括,又有作者獨具匠心的創造。這種創造的理論說法叫做“全景式長篇小說”。這一理論的主要特徵是:超越階級意識形態的局限,從人類意識的高度看人性的複雜和變化;舞台儘量設計得博大;時間長;人物多;讓豐富的事實說話;敘事的話語則是冷峻和白描式的。
《2666》所描寫的地域範圍遠遠突破了拉丁美洲的天地,站在全人類的現實高度看人性惡的膨脹,更在預見未來。因此,這部作品的意義超出了自身的文學價值,對於研究歐美國家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思潮變化、人類文化價值觀念也具有參考價值。
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社會事件後,21世紀初又發生了“9·11”事件和全球範圍的經濟危機,拉美少數知識分子在反思。反思的過程中,作者羅伯特·波拉諾超越了簡單的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從人性的表現和變化觀察社會問題,因而有了《2666》的問世。書中流露出一種“淡淡的哀愁”,因為作者看不見解決人性惡膨脹的出路。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價值觀甚囂塵上的時候,人類應該有所警惕並找出應對措施,努力避免人類的自相殘殺和毀滅。或許這就是《2666》的創作初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