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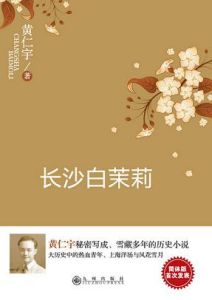 《長沙白茉莉》
《長沙白茉莉》九州出版社此次出版《長沙白茉莉》作者署名還原為黃仁宇。小說講述了上世紀30年代發生在上海灘的故事。作品以湖南青年趙克明為貫穿全書的線索,描述了那個時代以上海-長沙為主軸的中國社會圖景。青年學生趙克明受同班女友的影響,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研習團,然後被派往上海參與中共與上海黑幫老大杜大耳的黃金交易,並被杜大耳利用,捲入上海工人罷工事件。“長沙白茉莉”是書中女主角、交際花胡瓊芳的外號。胡瓊芳是杜大耳的情人,也是趙克明在上海的聯絡人,如魚得水地周旋在各種勢力之間。
在黃仁宇筆下,趙克明懵懂彷徨,胡瓊芳顧盼生姿,杜大耳威風凜凜。作者特別聲明,本書“局部地摻雜了一些真人實事”。在這樣的提示下,讀者很容易發現,小說中的杜大耳無疑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作者借一個涉世未深的湖南青年之眼,將青幫與國共兩黨及殖民勢力之間撲朔迷離的關係、上海工人運動的風雲變幻以及杜月笙勢力掌控下的上海市井社會和盤托出。趙克明所看到的人和事,正是那個時代的縮影。黃仁宇用他嫻熟的筆觸將大歷史中小人物的躑躅無奈、大歷史的波瀾壯闊描寫得淋漓盡致,與他一貫提倡的“大歷史觀”不謀而合,殊途同歸。
出版情況
九州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黃仁宇全集》,此次《長沙白茉莉》的出版,可以看作是《黃仁宇全集》的補遺。據了解,《長沙白茉莉》原用英文寫成,1990年由台北時報出版社出版繁體中文版,1998年台北商務印書館再版。小說出版時署名李尉昂,他另一部小說《汴京殘夢》出版時署的也是這個筆名。縱觀黃氏作品,似乎只有這兩部使用了筆名。
作者介紹
黃仁宇出生於湖南長沙,是蜚聲中外的歷史學家,以“大歷史觀”(macro-history,亦即“巨觀歷史”)聞名於世。1985年,時年63歲的黃仁宇在台北版的《萬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大歷史觀”的概念,提倡“將巨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引入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而不主張糾結於事件的微觀層面。
在他看來,大歷史觀不是去研究諸如秦始皇焚書坑儒是聽取誰的意見,交由誰付諸實施的具體過程,也不去是去進行武則天穢亂春宮的道德批判,大歷史觀要求對中國歷史整體的認識和把握,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和走向,洞悉其背後深刻的自然環境、經濟和文化因素,從而“把一切事件的發生,均納入歷史的潮流中”。
大歷史觀在史學界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影響深遠。其代表作《萬曆十五年》出版以後,黃氏作品受到讀者追捧,從早期的英文論著到後期的中文論著,幾乎每一出版都會引起學界的熱烈討論和讀者的普遍關注。黃仁宇所著主要是歷史著作,不少人還不知道他曾經寫過小說。《長沙白茉莉》就是是黃仁宇僅有的兩部小說之一。
創作背景
寫《長沙白茉莉》的李尉昂就是那個寫《萬曆十五年》的黃仁宇。當然,李尉昂更接近寫《黃河青山》的那個黃仁宇。從時間上看,黃仁宇是先於1980年至1983年寫完《黃河青山》這部回憶錄,然後再於1989年寫《長沙白茉莉》。1980年正是歷史學教授黃仁宇離開教職的年份,那一年,黃仁宇因多年沒有新著問世,且上他的課的學生寥寥無幾,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從正教授的職位上解聘,背後更深刻的原因則是學校政治權力的傾軋,黃仁宇滿是失落憤懣。《黃河青山》多述平生不得志,同時也在人事交融的憶敘中,反覆強調自己的大歷史觀、歷史研究的思路,不難感覺到他內心的焦慮和壓抑。而寫《長沙白茉莉》的黃仁宇,已功成名就,冠蓋滿京華,《萬曆十五年》在國內外被熱情地認可,先前的所有焦慮壓抑似已與時間和解。對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軌跡,也有了別一番的理解。《黃河青山》里,黃仁宇多次感慨生命的偶然性,在生命中,我們似乎遇到無數做決定的機會,但是回顧時發現,每一個轉折其實都只有一座橋,選擇縮小到要不要走過去;到寫《長沙白茉莉》時,黃仁宇對生命偶然性的看法已經變得輕鬆。
小說主角
小說的時間跨度不到三年,一個叫趙克明的年輕人,被黃仁宇請出場時,仿若堅毅剛烈之士:“別搞錯。我仍是共產黨員。就算你用手槍抵著我的腦袋問我同一句話,我也還是這么說。”這種話語,對於英雄主義教育曾雄赳赳行走在社會意識形態中的國度,熟悉得讓你能條件反射似想像出說話人的臉龐,濃眉大眼,國字臉,一臉正氣,鋪滿鋼鐵般的意志好沒有私慾的表情。而黃仁宇要寫的,是一個承受生活中各種偶然事件的拍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被時代、周圍世界、他人以及慾念紛紛的自己所塑造的小人物。趙克明參加革命,僅僅因為他愛戀的女子帶他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習團”,並不是如一廂情願的宣傳教育中,受烏托邦的號召,油然產生崇高的理想、時代的責任感和解放全人類的終極目標,這是愛情荷爾蒙的烏龍,而非腎上腺素的催情。當他作為文學青年,所珍愛的一切名著被無產階級的文藝觀粗暴否定成庸俗資產階級文學時,他內心產生難以言狀的彷徨和困惑。他從長沙坐船來到上海,是因為一個以組織的名義、領導的身份出現的人,給了他一個崇高神秘不可抗拒的任務,要他護送一批黃金給上海地下黨。這些黃金,全部是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的過程中掠奪一切私人財產而來。在上海,他遇見了交際花胡瓊芳,然後是她的情夫杜月笙,當時上海黑幫最高頭目。繼而,他奉命趁機打入青幫內部。
至於那位單線聯繫的領導,儘管在世人面前有怎樣狂熱的幹勁和堅定的信念,但變節之快,直讓趙克明無法相信事實。也許,日後的他將搭船去台灣度過餘生;也許,他和趙克明一樣,在大陸身陷囹圄,誰能保證,無間道的趙克明,會被勝利後的新政權順利接受歸隊;也許,他們都死在了隨後同仇敵愾的抗戰中;也許……人生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趙克明這個主角,就這樣,從歷史影影綽綽的人群中,被黃仁宇拈出來,放到30年代的上海顯影。他替杜月笙做了一些事,並非扭轉歷史之大事,卻扭轉了自己的人生。他在他人的安排中,稀里糊塗成為一個丈夫,又暈頭轉向間成為一個被妻子拋棄的男人,當他發覺自己差點成為另一個女人的丈夫時,他倉皇出逃。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趙克明還年輕,還會繼續有偶然的事件隨時改變他生命的軌跡,接下去的故事,不可預測,你也完全不用去管他究竟是誰,是否有真實原型。事實上,每個人的生命里都會有相類似的故事,只不過上演時,道具和布景不同,舞台和觀眾不同,濃縮起來,凝聚一下,你才能看到它們閃著光里映照的命運的必然。
小說家李尉昂作《長沙白茉莉》,始於一個青年對某一個自我身份的確定表述,以這個青年欲掙脫命運無常的擺布而出逃做結。在一個具體的時代社會背景里,一個人周圍的那些人事,決定了這個人的命運。他愛戀的女子死了,所以他純潔的愛情理想跌落粉碎,無聲無息。他的朋友拉皮條把一個女人的身體引入他的生活,所以他曾經對美好性愛的幻想墮落成兩具肉體的交疊。黑幫權力戰爭的擴張,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入贅為黑幫首領的女婿,他的合法妻子在個人的壓抑失落中,以躥升的火焰般的激情與人私奔,使他成為被妻子拋棄,卻仍須被妻子的社會關係利用的人物。在波濤暗涌的歷史面前,個人顯得渺小卑微,即便身處浪口,也是一時之風所為,而它一個浪撲來,個人霎時無從喘息,浪奔開後,生活依舊可以在驚魂未定時安靜地繼續。
故事情節
在故事情節的安排上,作者特別聲明,本書“局部地滲雜了一些真人實事”,“此種背景上之情節以陪襯虛構之主題故事為宗旨”。通覽全書以後再翻檢並不遙遠的歷史,我們卻能看出歷史正以另一種表達方式浮出水面。我們會很容易也很驚異地發現,書中所寫的“青幫老大、上海黑社會總司令”杜大耳,無疑就是上海灘大名鼎鼎的杜月笙。作者借一個涉世未深的湖南青年之眼,將青幫與國共兩黨及殖民勢力之間撲朔迷離的關係、上海工人運動的風雲變幻以及杜月笙勢力掌控下的上海市井社會和盤托出。趙克明所看到的人和事,正是那個驚天動地的時代的縮影。比如,為了說明上海青幫的勢力範圍,作者讓趙克明去和測字的、拔牙的以及開租書店的人打交道,使讀者對舊上海幫會勢力的橫行及組織規範有所了解。作者的種種努力,是將角色放置在時代的背景下,通過角色的種種遭遇,表現拉扯著這個特定歷史時空的種種力量,讓讀者感受大歷史中小人物的踟躕無奈,探究小人物背後大歷史的波瀾壯闊與鮮活生動,進而窺見歷史的形貌——與他一貫提倡的“大歷史觀”不謀而合,殊途同歸。儘管作者用了筆名,但是他實踐大歷史的企圖還是讓人一覽無餘。
作品評價
歷史學家黃仁宇的長篇小說《長沙白茉莉》(以下簡稱《白茉莉》)似乎講述了一個如今正“髦得合時”的諜戰故事。但後者風頭雖健,到底無法望《白茉莉》之項背。這部“秘密寫成、雪藏多年”的歷史小說在諸多方面可圈可點,理應納入文學經典之列。
小說最先打動我的是人物身上呈現的斑駁色彩。斑斕是生命的本色,駁雜乃生活的常態,色彩單一至透明的童話式人物在《白茉莉》中無處容身。以杜月笙為原形的黑社會大佬杜大耳既狡黠、狠毒也不乏膽識和義氣;交際花胡瓊芳妖冶魅惑、風情萬種,華美的衣襟掩映著墮落的靈魂,末了,殘存的一縷善意卻又靈光乍現;掛名妻子蒲艾齡把囂張跋扈貼在臉上,終究藏不住心底的隱痛和善良;甚至著墨不多的閎家母女、僅有幾句台詞的老僕阿朱,一個個都因著光影的駁雜而豐滿鮮活、栩栩如生。
主人公趙克明尤然。作為共方臥底,他思想不夠純潔、信仰不甚堅定,甚至任務也不明確;但與此同時他又敏銳、善感、擅長分析和推理。
這樣的人物恰好充當觀察者和傾聽者,敘事人的角色捨我其誰?我們躡足追蹤趙克明,一頭扎進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場,借用他清亮得近乎原生態的眸子掃視彼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外國租界到亭子間;從青幫上層到十六鋪碼頭;從交際花姨太太到革命志士,熱氣騰騰的日常生活、緊張微妙的勢均力敵、驚險不斷的江湖行走……一座城搖搖欲墜,一代人彷徨無地。
作者開宗明義說道:“這是一部‘時代’小說”。“時代”在這裡顯然並非背景,而是足以與趙克明等量齊觀的主角之一。透過小說的視窗,黃仁宇展開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引領我們眺望尚未走遠的歷史—市聲還在喧囂,細節蔥蘢搖曳。
諜戰題材小說和影視劇鑒於其大眾流行話語的本質屬性,往往不忍割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正邪較量、邪不壓正的主題設定。黃仁宇卻難能可貴地自覺將道德審判無限延期了。在精悍到不足80字的序言中,作者特彆強調“尤無意以之作任何道德上之褒貶”,如果遵照主流意識形態標準對青年趙克明進行評判,從最初因為朦朧的愛情加入“馬克思主義研習團”到最終走投無路、躑躅人海,青年趙克明的選擇和行為屢屢表現出青澀、脆弱甚至投機等不成熟、不光彩的側面。同樣的人物如果出現在石鐘山《地下地上》或者龍一的《潛伏》中,開篇就會作為革命隊伍中的一粒沙子被毫不留情地剔除,在那裡,筆墨和紙頁應該留給光榮的英雄。
事實上,小說中的工運骨幹也已經採取類似的剔除行動,只不過在作者的悉心關懷之下,趙克明總是大難不死,頑強地展示著大時代中小人物的狼狽和堅韌。不排除這種處理方式與作者的疏離立場緊密相關,但米蘭·昆德拉的敘事法則竟然完美現身歷史學家偶一為之的小說,仍然令我驚嘆不已。
黃仁宇是注定不肯按常理出牌了。在合上書頁回味故事的過程中,一個疑問倏忽而至:為什麼叫《長沙白茉莉》?交際花胡瓊芳外號白茉莉,但她一則並非主角,二則也撐不住那幽渺淡雅的香氣。
或許,這部小說就是一株低調而精彩的白茉莉,靜靜地開放在熱鬧的文壇,給粗率單薄的寫作提神醒腦。
將搬螢幕
據悉,著名導演李安曾表示對此小說有興趣,希望能把它搬上螢幕。國內亦有多名導演表達同樣的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