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金瓶梅》的版本主要有兩個系統:
一為現存最早的有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東吳弄珠客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詞話》,一百回,所謂“詞話”是指書中插有大量的詩詞曲賦和韻文,這個本子及其傳刻本,統稱詞話本。
一為崇禎年間刊行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又稱《原本金瓶梅》,故一般稱這個本子及其傳刻本為崇禎本。清康熙年間張竹坡對崇禎本加以評點,推出《第一奇書金瓶梅》。這就是張竹坡的批評本。流行非常廣。清同治年間,蔣敦復刪削《第一奇書金瓶梅》不潔文字而成的《繪圖真本金瓶梅》,民國五年由存寶齋印行,成為《金瓶梅》的第一部刪節本。齊魯書社出版了崇禎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金瓶梅詞話》一書是一部古今艷情小說中燦爛的一朵文化奇葩。曾因歷史的變遷遭到打擊,後因戰亂以致流失海外。
隨著新時代的改革開放,社會的研究需要,港台金瓶梅研究協會從日、英、法、美、德等國家蒐集加以整理,才從新得以完善。讓這部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燦爛文化奇葩,重放異彩。
此書故事曲折、生動、情節感人,並有六十餘幅古代俏男、倩女狂愛之圖片,實為讀書愛好者茶餘飯後的精神食糧、藏書愛好者收藏之精品。
《金瓶梅詞話》算得上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與《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列。但《金瓶梅》是一部奇書,被列為“淫書”,歷代禁止公開出版發行。
《金瓶梅詞話(初刻本)》仿古印製,它包括擁有最充分原始信息、最具可讀性的"崇禎本"全部內容(該版本曾面向中國高級領導幹部、學者和大型圖書館少量印製),並附錄萬曆"詞話本" 中和"崇禎本"內容不同的部分(將"詞話本"中與"崇禎本"差別較大的第一回前半部分,第五十三、五十四回,以及詞話本特有,而崇禎本所無的"欣欣自序 "、"廿公跋"、"詞曰"以及"四貪詞",也一併附上)使得讀者花一套書的錢,同時可得兩大主要版本的內容。崇禎本的200幅精美插圖,雖然有"春宮色彩 ",也全以每圖一頁予以保留。
內容概況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金瓶梅詞話》是我國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為素材的長篇小說。它的開頭據《水滸傳》中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改編,寫潘金蓮未被武松殺死,嫁給西門慶為妾,由此轉入小說的主體部分,描寫西門慶家庭內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門慶與社會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縱慾身亡,其家庭破敗,眾妾風雲流散。書名由小說中三個主要女性(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萬曆年間,已有《金瓶梅》抄本流傳。據袁中郎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寫給董其昌的信,他曾從董處抄得此書的一部分;又據《萬曆野獲編》,沈德符在萬曆三十七年(1609)從袁中道處抄得全本,攜至吳中,此後大約過了好幾年,才有刻本流傳。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萬曆四十五年丁巳(1617)東吳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詞話》,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後有崇禎年間刊行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一般認為是前者的評改本。它對原本的改動主要是更改回目、變更某些情節、修飾文字,並削減了原本中詞話的痕跡。清康熙年間,張竹坡評點的《金瓶梅》刊行(此書扉頁刻有“第一奇書”四字,因此也稱作《第一奇書》)。它是以崇禎本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張氏的回評、夾批,並在卷首附有《竹坡閒話》、《金瓶梅讀法》、《金瓶梅寓意說》等專論。這個本子在清代流傳最廣。
《金瓶梅詞話》的作者,據卷首“欣欣子”序說,是“蘭陵笑笑生”。用古名稱為“蘭陵”之地有二,一在今山東嶧縣,一在今江蘇武進縣,以何者為是,尚無定論。這位“笑笑生”究為何人,也至今無法確認。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作者是“嘉靖間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錄》中說作者是“紹興老儒”,謝肇淛《金瓶梅跋》說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門客,皆語焉不詳。後世人們對此提出種種猜測和推考,先後有王世貞、李開先、屠隆、徐渭、湯顯祖、李漁等十幾種不同的意見,但尚沒有一種意見能成定論。關於小說的創作年代,也有嘉靖與萬曆兩說,研究者一般認為後者為是。如小說中引用的《祭頭巾文》,系萬曆間著名文人屠隆之作;寫西門慶家宴分別用“蘇州戲子”、“海鹽子弟”演戲,為萬曆以後才有的風氣,都可以作為證據。
雖然《金瓶梅詞話》作者的情況不詳,但仍可以推斷為我國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有人認為,根據《金瓶梅詞話》較多保留了說唱藝術的痕跡、書中情節與文字前後頗有牴牾、較多引錄前人作品等情況,這部小說當是和《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一樣,是由某個文人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改寫而成,但這一說法難以成立。和《三國演義》等不同,在《金瓶梅詞話》問世之前,根本沒有內容相似的雛型作品流傳,而且據《萬曆野獲編》的記載來看,廣聞博識的沈德符在未讀這部小說之前,也不知道這是一部什麼樣的書,此其一;《金瓶梅詞話》是一部大量描繪日常生活瑣事的小說,沒有傳奇色彩,故事性也不強,不易分割成相對獨立的單元,儘管在這部小說流行漸廣以後,也有取其片斷為說唱材料的情況,但從全書來說,它不適宜作為民間說唱的底本,此其二。至於保留了說唱藝術的痕跡,只能說是作者有意模擬及個人愛好的表現。
特徵
《金瓶梅詞話》是以北宋末年為背景的,但它所描繪的社會面貌、所表現的思想傾向,卻有鮮明的晚明時代的特徵。小說主人公西門慶是一個暴發戶式的富商,是新興的市民階層中的顯赫人物,他依賴金錢的巨大力量,勾結官府並獲得地方官職,恣意妄為,縱情享樂,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無休止的滿足。他以一種邪惡而又生氣勃勃的姿態,侵蝕著末期封建政治的肌體,使之愈益墮落破敗;而他那種肆濫宣洩的生命力和他最終的縱慾身亡,也喻示著他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在當時難以得到健康的成長。當然,對晚明時代各種社會問題,作者並未能提出明確的理論見解,但小說卻以前所未有的寫實力量,描繪出這一時代活生生的社會狀態,以及人性在這一社會狀態中的複雜表現,這是很大的成功。
《金瓶梅詞話》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它所描寫的官商關係和金錢對封建政治的侵蝕。本書在討論漢初賈誼、晁錯的政論文時,就已指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於商人所擁有的金錢力量足以對以政治權力為核心的封建等級秩序構成破壞。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工商業的興盛,這種破壞又終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這樣一個時代。從《金瓶梅詞話》中我們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頒布的《明律》中關於房舍、器物、服飾等諸方面區分等級的規定,這時早已形同虛設。西門慶一家物質享用的奢華,遠遠超出於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會被路人議論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來的宅眷”,“是貴戚皇孫家艷妾”。而官僚階層面對這種金錢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紆貴。第四十九回寫文採風流的蔡御史在西門慶家作客,受到優厚的款待,還得了兩個歌妓陪夜,對於他的種種非法要求,無不一口應承。而位極人臣的蔡太師,也因收受了西門慶的厚禮,送給他一個五品銜的理刑千戶之職(第三十回),做了一筆權錢交易;在過生日之際,更以超過對待“滿朝文武官員”的禮遇接待這位攜大量金錢財物來認乾爺的豪商。至於賄賂官吏,偷稅逃稅,在西門慶更是輕而易舉之事。封建國家機器在商人的金錢的鏽蝕下,已失去其原有的運轉能力。
而西門慶正是憑藉其金錢買通政治權力,在相當的範圍內為所欲為,乃至發出這樣的“豪言壯語”:
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擄了許飛瓊,盜了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五十七回)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西門慶這樣的人物並無機會被引納為國家機器中的核心分子,他和這個封建政權多少仍是處於游離狀態的。小說中有兩處描寫頗值得體味。一是四十九回寫歌妓董嬌兒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紅紙大包封著”的一兩銀子,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嘲笑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裡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這裡顯示了富商對文官的寒酸的卑視。另一處是五十七回寫西門慶對尚在懷抱中的兒子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這裡卻又表示了對做“文官”——國家機器中的核心分子——的嚮往。
小說在這方面雖沒有充分展開,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如果說西門慶是晚明市民階層的一個代表人物的話,這類人物雖然能夠以金錢買到一部分政治權力為己所用,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從根本上影響這部國家機器。作為一種社會勢力,他們既不是獨立的,也不是積極反抗的;在他們興起之時,就已經捲入到封建政權的腐敗過程中去了。所以,生命力的肆濫的宣洩,成為西門慶這一類人物體認和表現自身存在的方式。
在揭示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方面,《金瓶梅詞話》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官商勾結、錢權交易,而是十分廣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儘管過去的小說在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我國戲曲、小說的特質之一,是“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有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即使歌頌民間反抗鬥爭的《水滸傳》,也還是讓正義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張(包括死後成神這一類給讀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這多少給那種黑暗的社會抹上了一層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詞話》中,我們卻看到許多無告的沉冤,難雪的不平:西門慶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蓮,逍遙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對他莫可奈何;苗員外慘遭殺害,主犯苗青卻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蓮被害死後,她父親想給女兒報仇,結果也被迫害而死……,這種無辜者受盡煎熬、悲慘而死、毫無抵償的故事在小說中比比皆是。而那個作惡多端的西門慶,卻享受了一輩子的富貴榮華。他最後的縱慾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檢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惡有惡報”;甚至他轉世投胎,也仍舊是做富戶。現實的沉重和陰暗,使讀者感受到巨大的壓抑,從而更有可能認識到封建社會的本質。這種描寫,一方面是因為封建末世的政治確實格外地混亂無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作者對傳統道德已徹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夠有效地約制社會的統治階層,提供正義的理想。與上述內容相關聯,《金瓶梅詞話》不僅反映了社會政治的黑暗,還大量描寫了那種時代中人性的普遍弱點和醜惡,尤其是金錢對人性的扭曲。在這部一百回的長篇小說中,幾乎沒有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裡勾心鬥角,相互壓迫。西門慶家中妻妾成群,花團錦簇,但眾妻妾乃至奴婢之間的爭寵奪利,無所不用其極,顯示出在多妻制婚姻關係中女性心理的陰寒。小說有很多地方寫到西門慶在占有各色女子時,一面尋歡作樂,一面商談著財物的施予,兩性關係在這裡成為赤裸裸的金錢交易。還有,像五十六回寫幫閒角色常時節因無錢養家,被妻子肆口辱罵,及至得了西門慶周濟的十幾兩銀子,歸來便傲氣十足,他的妻也立即變得低聲下氣。這些描寫,都尖銳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錢的驅使下是何等的可悲與可憐。而且,作者明顯是有意識地在描寫兩性之間為金錢所左右的交往時大量引用那些辭采華美、富於溫情的詩、詞、曲,讓人感覺到:在那樣的社會裡,不僅在政治方面不存在王國維所謂“詩歌的正義”,在男女交往中也極少存在詩歌的溫情。
歷史的演進是複雜的過程。一方面,正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肯定“好貨”、“好色”是晚明時代具有進步意義的新思潮,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會力量遠不夠強大、具有正面意義的新道德難以確立的情況下,這種思潮在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西門慶一類人物身上)卻常常會以邪惡的形式表現出來。《金瓶梅詞話》的思想內涵因此也帶有這一歷史變異時期的複雜性。為小說作序的“欣欣子”(許多研究者認為這是作者的另一化名),稱此書的宗旨是“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但這只是一種有意識的和常規性的標榜,小說本身則很少有基於傳統道德的說教;作者一方面揭示了物質欲望和情慾的膨脹使人性趨向於貪婪醜惡,同時也如實地反映出追求這些欲望的滿足乃是人性中不可抑制的力量。金錢和情慾不是被簡單地否定的,而是同時被視為既是邪惡之源,又是快樂與幸福之源。以對於李瓶兒的描寫為例,她先嫁給花子虛,彼此間毫無感情,後來又嫁蔣竹山,仍然得不到滿足,在這一段生活中,她的性格較多地表現為淫邪乃至殘忍;嫁給西門慶後,情慾獲得滿足,又生了兒子,她就更多地表現出女性的溫柔與賢惠來。這明白地顯示出:過度縱慾固然不可取,但對自然欲望的抑制,卻只會造成更為嚴重的人性的惡化。雖然,作者很難以一種恰當的態度來處理這種人性的矛盾,而最終只能以虛無和幻滅來結束他的故事,但至少他對人性的看法,已經不再是簡單化的了。
《金瓶梅詞話》受後人批評最多的,是小說中存在大量的性行為的描寫。這種描寫又很粗鄙,幾乎完全未曾從美感上考慮,所以格外顯得不堪,使小說的藝術價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認為,當時社會中從最高統治階層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談房闈之事為恥,小說中的這種描寫,是當時社會風氣的產物。不過,同時還應該注意到,這和晚明社會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關聯,它是這一思潮的一種粗鄙而庸俗的表現形態。
歷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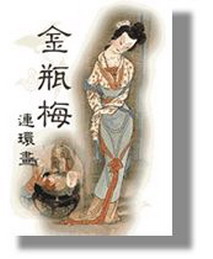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從取材來說,在這以前成就最高的三部長篇小說——
《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分別以歷史上的顯赫人物、民間英雄好漢、神話人物為中心,歸納起來,可以說它們都是寫非凡人物的非凡經歷和非凡故事,是傳奇性的小說。
雖然這些人物故事也反映出一定的社會生活情景,但畢竟是經過了很大程度的想像與改造,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有距離的。《金瓶梅詞話》則是以一個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為中心,並以這個家庭的廣泛社會聯繫來反映社會的各個方面。它的人物是凡瑣的,沒有什麼超常的本領和業績;它的故事也是凡瑣的,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它表現了小說創作對於人的真實平常的生活狀態的深入關注與考察,從而成為我國古代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小說,或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的“世情書”。
凡是優秀的小說,都必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一定成就。但儘管如此,傳奇性的小說放在首位的還是故事情節,即使以前小說中最以寫人物擅長的《水滸傳》,也首先是以故事情節吸引人,很少能看到僅僅為了顯示人物性格而對情節發展並無多大意義的事件。而在《金瓶梅詞話》中,則明顯地出現了故事情節的淡化。它所描繪的大量的生活瑣事,對於情節的發展並無意義,卻能充分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如第八回潘金蓮因等西門慶不來,便拿迎兒出氣,打了她幾十馬鞭不夠,又在她臉上掐了兩道血口子才罷休,這和以後的故事發展毫無關係,卻有力地揭示了潘金蓮那種帶有虐待狂傾向的殘忍性格。此外如五十四回寫西門慶與應伯爵等游郊園,五十七回寫道長募緣、西門慶施銀等等,此類“閒筆”甚多。可以說,《金瓶梅詞話》與以前的小說相比,已經把重心從故事情節轉移到人物形象上來,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過去從民間“說話”中發展起來的通俗小說,為了使文化水平不高的聽眾、讀者容易把握人物,其人物性格一般是單純而鮮明的,壞人一切都壞,好人縱有缺點(如《水滸傳》中李逵、魯智深那樣),也無損於其基本的品質。但這樣的人物雖然容易被接受,相對於複雜的實際生活來說卻是簡單化了。《金瓶梅詞話》寫人物,就不再是這樣簡單的處理。
前面我們說到,這部小說中幾乎不存在通常意義上的“正面人物”,但同樣這部小說中也幾乎不存在通常意義上的“反面人物”。如小說中寫李瓶兒,既有潑辣、兇狠,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不顧一切的一面,但在更多的場合下,她表現出善良、懦弱和富於同情心一面,她的性格是極為豐富的。又如奴才來旺的妻子宋惠蓮,是一個俏麗、輕浮、淺薄的女人,她勾搭上了西門慶,便得意忘形,一心想擺脫丈夫,在西門慶家爬上個小老婆的位子。但當來旺被西門慶陷害時,她卻悲憤異常,“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念著他們在貧賤生活中所建立起來的真誠感情。她痛罵西門慶:“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西門慶百般勸誘,她再也不肯就範,最後終於自殺(第二十六回)。她確實是貪圖錢財和虛榮、品格卑賤的人,但在這後面,卻又保存著某種人性中的高貴的東西。
這樣的人物形象,是過去的小說中所沒有的。就是西門慶,固然是個惡人,但他的“惡”也不是以簡單的符號化的形式表現出來。他的慷慨豪爽、“救人貧難”,多少表現出市民階層所重視的品德。他對婦女從來就是貪得無厭地占有和玩弄,但當李瓶兒病死時,他也確實表現了真誠的悲痛。小說對這一事件的描寫十分細緻。一方面,西門慶不顧潘道士提出的“恐禍將及身”的警告,堅持要守在垂危的李瓶兒的身旁,當她死後,不顧一切地抱著她的屍體哭叫:“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於世了,平白活著做什麼!”另一方面,作者又借西門慶心腹玳安之口指出:“為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人,是疼錢。”但這裡並不是說西門慶的感情是虛假的,而是說這種感情與李瓶兒嫁他時帶來了大量的錢財有極大關係,貪財是他的感情的重要基礎。而這種真誠的一時衝動的感情,卻又不能改變西門慶好色的無恥本性,小說接著又寫他為李瓶兒伴靈還不到“三夜兩夜”,就在靈床的對面姦污了奶子如意兒(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回)。西門慶的形象就是在這樣豐富的性格層次中塑出來的,所以能夠給人以活生生的感覺。
而且,《金瓶梅詞話》描寫人物性格,不是把它當作一種單純的個人天性來看待,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環境、生活經歷聯繫起來。譬如潘金蓮,可以說是小說中最富於邪惡品格的女人,同西門慶真可謂天生一對。但仔細讀小說,我們就會發現,她的邪惡是在她的悲慘的命運中滋長起來的。潘金蓮出生在一個窮裁縫的家庭,九歲就被賣到王招宣府中學彈唱,學得“做張做勢,喬模喬樣”;後來又被轉賣給張大戶,年方十八就被那老頭兒收用了;再後來她又被迫嫁給“人物猥獧”的武大。她美貌出眾,聰明伶俐,卻從來沒有機會在正常的環境中爭取自己做人的權利。來到西門慶家中,她既不像吳月娘那樣有一個尊貴的主婦身份,也不像李瓶兒、孟玉樓那樣有錢,可以買得他人的歡心,但她又不甘於被人輕視,便只能憑藉自己的美貌與機靈,用盡一切手段來占取主人西門慶的寵愛,以此同其他人抗衡。她的心理是因受壓抑而變態的,她用邪惡的手段來奪取幸福與享樂,又在這邪惡中毀滅了自己。
《金瓶梅詞話》的語言一向為人們所稱道。雖然有些地方顯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詩、詞、曲時,往往與人物的身份、教養不符,但總體上說是非常有生氣的。作者十分善於摹寫人物的鮮活的口吻、語氣,以及人物的神態、動作,從中表現出人物的心理與個性,以具有強烈的直觀性的場景呈現在讀者面前。魯迅稱讚說:“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中國小說史略》)如第四十九回寫西門慶宴請蔡御史,請他關照生意,之後留他宿夜,來至翡翠軒:
只見兩個唱的盛妝打扮,立於階下,向前花枝招颭嗑頭。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厚愛,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游,又何別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於是月下與二妓攜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要留題。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
風雅的形態與卑俗的心理交結在一起。作者不露聲色,就寫盡了兩面。這種文筆,後來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極大的發展。
《金瓶梅詞話》以其對社會現實的冷靜而深刻的揭露,對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點)清醒而深入的描繪,以其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現人性之困境的視角,以其塑造生動而複雜的人物形象的藝術力量,把注重傳奇性的中國古典小說引入到注重寫實性的新境界,為之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儒林外史》、《紅樓夢》就是沿著這一方向繼續發展的。《石頭記》的脂評說《石頭記》(即《紅樓夢》)“深得《金瓶》壺奧”,不為無見。所以說,《金瓶梅詞話》儘管有種種不足,它在小說史上的地位,實不可低估。
《金瓶梅》傳世既廣,隨之也出現了一些續書。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稱,有一種叫《玉嬌李》的,“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今已不存。另有清初丁耀亢撰《續金瓶梅》等,俱不見佳。
版本及出版
萬曆本《金瓶梅詞話》在國內多年無聞,至1932年方在山西介休發現一部,收購者“文友堂”書鋪奇貨可居,幾流入日本,終在社會輿論干預下由北京圖書館購藏。當時為償購書款,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單色縮小影印120部。此本全書幾近完整,僅第52回缺失兩葉,影印時以崇禎本鈔補,同時加入崇禎本的100幅插圖一併付印。此後。1955年北京以“文學古籍刊行社”名義,用32年影印本(原本在抗戰時暫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當時尚未歸還),翻印一次,內部發行,製作時,對底本略有挖改。1963年,日本清查全國所存《金瓶梅詞話》,得殘本3種,以其中保存較多的日光輪王寺慈眼堂藏本和德山毛利家棲息堂藏本配合影印,由大安株式會社(大安公司)出版,大安本號稱完整無缺(見[日]長澤規矩也《序》),經梅節等學者研究,慈眼堂藏本與棲息堂藏本相配尚有殘缺,大安株式會社影印時“盜用”32年本第94回兩個單面頁補充完整。此大安本在台灣又有翻印。1978年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以朱墨二色套印成歷丁巳本《金瓶梅詞話》,還原原尺寸大小,所缺第52回兩葉用日本大安本配補。但聯經並非直接據當時已歸還並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古佚小說刊行會”本的底本照像分色製版,而是用傅斯年藏“古佚小說刊行會”本放大成原本尺寸複印兩份,一作原文,一據故宮藏原本描抄朱墨評改,“整理後影印”。所以出現正文虛浮湮漶,朱文移位、變形、錯寫的現象,實為美中不足。1980年大陸重印55年本,,續有“加工”,去真愈遠。1982年香港中華書局以“太平書局”名義據55年印本印行,此“太平本”行銷海內外並被大量盜印。199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32年本,並據大安本補足底本所缺第52回的兩葉。另外,台灣增你智出版社等有排印全本,香港學者梅節窮多年之力,校理成定本在香港、台灣以《夢梅館校本金瓶梅》。大陸則有齊魯書社特批印製內部發行一批排印全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