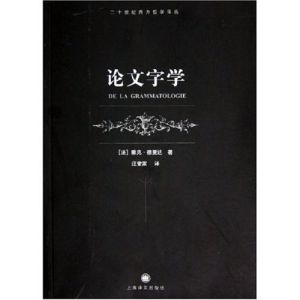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論文字學》作者雅克·德希達(1930-2004)是二十世紀法國著名哲學家和文藝理論家初版於1967年的《論文字學》是他的成名作之一。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從解構主義的基本精神出發著重追溯了文字概念的歷史、深入剖析了以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言語中心主義為特徵的西方形上學傳統。第二部分通過對萊維-史特勞斯和盧梭的著作的解讀,展示了一種新的閱讀風格和閱讀策略,揭示了文字的替補特徵以及它對人類社會組織、情感世界、文化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的深刻影響。相關書評
在90年代以來的漢語學術思想界,德希達是一個得到極多引用和極少研究的人物。他的一些獨特論點和術語似乎已經成了哲學、文論乃至文化研究領域中的老生常談。與之構成鮮明對照的是,他的幾部公認的重要著作卻遲遲未見漢譯。直到1999年下半年,《語音與現象》和《論文字學》的簡體字版才由京滬兩地分別出版,幸而避免了把遺憾帶入新世紀。一般認為,德希達在1967年同時出版的三部著作(《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以及《語音與現象》)是為他贏得聲譽的重要著作,也是理解德希達思想的鑰匙。這幾本書都有“二手著作”的外表,因為直接地看,它們無非是一些對其它作者的評論。這個特徵實際上貫穿在德希達的所有著述中。要理解德希達,也許首先必須理解這個寫作特徵。德希達曾經自陳說:“越過哲學不在於翻過哲學這一頁,而在於用某種特定的方式來不斷解讀哲學家”(《書寫與差異》)。這話讓我們想起晚年海德格爾所說“我一生的工作就是解釋西方哲學史”。對這兩句話及其間的關聯決不能做表面的理解。此間的關鍵首先在於兩者對哲學的態度,其次在於越過哲學的方式。海德格爾明確宣告了“哲學的終結”(可以參見《哲學的終結與思想的任務》一文),與馬克思和尼采的類似斷言有所不同的是,海德格爾對哲學特質的洞察是探本究源式的,也就是說,他是從“開端”來思慮那個“終結”的。對於海德格爾來說,終結就是回到“第一開端”,揭示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被哲學遮蔽的東西,敞開在哲學之外思想的可能性。思想就是澄明、去蔽、道說、敞開“林中空地”,就是對源於哲學的“存在”一詞“打叉”。打叉這種比較極端的做法在作為現象學家的前期海德格爾那裡就已經可以發現徵兆了。海德格爾為現象學方法制定了三個環節:還原(Reduktion)、構成(Konstruktion)和解構(Detruktion)(參見海德格爾〈現象學基本問題〉第五節)前兩者胡塞爾述之甚詳,而“解構”則是海德格爾的獨特提法。據說,對存在及其結構的還原性構成也是一種解構,即對流傳下來的諸哲學概念進行拆毀(Abbau)。後期的去蔽、打叉無非是把拆毀範圍擴大到了“哲學一般”而已。
一篇與德希達有關的簡評從談論海德格爾開始,這決非不必要的。因為德希達的思想淵源固然龐雜,就其大體而言,走的仍然是尼采----海德格爾的哲學終結之路。他的若干基本說法是接著、甚至對著海德格爾說的,而其後則貫穿著更加徹底的尼采精神(與一般的法國哲學家一樣,德希達也認為尼采較海氏更為徹底)。與海德格爾相比,德希達對西方哲學的判定和“超出”更多地從語文問題入手(其實這一點尼采也早已提示在先,可參見〈偶像的黃昏〉中談論語法的地方)。西方哲學的特質植根在西方語言之中。因此對哲學的解構成(deconstruction——這個詞是針對現象學的構成概念的,與“結構”沒有直接的字面關聯,因此最好譯作解構成)活動實即一種語言遊戲。與維根斯坦---奧斯汀的語用學路向的語言遊戲不同的是(可參看德希達在〈哲學的邊緣〉之〈署名、事件、語境〉一文中對奧斯汀的討論),德希達對對話並無太大興趣,而是熱衷於對文本下手,這種工作看起來口子小,實則破壞面大,因為它(至少按照德希達的用意)乃是對語言本身的解構成。可以說,德希達畢生的工作都是在“語言的邊緣”對各種文本從事解構成活動。當然,在這些具體的解讀活動之前,德希達必須解決兩個關鍵的問題:第一,為什麼要從語言入手進行解構成;語言究竟是什麼,有如許重大的地位?第二,作為一種語言遊戲(或不如稱作對語言的遊戲),解構成有哪些“遊戲規則”呢?這是兩個提綱挈領的問題,必須由提綱挈領的“論著”來回答。可以說,《論文字學》及其同期著作(尤其是《語音與現象》)就占據著這樣的地位。
這部《論文字學》由兩大部分構成。第一部分“字母產生之前的文字”分為三章:書本的終結與文字的開端”;語言學與文字學;論作為實證科學的文字學。第二部分“自然、文化”用三章的篇幅解讀了盧梭以及萊維-史特勞斯關於文字起源的著作。用德希達自己的話說,第一部分“簡要勾畫了一種理論淵源。它指出了某些重大歷史事件,提出了若干關鍵概念”(《論文字學》中文本,第1頁,下引該書只注頁碼)而第二部分則對這些概念提出了審查,並“試圖提出一些批判性解讀的問題”(同上)。也許,對我們上文提出的兩個關鍵概念而言,第一部分更為重要一些。但無論如何,這部著作的首要論題是文字。可以說,文字這個論題就貫穿了上述那些關鍵問題:即,語言是什麼、為什麼要對語言進行並且如何進行“解構成”?
眾所周知,這是一個“語言轉向”(linguisticturn,或譯為“語言學轉向”,不妥)之後的時代。問題是,雖然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都會贊同這個提法,它們所理解的“語言”及其地位卻不是一回事。大體地說,英美哲學的語言轉向主要依賴符號邏輯;德法國家的語言轉向則基本依賴解釋學與符號學。它們對語言及其地位的看法與這三種學問息息相關。事情的複雜主要在於德法哲學之間的特殊關係。在法國,源於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實際上擁有一種現象學克服者的姿態。而“從現象學過渡到結構主義,主要圍繞著語言問題”(福柯的訪談:《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也就是說,現象學主體被認為不能作為賦義者參與例如語言結構這樣的東西(參見同上)。然而在德國,現象學與作為語言哲學的解釋學、與“通向語言之路”的海德格爾之思卻並沒有這樣截然對立的關係。這樣,作為法國哲學家和現象學第二代研究者(如果我們把薩特、梅洛-龐蒂、勒維納斯看成第一代的話)的德希達必定要檢查胡塞爾現象學、海德格爾現象學存在論中的語言問題;而他對語言問題的回答,必定以符號學為主要依據。在《語音與現象》以及《幾何學起源》的譯序中,德希達集中討論了胡塞爾現象學中的語言(更確切地是說,指號)問題。但是,與福柯有所不同的是,德希達並沒有孤立地看待語言與意識(賦義行為)的關係,而是將它置於語言與存在這樣一個更大的關係下加以考察的。他對語言所持的獨特批判立場,正基於此。
意識也是一種存在者(關於這種存在者與此在的關係,可以參看海德格爾《四個討論班》,1973年9月7日的討論紀要)。按照胡塞爾的說法,如果意識在場(praesent),那么這也就意味著,其對象“意向地當前呈現(intentionalgegenwaertig)”(參看胡塞爾《第五項邏輯研究》第11節)(注意在英語文獻中,這裡的在場與當前呈現往往不加分別地譯為present,在場)。按照海德格爾的看法,胡塞爾現象學面對的實事自身(Sacheselbst)就是意識(確切的說法是作為世界構成者的意識之主觀性——參看海德格爾《哲學的終結與思的任務》)。在象胡塞爾那樣描述意識結構之前,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研究意識的存在方式。“關於這個構造者本身的存在方式自身的問題的提出是不可避免的”(參看海德格爾1927年10月22日致胡塞爾的信)對這種存在方式追問下去就會達到“存在於世界之中”這樣一種自身超越的“綻開”式存在,而這種存在方式的最終根基就是時間性。與海德格爾的路子相通,德希達也在與內時間意識的關聯中考察意識本身的存在方式(實際上胡塞爾本人早已提示過,意識仍然是在內時間意識這一“最終的和真正的絕對”中被構成的——參看胡塞爾《觀念1》第81節)。這樣,意識的存在方式就是作為時間性東西的“持續”。事情的自身性就在於持續者作為自身同一體的當下呈現、在場。然而胡塞爾本人的分析表明,當下在場者的構成需要對剛才消逝掉的瞬間的持留記憶(Rention)。這就是說,在場者實際上是以對已然缺席者的“使當前化”(vergegenwaertigung)為根據的。而在德希達看來,在場化實際上是符號的功能。“語言是在場與不在場這個遊戲的中介”(《語音與現象。導言》);“。。。。。。意識的成分和語言的因素會越來越難於分辨。那么,它們的不可分辨性難道沒有把非在場和區別。。。引導至自身意識的核心之中嗎?這個困難要求得到一種答案。這個答案就叫語音。。。作為意識的在場的特權只能。。。特別通過語音被建立”(同上)。這也就是說,對現象、“實事自身”起構建作用的,不是別的,正是作為能指的語音。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存在者之存在還是作為在場性的存在一般,都是“先驗所指”。
德希達認為,支配整個西方哲學的在場形上學及其中包涵的一系列二元對立(感性/理性、自然/精神、肉體/靈魂等等),全都源於符號的能所指結構。在表音文字那裡,語音的瞬間消逝提示了所指的在場。在場形上學中包涵的諸二元對立不是平等的,在場、理性、精神、靈魂一向壓抑著變易、感性、自然、靈魂。而這些二元分立及其中的壓抑都是表音文字中的能所指分立的派生結果。邏各斯中心主義就是表音文字的形上學,在場形上學的根源就是西方語言。於是,哲學終結的任務必然表現為批判以語音為中心的西方語言,提示在西語之外、在非表音文字之中思想的可能。在《論文字學》中,德希達對語言與文字關係的探討,對文字的本源地位的揭示,實際上就意味著對哲學(或在場形上學)與另一種思想形態的關係的探討,對那種非表音語言的“文字式思想”的本源地位的探討。當然,非表音文字及其相應思想形態的最合適例子是漢字與漢語思想。作為以漢語為母語的讀者,我們對德希達此書的意蘊應當有更深沉的體會。
在語言學以及一般的語言論看來,語言的本質存在於語音與意義之間的指示關係。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揭示的符號之能所指結構正是圍繞著這種語音中心主義建構起來的。聲音本身總是稍縱即逝的,但作為語音的聲音必然具有一種觀念同一性(例如我們可以兩次發two這個音,但發的是同一個語音),也就是無限可重複性。但語音的同一性實際上只能建立在其所指意義的同一性上,而非聲音本身的相似性上(例如我們不會認為two與漢語的“吐”是同一個語音,雖然它們的物理聲音一致)。胡塞爾現象學認為,把單純的聲音“立義”(auffassen)為語音的是相關的“賦義體驗”亦即意識。但意識其實也就是“意義的(意向式)在場”的另一種說法(參見上引《第五研究》之語)。並且意識本身作為一種時間性存在者,自己也有一個同一性問題。因此,對於同一個例子,德希達按照符號學的路子解釋說,是並且只是所指才從流逝中挽救了語音的同一性。在場就是對所有流逝的克服。反過來說也一樣,那種圍繞語音組建起來的語言必定是以所指之在場為中心的。“所指的形式本質乃是在場,它靠近作為語音的邏各斯的特權乃是在場的特權”(24頁)語音中心主義與在場形上學的息息相關,正基於此。所指對能指的主宰地位,亦出於此。所指、在場是逾時間的,聲音是物質性的,隨時間流逝的。因此超感性世界的優越性實際上也植根於表音文字的本源的能所指關係。
聲音固然是一去不復返,必須由在場將之拯救為語音的。現在的問題是,文字是什麼?西方語言學及其一般的語言起源論一致認為,文字,作為對語音的記錄,只不過是語言的“補充”(supplement,漢譯《論文字學》作“替補”)。但這是一種足以威脅到語音中心主義及其背後的在場形上學的“危險的補充”(參見204頁以下)。既然存在著象漢字之類顯然與“語音記錄”無關的文字,那么,文字是否有獨立的起源?這種起源對能所指的符號學關係,乃至語音中心主義與在場形上學有著什麼樣的顛覆作用?此間,與其說德希達的主題是文字的起源,還不如說,他更感興趣的是,揭示西方語言學如何不成功地抹殺文字的獨立起源;特別是,這種抹殺對在場形上學的維護作用。“文字是什麼”這樣一個銳利的問題,實際上是刺在整個西方哲學的阿刻琉斯腳踵上的。而德希達的這種工作,其實是在不拒絕符號學、語言學、現象學的基本概念的同時(參看18頁),為在它們內部發動“以必要的暴力反對不必要的暴力”(24頁)的解構成革命做先導。因此,《論文字學》只是一種後符號學、後語言學以及後現象學,而其後的若干文本實驗(如《撒播》、《喪鐘》等),才是這裡預言的“必要的暴力”本身。
既然西方哲學的主旨其實是由能所指關係確定的,那么揭示文字對這一關係的顛覆作用,便是至關緊要的。文字是什麼?一種銘刻、印記和跡象;一種頑強地拒絕消逝的能指;一種對所指的開啟和遮擋。文字首先是穩固地維持在自身中的感性事物,它並不直接顯示自身之外的、超感性的東西。也就是說,在文字那裡,所指的在場是懸而未決的。如果說,語音以其短暫易逝立刻超越了自己,必定(也就是先驗地)敞開、指示著一個所指(意義世界、精神世界或者在場性本身-存在一般)的話,那么文字則是純粹的能指鏈。文字固執地存在著,提示著它是一種無法消除的、與所指不同的東西。在對語音的“聽”這種理解方式中,意義立刻當下被把握到,“我們的興趣並不生活在[對語音能指的]知覺中,。。。因而,此間起主導作用的行動性應當屬於賦義行為”(胡塞爾《第五研究》第19節)語音的被遺忘意味著意義的在場。“聽”就是這種“遺忘能指-讓所指在場”本身。但在“看”中,由於文字並不是轉瞬即逝的,它的存在的固執性將不斷推遲意義的出場。這樣,文字提示了一種不可能被超感性世界“同一化”的“差別”;並且它不斷地延宕著那個世界的出場。於是,文字就是一種“分延”(ladifferance)。這是德希達生造的詞,與差異(ladifference)的讀音完全一樣,兼有“差別”、“延宕”的意思。“分延”正是德希達一切立論的關鍵。德希達正是憑藉它“接著”海德格爾說的。“與我們所說的分延相比,存在者與存在同樣是派生的。。。分延才是更‘本源’的東西,但我們再不能將它稱為‘本源’或‘根據’因為這些概念。。。屬於抹去差別的系統”(31頁)
作為文字的不可還原的特性,“分延”將徹底顛覆整個形上學的歷史。形上學就是對在場性的指向。無論這個在場性被稱作“本源”、“根據”,還是“實事本身”、“存在一般”,它總是對差異的抹消。那些抹消方式相應地就是:“思辨”(揚棄感性外在性,回到精神中的辨證運動)、“現象學還原”(懸置差異,將現象學的在場性作為“剩餘”顯露出來)、或通過揭示存在論差異以“指引”(anzeigen,關於formaleAnzeige,參見海德格爾《全集》第60卷)“存在一般”(也就是所謂“無化”——參見筆者對《無之無化》的評論,本刊第三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抹消”當然不是無視差異,而是將其實居於“本源”地位的差異重新吸收到所指的在場性之中。因此,解構成就是對差異的本源地位的恢復,對其不可還原性的指認。在這個意義上,“分延”的提出是而且必然是後辯證法、後現象學、後存在論以及後符號學。解構成既是恢復也是超越。回到“分延”也就意味著對西方哲學或毋寧說哲學本身賴以成立的能所指結構打叉(而不象海德格爾那樣只對能指打叉,因為這樣的打叉只是再一次確證了所指的優越、再一次犧牲了能指的差異而已)。然而這個打叉是通過作為能指之鏈的文本自身在閱讀中的流動(也就是說,意義不斷地逃逸掉了)來實行的。因此,解構成主義必定是對各種文本的終極意義的阻止和延宕,它必定是“後……”。
對於漢語思想來說,漢譯《論文字學》的出版,也正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情。這不單是因為這本譯者用力多年的上乘譯作是對原作的一個不可替換的“補充”(按照德希達,“補充”恰恰是一種本源的反本源性),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本身與漢語思想之間存在著極其重要的互涉關係。在某一個方向上,《論文字學》就是為漢語思想之類的後語言的“文字思想”而存在的。它對於漢語思想自覺為西方哲學的他者,恢復漢語思想的世界歷史意義,具有目前尚難以充分估計的作用。未來籌劃現在。也許,後世的思想家會意識到,這個譯本原來是通向漢語思想之路的第一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