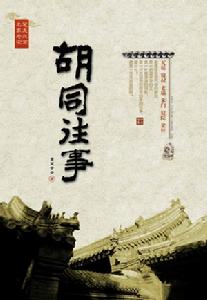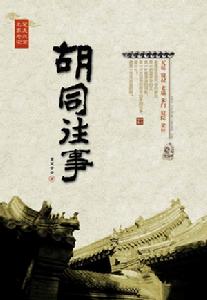 《胡同往事》
《胡同往事》概述
作 者: 董夏青青 出 版:萬卷出版公司
作為北京街巷概稱與代表的胡同,不僅構成了北京城的交通網路,關係到北京的城市格局,而且是北京的城市格局,而且是北京城市生活的依託,北京居民生息活動的場所,並從而成為北京歷史文化發展演化的重要舞台。時代變遷,政局嬗替,世事滄桑,人情冷暖,風風雨雨,恩恩怨怨,幾多生死,幾多悲歡……既在這個舞台上不停頓地上演,又在這個舞台上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印記。
作者簡介
董夏青青,女,1987年1月生於北京,現就讀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97年舉辦個人書法展,200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校園風鈴》2002年12月獲“紀念沈從文涎辰100周年” 鳳凰古城徵文大賽一等獎,黃永玉先生為其頒獎。先後在《當代》、《芙蓉》、《創作》、《青年文學》、《三湘都市報》等多家報刊發表20多萬字的作品。新華網、人民日報、湖南日報、中國青年報、湖南衛視、三湘都市報、中學生等多家媒體對其進行過報導。
內容欣賞
第一章 失明的窗欞
南北走向的豐盛胡同,是以明代一位叫"豐盛"的公主命名的,老舍的房子在這條胡同的路西,進了胡同的第一個門就是。這條胡同的南口直通奶子府大街,北口通向東廠胡同,離王府井商業街和隆福寺都很近。在老捨去世前,北京有兩個豐盛胡同,另一個在西城,胡同和名氣都比老舍住的這一條大。很多郵遞員都理直氣壯地認為名氣大的人,也應該住名氣大的胡同,於是,給老舍的信就經常被錯投到了那裡。老捨去世後,他住過的豐盛胡同改名為豐富胡同。
第一章 失明的窗欞
齊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鋪展
一
站在齊白石居住了31年,直到他生命最後的小屋門口,可以看見四周已經擠滿了巨大、僵直、硬挺的高樓,開著玻璃窗,袒露著明晃晃的心臟。它們輕聲地湊著靠近過來,像黑夜的狼群一樣伺盯著眼下這幾間破敗的老屋。
門上寫著的"謝絕參觀",把我擋在了齊白石生前生活場所的視線之外。這個房子是一個並不太大的器皿,裝滿關於他的記憶後就再也裝不下別的東西了,可是奇怪得很,這裡一開始,還盛裝著供成群結隊的人用來潤喉嚨的清水,然而,現在竟倏地在急忙趕來的人面前,變成一個濕嗒嗒的、發黏的土罐子,只裝了無盡的荒涼和為數不多的幾聲孤寂的咳嗽。濃厚的陰影重重地壓在這個小院子的胸口上,於是這小院仿佛是一個正趴在母親膝上酣睡的孩子遇上汽車相撞時,猛然被震動驚醒了。它試圖埋下頭,把眼睛再睜大來看,是不是還沒脫離剛才混混沌沌的夢?然而,它的懷疑已沒有了容身之所。
二
時間像一小叢火,慢慢且細細地煨著歷史的藥罐,直待到歲月的清水完全變成濃黑的中藥湯。
齊白石原名純芝,後改名齊磺,號渭青,字瀕生,別號"白石",是借用故鄉湖南湘潭老家的一個鄉村驛站"白石鋪"的名字而起。
他唯讀過一年書,從15歲起便當起了木匠學徒,但是,齊白石把這項"下等活"做得很有滋味。他經常摹習《芥子園畫譜》,使自己雕花的技術臻於"庖丁解牛"般的境界。
1888年,齊白石先後向一些鄉里名士學畫,並請陳少蕃教他詩文。以至後來,他自我評價:篆刻第一、詩詞第二、書法第三、繪畫第四。
從1864年到1901年,齊白石都沒有離開過故鄉。在故鄉,每天總可以偷聽到一點天地中的事,聞見造物者帶有泥沼氣的智慧,即便回家時,口袋裡也不忘塞上一點輕快、一點煩惱。
這使得齊白石的畫紙像一個奇怪的旋渦,以往舊文人根本不屑的什麼農民幹活用的釘耙、钁頭、竹筐、瓦罐等都統統被卷了進去,鄉間的各種草蟲、青蛙、魚蝦、瓷器以及放牧、打柴等都成為他畫面上的題材,甚至算盤、秤砣、老鼠、蚊子都越過名聲的藩籬,沒入畫中。
因此,他的畫裡不小心就塞滿了田地里綠油油的草樹的清香,混進了孩童們熱鬧的歌謠,以及本分的老農勞作過後歇息時的余慵。他的心是一座寬敞的宅院,任由自然萬物的聲音和光輝進出。
在眼下一些藝術家的新鮮視角中,"尋常"已經是一條在入口處寫著"此路不通"的窄徑,是對藝術家發揮才能的限制。這樣一來,"內容"上的窮途末路,則直接致使更多的人在藝術形式上求新求變,蹊蹺的"主義"、複雜的"理論"成為創作市場上的俏貨。
可是,藝術並非為顯示藝術家過人的才智而生,藝術作品不是為理解力驚人和偏於病態的讀者準備的。藝術家也用不著披肝瀝膽地硬要造出個奇形怪物來。"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該無生機也"(董其昌),藝術是人性靈棲息的居所,齊白石本人97歲的高壽就是生動的說明。
三
在故鄉待了近40年的齊白石,在不惑之年,開始接觸外界的天地河流。八年里,他"五出五歸",遊歷了隴中、嶺南、江浙等地。然而,他的藝術爆發力此時仍凍結在一片混沌當中,頭腦里依稀只是一片家鄉"寄萍堂"模模糊糊的光景。直到家鄉遭遇戰亂,軍隊和土匪競起,齊白石為了養活家庭和躲避災禍,來到了北京,碰上了陳師曾。在一座城市,同一個人偶然的相遇,竟然使得已經57歲的齊白石,終於等來了自己藝術創造力的覺醒和藝術才能的迸發的時刻-"衰年變法"。
好比是偌大的競技場上款款走來一位頭頂蘋果的窈窕、端莊的女子,她就是傳統文化的象徵,頭頂放著的那顆鮮艷的紅蘋果是"求變"。台下走上來中國勇士吳道子,他拉開大弓飽滿如圓月,一箭將蘋果射落在地,女子毫髮未損,吳道子向著沸騰的人群欠身致意:"I'am后羿也"。這時,西班牙遊俠畢卡索也緊跟著上來,將蘋果一箭射穿,得意地說:"I'am羅賓漢。"眼看著,齊木匠竟然也趁人不備,從後台潛到了眾人的視線當中,顫抖著拉開了弓,這一射,極有可能不但射不中蘋果,還把公主的命給了結了,然後以一句哆嗦的:"I, I am sorry"了結,可所幸歷史沒有給他機會去演繹如此荒誕的戲劇情節。
第二章 失憶的瓦礫
歷史上有人曾把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作為這個國家是否太平昌盛的評判標準。作為邵武縣令的袁崇煥,他首先是一個清官,在任上沒有為自己斂財不說,更是身體力行為民做事。據乾隆《邵武府志》記載,袁崇煥"嘗出救火,著靴上牆屋,如履平地"。這個父母官,遇到百姓房子著火,立即穿著官靴上牆爬屋,實在讓人感動。他微服私訪、秉公執法、平反冤獄,史料稱"明決有膽略,盡心民事,冤抑無不伸"。
第三章 失重的樑柱
梁漱溟說自己是個樂天派,什麼事都不必悲觀,對世界"不必悲觀,對前途不必悲觀,既然事實發展要如此,你悲觀有什麼用呢?事實要發展,發展總是好的,我認為發展總是好的"。作為一個哲學家,梁漱溟的一生充滿了矛盾,他討厭哲學,自己卻講了哲學;在學校沒讀過孔子的書,結果講了孔子的哲學;未曾讀過大學,後來教了大學;生於都市,長於都市,一生卻致力於鄉村工作。
第四章 失聰的庭院
1980年,年邁病重的宋慶齡,托隨同尼克森來華訪問的陳香梅,給美齡捎了一封信,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見到小妹。她說,如果美齡來了,覺得住在家裡不方便,可以讓她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宋慶齡的願望沒能實現,在她生命的最後日子裡,讓她難以釋懷的牽掛,就是沒能見到她的弟、妹親人。大海很寬,但總有一條船可以幫人渡過去;天空很大,坐上飛機,很快就能到達,唯有蔣介石先生為宋家姐妹砌的這道政治高牆,讓她們日夜隔牆相望,幾十年都無法邁動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