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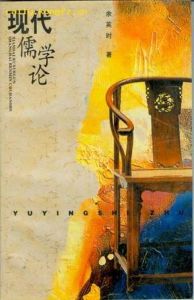
《現代儒學論》收錄了“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現代儒學的困境”、“錢穆與新儒家”、“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等重要的長篇論文,是余英時教授近年在現代儒學研究上的最新成果。
圖書目錄
序
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
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表現
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
“天地君親師”的起源
錢穆與新儒家
現代儒學的困境
群己之間——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兩個循環
儒家思想與日常人生
作者介紹
 余英時
余英時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1987年起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2001年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著作包括《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英文)、《後漢的生死觀》(英文)、《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現代儒學論》等多種。
讀書評論
對關心儒家現代命運的人來說,常常不能不面對以下問題:儒家在現代是一個什麼樣的處境?儒家在21世紀將如何存在?前者是要求對現狀作出一個判斷,後者是要求對未來給出一個預測。預測當然離不開判斷。毋寧說,對儒家現實處境的判斷引導與規定了對儒學未來命運的預測。因此,與其急於對儒家在21世紀的前景問題發表宏論高見,不如先平心靜氣地對儒家的現狀問題作一個學理的考察。在這方面,作為思想史學家的余英時所提出的“遊魂說”,雖然對人不無刺激,但卻是從思想史本身演繹出的一個判斷,值得一思。如果不去過多地推敲用詞、猜度居心,那么,我們不妨這樣來理解:余英時使用“遊魂”這樣的提法,無非是想以一種尖銳的方式凸顯出儒學的現代困境。事實上,這一比喻最初正是出現在余英時那篇題為《現代儒學的困境》的文章里,他的原話是“讓我們用一個不太恭維但毫無惡意的比喻,儒學死亡之後已成為一個遊魂了。”(第233頁)這句話頗堪玩味:在什麼意義上可以宣布“儒學死亡”?這裡的“死亡”是什麼意思,既然死亡,何以又“成為一個遊魂”?在一個唯物論者看來,死亡意味著個體的消滅,即無物存在。這裡既然談到靈魂,顯然就不能作唯物論式的理解,而應當從一種有靈論的立場進入。在有靈論的視域中,肉身之外別有靈魂,靈魂可以獨立於肉身之外而存在,所謂“身雖死而魂不滅”。余英時使用遊魂這樣的比喻,當然是假設了對儒學可以作出類似於靈魂與肉身之分的前提。那么,對儒學而言,何為肉身,又何為靈魂?如果進一步追問,究竟有什麼理由可以對儒學作出如此區分?
按其文義,只是因為引入了“思想/建制”的二重區分,才順理成章地聯想到“靈魂/肉體”這樣的比喻。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發揮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這一點恐怕無人否認。但如果要問:這種影響是如何實現的?對此問題的回答,則標識出不同的致思路徑,也正是在這個地方,余英時的解釋逐漸顯示出其理論的個性。他認為,儒家之所以能發揮這樣巨大而持久的影響,顯然與儒家價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關係,上自朝廷禮樂、國家典章制度,中至學校與一般社會禮俗,下及家庭和個人的行為規範,無不或多或少地體現出儒家的價值。(第241~242頁)當然,這種見解(sight),更早也許可以追溯到陳寅恪,後者認為:“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掂量起來,也許“建制化”一詞比“法典化”可能更容易為現代讀者所理解,而“建制化”所側重者似乎尤在於制度法律方面。
然而,余英時的看法並不僅限於承認儒家有思想與建制之分這一命題。須知,即使是當代一般的儒家辯護者亦不否認此點,甚者,他們恰恰是利用思想與建制的二分為儒家不亡尋找根據。余英時當然不是這樣的儒家辯護者,他與後者分手之處在於:余英時強調,在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對建制有著很強的依賴關係。換言之,如果不是由於建制化的發展,儒家思想在古代便不可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了。因此,討論儒家的現代命運就不能不考察儒家建制這部分。
在書中,余英時向讀者描繪了自辛亥革命以來儒家思想怎樣被迫從各層次的建制中撤退的圖景。這些建制包括國家組織、教育系統以至家族制度等等,其中教育系統尤為關鍵。這是因為,余英時告訴讀者,儒家與有組織的宗教不同,它的思想傳播中心不是教會組織而是各級的公私學校,而中國傳統的教育則又直接與科舉制度連成一體。正是在這個意義,1905年科舉的廢止被看作儒家建制解體的一個最早信號。新式學校,以及隨之而來的儒家基本經典在新式教育中所占的分量越來越少,等等,這些事實正標誌著儒家教育體制在現代的解體。儒家思想與傳統建制分離之後,一直未找到現代的傳播方式。今天,儒學似乎只能在大學講堂和少數學人之間講論。此外,儒家思想(尤其是《大學》所代表的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中,家庭是一個重要的倫理單位,但在現代社會,隨著傳統大家庭的逐漸消失,儒家的孝弟如何安身?凡此種種,大抵也是人們不易否認的事實,這些構成余英時眼中的儒家現代困境。如果把建制比作儒家的肉身,建制的全面解體就好比儒家的肉身已死。如果說儒家思想與建制化是理想與現實的關係,作為現實基礎的建制已經解體,那么作為理想的儒家思想就因無依託而懸在半空,比作“遊魂”,又有何不妥?
在中國當代的思想語境中,恐怕難免會有人把余英時的“遊魂說”與大眾熟悉的唯物史觀相比附。余英時所說的儒家思想與建制的理想/現實關係圖式,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物質/意識一類範疇確乎有幾分形式上的相似。但如果因此把余英時當作唯物史觀的同道,那么對他本人而言恐怕是不敢當的“不虞之譽”了。——事實上,如果全面觀之,余英時的現代儒學論,決不僅僅是宣布儒家思想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已成為“遊魂”這樣一個判斷,毋寧說,作者近年來思考的更多是如何為儒家“招魂”的問題。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余英時的“遊魂說”,並非如某些淺人所想像的那樣是以攻擊儒家為能事。
基於深厚的思想史學識,余英時為儒家現代命運問題提供了一個建設性意見。他的基本看法是:儒學的現代出路在於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避開建制而重新產生精神價值方面的影響力。(第244頁)對明清思想史的重新梳理,使他發現:儒家的日常人生化最遲在明清時代就已開始萌芽。王陽明以來的儒家有一個重要轉變,那就是不再把“道”的實現完全寄托在建制上面,對於皇帝以至朝廷的作用不象宋儒那樣重視,而是專就日常生活處指點,而且遍及於“愚夫愚婦”,也就是轉而注重下面老百姓怎樣能夠在日常人生中各自成聖成賢。具體說來,在《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他側重於儒家如何開拓民間社會這一面,在歷史背景方面,特彆強調明代專制皇權的惡化怎樣促成了儒家的“異化”;而《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一文則更進一層,從社會變動的背景著眼,觀察儒家價值意識和思想的轉向。
以明清以來儒家的轉向為起點,余英時進一步考慮了儒家的價值意識如何在現代社會落實的問題。明清之際乃至近代人,已不相信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有必然的關聯,有鑒於此,在西方近代公私領域之分說啟發下,余英時對儒學定位如下:儒家在修身齊家的層次(私領域)上仍然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對於治國平天下(公領域)而言,儒家只能以“背景文化”的地位投射間接的影響力。這實際上是對當代新儒家所提出的由“內聖”開出“外王”思路的一個超越。或者說,是對“外王”作出了新的解釋,即不必直接參政,通過修身以塑造民主社會需要的“公正的人”(justman)而間接影響政治。當然,這種為政方式,在《論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根據,孔子即表示“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為政》)。
以上思路,粗看似乎“卑之無甚高論”,但對比近年來國內某些學者一往情深構築的所謂“政治儒學”,孰昏孰明、孰高孰下,讀者自可判斷。
不過,嚴格說來,余英時在此主要只是提出了一個構想或一個致思方向,至於如何實現儒家思想的日常生活化,這更多地是需要每個關心儒家現代命運的人都來參與的實踐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