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少數人的上海--富裕階層生活方式探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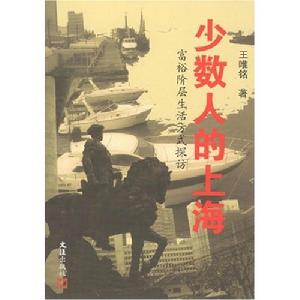 《少數人的上海》
《少數人的上海》作者:王唯銘
出版社:文匯出版社
頁碼:255頁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807413964/9787807413967
條形碼:9787807413967
版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大32
中文:中文
讀者對象:本書適用於文學愛好者。
內容簡介
本書記述了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中的“少數人”的尖鋒生活方式,這些生活方式或許可以從以下兩部分予以解讀:其一,上海中產階級的雅致和前衛生活,以及他們在上海國際化進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特殊而新興的生活氣象;其二,上海絕對少數的富豪們在自己的私密王國中較為奢華的生活行為……“這兩種向度完全不同但都需要非一般物質當量的生活,都是對盤踞在中國上海財富寶塔尖上的那些人們的說明。”作者王唯銘是這樣闡釋擁有這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上海少數人”。
據王唯銘介紹,寫作此書源於三年前的一個偶然,“那是2005年的11月光景,上海文藝出版社剛剛出版了我的《上海七情六慾》,市場反響還算不錯,不少業內人士和普通讀者都強烈地要求我寫一本《上海七情六慾》的續集,集中地記錄一下2005年至今上海擁有頂尖財富的男女,在閒暇時候,他們是如何生活的,又是如何地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於是就有了《少數人的上海》的構思。書中寫到的不少人我與他們有著多年的交往,更多的人我對他們觀察甚久,因此,他們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有著真正的現場質感。”
作者簡介
王唯銘1955年生於上海。上海作家。多年來一直和上海這座城市以及城市裡的時尚打交道的記者、評論家、擎旗者。至今,他已經創作了9本有關城市題材的作品,包括《欲望的城市》《叫喊的城市》《班駁的城市》《女人的城市》《遊戲的城市》《妖媚的城市》《蝴蝶與鸚鵡之腳》和《上海七情六慾》。近日,他將在八月中旬上海書展上推出新書《強呼嘯》,這是一本關於上海百年建築的書,書中涉及的這些歷史建築圖片由王親自一一攝取,堪稱工程浩大。這一系列的作品使得他在上海城市紀實題材領域有著無可辯駁的宗師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城市狩獵者”王唯銘是敏感而性情的,在《上海的七情六慾》一書中,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寫作此書,每每紅酒使他微醺時,他為書中人物的命運而傷感而落淚甚或劇吐。但第二天上午9點,他一定在自己的書房裡坐好了,試圖以外科大夫的敏捷和果斷解剖上海。
目錄信息
第一章 看那一匹匹活蹦亂跳的馬
 《少數人的上海》
《少數人的上海》第一節 馬背上的遊戲和夢想
第二節 上海最年輕的馬主
第三節 馴服"圖朵王"的金領
第四節 絕對"馬痴"馳騁上海灘
第二章 雅舍花園里究竟種了些什麼
第一節 雅舍與豪宅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節 吳建民熱愛的園中手藝
第三節 乾、徐兩先生的花園審美
第四節 "花園讓我盡情抽著板煙"
第五節 這裡,你可以不止養一條狗
第三章 潛水者感覺到的"多重世界"
第一節 水下一米等於水下三十米
第二節 有一種人叫作"潛水瘋子"
第三節 你好,詩巴丹;你好,PALAU島
第四節 "下潛"中的思想者
第四章 去亞洲美容,在世界"溫泉"
第一節 我就想要-個"布蘭妮下巴"
 《少數人的上海》
《少數人的上海》第二節 人生快意在於世界各地洗把溫泉
第五章 高爾夫、VIP金卡與神秘古畫
第一節 "曾經的夢想是破掉90桿"
第二節 虹橋友誼商城中的"拉卡運動"
第三節 董榮亭的"神品"之夢
第六章 奢華超級艇絕對"隱秘"
第一節 "超小型俱樂部"緊閉大門
第二節 那些日子分不清遊艇與快艇
第三節 豪賭黃浦江的男人們
第四節 我與遊艇主僅一紙之隔
第五節 "遊艇生活"猶如海市蜃樓
尾聲 這座城市的生活如此不可思議
後記
作品書摘
第一章 看那一匹匹活蹦亂跳的馬
第一節 馬背上的遊戲和夢想
陳江寧,一個品馬的高手,一個玩馬的老手,一個嘗試將生活與事業都統一在馬這種生物上的好手。
對陳江寧的採訪開始於整整兩年之前。
2006年6月3日下午2點左右。
這是一個多少有些陰沉的日子,天空中沒有出現被媒體所鼓吹的那種無限透明的藍色,重重雲層將一切都暫時地遮蔽住了,氣溫倒因此變得涼快了起來。
經由始終險象環生的A20公路,一陣行馳後,我從上南路匝道口下去,再穿過三林鎮,在新華路小轉彎行馳五六分鐘,便再次來到了新華路517號上海輝煌騎馬場,一種新上海生活的實驗之地。
馬廄在我左側一路排開,那裡總共圈養著95匹馬;它們中有7匹身形矯健的純血馬,有57匹充滿了若干傳奇色彩的伊犁馬,還有10匹將被培養成未來參與運動競爭的馬駒子,以及外形稍微困難了一點但絕對經濟耐用的內蒙馬、東北馬、陝西馬、廣西馬等等等等。那一刻,純血馬、伊犁馬、內蒙馬們正紛紛探出各自的頭顱,它們對“不速
 《少數人的上海》
《少數人的上海》之客”的到來保持著高度的警覺。
右方,是輝煌騎馬場的訓練場,我看見場地中皮膚黝黑的訓馬師正調教著一匹桀驁不馴的純血馬,但見純血馬高高地揚起著前蹄,一聲“咴咴咴”的長鳴,在六月初夏的上海天空下激盪人心地綿延許久。
訓練場後是很大的一塊草地,3匹小馬駒正盡情撒歡,或在草叢中打著滾,或沿著木圍欄作著最初的青春奔跑。
對輝煌騎馬場最好的觀察點是在它的茶樓看台上,站在馬場的這個制高點,你對輝煌騎馬場便能夠一覽無遺。
一條已快完工的馬路將占地100畝的輝煌騎馬場有些“殘忍”地一分為二。馬路那邊,是馬場的一個更大的訓練場。那一刻,兩個男子正策馬狂奔,其中的一個有著很優美的騎姿,身子略微前傾,如同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香港跑馬場里隨著奔馬而上下起伏的騎師;另一個顯然是“馬場菜鳥”,身子不自然地向後仰去,呈現著僵硬、笨拙的狀態,人與馬的運動節奏也明顯錯位……
眼前的草地上,長著種種不知名的野草,開著種種不知名的野花,有幾聲黯然的蛙鳴從草地一頭傳來;仿佛是對其的呼應,我看見~只色彩斑斕的野鳥從草地中戛然而起,它們在空中優美地盤旋著,一聲又一聲的叫喚之聲嘹亮在六月的上海天空下。
那一刻我十分陶醉。
天空儘管還是十分陰沉,但萬籟俱寂,不時響起的蛙鳴和鳥啼更增添了鄉野的寂靜之感,有“鳥鳴山更幽”的那份古雅意境。隨後,初夏的氣息真切地瀰漫在我的身邊。這是我在城市生活中再也無法聞到的氣息,是由馬糞、苜蓿草以及野地上的泥土所混合而成的氣息。那一剎那,它誘引著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浙江紹興錢清新甸的“施家樓”,在三爹的那幢樓房後面.我穿越著那片雅致的竹林,豁然開朗地看見“施家樓”後面的“陳家大”,以及“陳家大”後面的“白馬山”;這氣息也誘引著我想起了俄國(更正確地說是前蘇聯)的那部煌煌巨作《靜靜的頓河》,想起了我的心靈曾經反覆漫遊過的頓河流域,我仿佛看見高爾察克、鄧尼金們率領的哥薩克騎兵正無望地沿著頓河一路而去,馬蹄揚起了漫天塵土,當馬隊在天際處消失的時候,從散落的塵土中浮起的是血紅的殘陽,還有便是頓河流域中濃郁的草原氣息……
難怪上海中產階級的一部分將輝煌騎馬場當成了他們的聖地,難怪他們會穿越半個或整個上海駕車而來,在這裡蹣跚地學著騎馬,進而學著養馬,再進而學著理解“人馬合一”的至高境界。
在這個下午,我通過前幾次採訪已有些熟悉了的許多“騎士們”並沒有出現。
 《少數人的上海》
《少數人的上海》我沒有看見彭煦。這個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的新上海人,這個日益深入著“金領”領地的“白骨精”,那刻也許正帶著他的筆記本電腦飛行在亞歐大陸橋之間。他讓他的純血馬“圖朵王”在馬廄中獨自深切地思念著主人。
在這個下午,我也沒有看見劉薇曄。這個市西中學初三女生有著這樣一份殊榮:上海最年輕的馬主人。我一直難以忘卻這樣的情景:年僅13歲的她,牽著她的“上將”走在馬場水泥地上時,身上洋溢著的那份特別上海的感覺。
在這個下午,我看見了被稱作“馬痴”的兩個上海男人,他們一個叫王力,另一個叫潘勁松。由於對馬的瘋狂迷戀,王力一人養了3匹馬,分別是“英雄”、“美納”和“魔非”;同樣,出於對馬的至高敬意,身高一米八五的潘勁松一度和自己的太太在輝煌騎馬場一人養了一匹馬。在後面的文字中,我將對他倆再作詳盡的描述。
那一刻,我的目光其實已被一人所吸引,他就是陳江寧,上海輝煌騎馬場場主,一個在馬的身上尋找著永遠夢想的男人,也是一個在馬的身上進行著資本運作的男人。
陳江寧沒有穿著他平日最喜歡穿的迷彩軍裝,一直要到很久以後陳江寧才告訴我,他之所以每每穿著迷彩軍裝上班,乃是希望通過著迷彩服這個細節暗示每個員工,馬場如同部隊,是一個組織紀律性要求非常高的地方,來不得半點閃失。那天陳江寧一身騎士裝扮,顯得異常幹練和瀟灑:他戴著一頂鈕扣可以靈活調整的帽子,賽馬時,這種帽子不會遮擋騎士的視線;他上身穿的彩衣相當輕薄,因而便顯得相當輕便,這件彩衣的價格並不昂貴;同樣不昂貴的還有他下體穿著的白色全棉馬褲;他戴的是300元左右一副的手套加200元左右一副的防沙眼鏡,某種意義上,這些東西都很樸素、都很平民。但陳江寧手中的那根馬鞭則要1500元左右,他的軟底馬靴也在1500元上下,他所有的騎士裝束中最具亮點的是那副馬鞍,這副重量半斤不到的CK馬鞍,價格高達15000元。對此陳江寧這樣解釋:一個騎士的行頭上檔次不上檔次,你只要看看他的馬鞍就大致有數了。
一身騎士裝扮的陳江寧在這個下午出現在他精心打造的輝煌騎馬場,遠遠地他向我微笑示意。我確信,那個時候的他並不曾意料到僅僅只過了兩年,馬場最主要的飼料之一的苜蓿草每噸紊從1650元漲到了2200元,內蒙羊草每噸也竟然從800元漲到了1l50元,馬場的開銷再次隨著CPI的不斷提升而提升了;我同樣確信,那個時候的他也不會有這樣的預感,兩年之後,馬主之一的彭旭遠去北京做項目,暫時地離別了馬場,而上海最年輕的馬主劉薇曄與上海最熱狂的馬主潘勁松也因了種種原因,一一離開馬場或許永不再回。
 《少數人的上海》
《少數人的上海》生活總是潮漲潮落,人生總是花開花謝,曾經滄海的陳江寧自然早已做到了處變不驚、瞭然於胸。也因此,膚色黝黑、體格強壯的陳江寧會在2006年6月的這個下午如此從容淡定地向我微笑,因為他知道有關那一匹匹正被上海中產階級寵愛的馬兒的故事。他不僅津津有味地一路聽來,還親力親為地一路說來。
敘述回到七年以前,回到世紀之交的l999年。
剛好四十歲的陳江寧徒步來到了三林鎮薏德村,即今天的輝煌騎馬場的地塊上。
展現在陳江寧眼前的景象只能用“荒涼”、“荒蕪”加以形容。曾經的農場因為經營不善而就此倒閉,留下了一些在風中搖搖欲墜、似乎立刻便要傾覆的房舍,此外便是比成人還要高上許多的遍地野草。陳江寧看見昂子魚在小河中興奮地遊動,看見癩蛤蟆在草叢中生動地蹦跳,看見許多野鳥“嘩喇喇”地從水田中飛起,如此優雅、悠閒地在他的頭頂上盤旋,仿佛在對他行著注目禮。
後來的馬場門衛,即1999年的農場門衛這樣說道:已經記不得有多少人到這裡看過場地了,但看完後全都走了,再也沒有回來,他們認為在這裡做事風險太大了。唯獨陳江寧在這裡拍板成交,一共是100畝土地,66000平方米。他決定在這片土地上辦一個馬場:野趣好啊,馬場就要這份心曠神怡的野趣。後來的馬場門衛當然不可能了解陳江寧熱愛馬的那部歷史。在雜草叢生、野渡無人的三林鎮一邊辦上一個馬場,這之中儘管有著資本運作的強勁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陳江寧自小那份對馬的濃烈感情,這份感情可以讓陳江寧將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放到利潤之上,而這是被老卡爾所定義、所判斷的一般資本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敘述由此再向前推去。
假如說對馬的熱愛可以追溯到遺傳基因的話,那么,父親便是陳江寧後來歷史的最好注釋者。
1943年,陳江寧的父親參加了新四軍,不久便成了首長的警衛員。在戰爭年代,父親喜歡騎馬,而且騎得相當不錯。父親的這種特殊愛好深深地影響了出生在部隊里的陳江寧。
有趣的是,陳江寧第一次騎的不是馬而是一頭驢。他還清晰地記得是在康健園,他騎在一頭“很大、很大”的驢子上,那驢子跑動起來的起伏感,讓他第一次有了一種“騎士體驗”。接著,陳江寧花了兩萬元買了兩匹馬,一匹自己騎著玩,另一匹則在女兒10歲那天做了她的生日禮物。
這時的陳江寧沒有後來的馬場,無論是占地100畝的輝煌騎馬場,還是占地20畝的航頭馬場,他全然沒有。他只能十分尷尬地將兩匹馬放在自己的工廠中,在不算寬敞的廠區中與女兒騎著馬並駕齊驅的那種情景多少讓人忍俊不禁。
但讓人忍俊不禁的陳江寧這時已經有了很多聯想,他意識到馬這種動物的與眾不同,體驗著一個“現代騎士”的種種妙處,一次事件的到來讓陳江寧徹底地與馬為伍,將辦上一個馬場當作自己第二份事業來追求。
那是1997年的某個晚上。
實業家陳江寧從上海市區心急火燎地趕往南匯白玉蘭度假村。周為實在疲憊,在80碼的亞高速中,他一下失控將車子撞向了公路邊上的水泥墩,笨重的水泥墩硬生生地被推開50厘米。當然,陳江寧這裡更是慘不忍睹:整個車頭全療拉掉,自己的肋骨撞掉了轎車方向盤,額頭亦把前檔玻璃撞了個6厘米的大洞。
江寧當時的反應是不可思議的,他只是下車看了一下,隨後竟然在車上睡著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去醫院做了治療,結果全身檢查下來竟然完好無損,撞掉轎車方向盤的肋骨也毫無損傷。沒多久,陳江寧便徹底康復了。車禍沒有帶給他任何的東西既沒有心理上的陰影,也沒有生理上的痛苦。他依然生龍活虎,依然精神抖擻,他將這一切都歸結於自己的“騎士生活”,因為愛馬,因為愛馬上運動,他的身體才會這樣強壯,才會遠離一切疾病,甚至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也對他退避三舍。感謝馬,感謝偉大的自然所創造的這種奇妙生物,他陳江寧能夠加以回報的便是辦上一個馬場。
 《少數人的上海》
《少數人的上海》第一個馬場的地址是在南匯航頭村。
20畝土地上有著16個馬廄,放養著16匹不同種類的馬。陳江寧用他第一桶金中的一部分,具體說來就是200萬人民幣投放在了航頭馬場上。
這時的陳江寧比較今天更為純粹一點,他並不期望馬場會帶來多少利潤,也沒有過多考慮如何收回投資,一句話,他不功利。他想著的是以後終於可以在自己的馬場上用自己的愛馬來招待各路朋友們了,也終於可以在自己的馬場上與自己的愛馬朝夕相處了。而當陳江寧徒步來到三林鎮薏德村,並一下敲定了100畝土地,將輝煌騎馬場置辦起來的時候,坦率地說,陳江寧的想法已從當初的絕對單純變成了而今的相對豐富。他依然強烈地愛著馬,在“慢步”到“伸長與收縮”這十一種騎術中體會著高度的快感。但今天的他,還在馬文化中看到了一種商機,假如他的1000萬投資能夠給他帶來回報,他為什麼不要呢?
絕對單純的陳江寧與相對豐富的陳江寧,在這中間其實還有許多的故事已經發生,還有著許多的人生必須歷練。
譬如,找馬。
先說“二號”馬。
這是1998年3月,陳江寧與他的同伴一起來到了東北與內蒙交界之處,尋找他中意的馬匹。
這個時候,陳江寧已經從在狹窄的廠區里學習騎術的尷尬情狀中解脫而出,他對馬文化的理解也逐漸深入,隨著騎術不斷提高和精進,作為上海最早的“騎士”,他已經可以對馬匹的好壞作出精準的判斷。
好馬的要義是什麼呢?
 《少數人的上海》
《少數人的上海》那便是結構必須勻稱,一匹馬要有足夠的“悍威”。具體來說,就是馬頭要小,馬脖要細,馬前胸要寬,馬腿要修長,馬屁股要飽滿,馬眼上方的凹坑不能太深,馬嘴中的牙齒則不能前沖。最後,國產馬的身高最好不低於1米55,而純血馬的身高則不能低於1米60。
數年如一日對馬文化的反覆浸淫讓陳江寧目光如炬,某日,當他在齊齊哈爾市的大街上看到一匹馬後,兩眼頓然放出電光。
那時,一個東北老漢正駕著馬兒蹣跚而行,老漢的馬兒毛色不太理想,但在老江湖陳江寧眼中,這馬自有它的“完好神態和清奇骨骼”。他當下將馬車攔下,這才發現,這馬的馬蹄上打的不是鐵掌,而是一圈橡皮輪胎,這使得這馬平空高了2厘米左右。這平空的2厘米不免“漿糊”,但陳江寧的如炬目光還是穿透了這馬的潛力,當下,他掏出4800百元交給老漢,拉了馬兒就走。
以後的事實印證了陳江寧的目光。到上海後,此馬被冠以“2號”,它能走會跑,而且沒有其它馬兒的通病,一直到2000年,此馬的腳關節壞掉,方才從“一線部隊”退役下來。此刻,2號依然以教學馬的身份發揮著餘熱。有時,當它在馬廄中低頭沉思,陳江寧會想到,它是否在思念著遙遠的東北老家?
3號馬的尋找頗具驚險性。
3號馬又叫“輝玉”,是汗血馬中的一種。所謂的汗血馬是土庫曼斯坦文化中的一個神話。這種馬在長時間奔跑後,其脊背上會出現類似鮮血一樣的汗水,所謂的汗血馬一說便由此而來。
陳江寧找到“輝玉”的時候正是新疆牧民立刻要“轉羊”的當口。所謂“轉羊”,是封山的另外一種說法。在新疆等地,每當進入冬季,草枯地荒,尋常牧民養不起馬兒,就會將自己圈養的馬匹統統放到深山之中,任由它們自生自滅。通常要到第二年春天,天山的大雪一一化為清澈的溪水,牧民們方才將那些按照達爾文“適者生存”的原則存活下來的馬兒從深山中牽回。陳江寧抵達新疆某地時,剛好封山伊始,為了獲得一匹好馬,陳江寧不惜冒險,央求牧民們去深山套回一匹符合他的審美理想的駿馬。當陳江寧與牧民們出發的時候,他清楚地知道,假如天山大雪提前降臨,那么,等待他的將是深山中的苦熬,而且是長達三四個月的苦熬,他完全有可能一直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方能獲得人身自由。好在一切有驚無險。不過,當牧民將“輝玉”搞到手的時候,陳江寧還有些不滿:怎么個子這么小,這可不符合駿馬的標準。但仔細打量之後,他看出了門道:這馬還是相當的有靈氣。13000元,陳江寧將“輝玉”搞到了手,而“輝玉”也果然沒有讓他失望,在後來的速度賽馬比賽中,“輝玉”連連獲得上好名次,讓陳江寧反覆慶幸、反覆感嘆當年在新疆時自己還算沒有走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