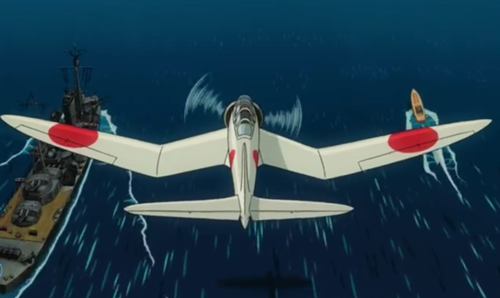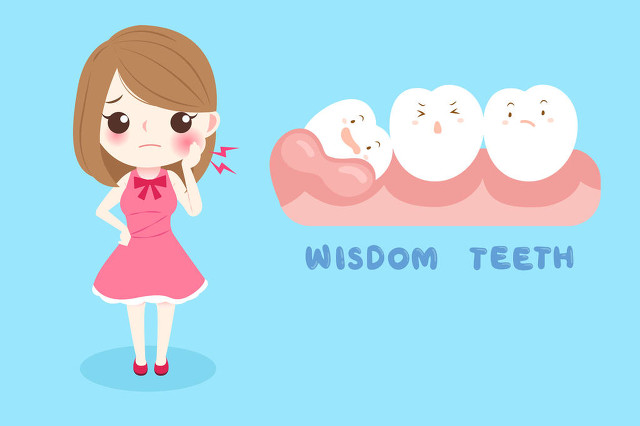2018年12月20日,
寂靜已久的洱海邊突然傳來了挖機的聲音。
“突突突…突突突…”,
挖機所到之處,
房屋加速破碎,體無完膚。
 這一天晚上,大理最早的海景客棧老闆洪嘉明,在朋友圈發了一個拆除客棧的視頻,寫道:“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這一天晚上,大理最早的海景客棧老闆洪嘉明,在朋友圈發了一個拆除客棧的視頻,寫道:“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一天終究還是到來了。
那些逃離北上廣,
辭職、賣房,甚至背債,
只為在洱海邊開一間客棧,
享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人,
在一夜之間,理想幻滅,
不得不面對這樣意外而苦澀的現實——
歷經14個月的苦苦等待,
滿心期待等不來餐館、客棧的重新開業,
卻只等來了一紙拆書。
2017年3月31日,大理市宣布啟動“環湖截污工程”, 洱海“生態紅線區”內的餐飲、客棧全部暫停營業。
 2018年5月30日,大理公布“湖濱緩衝帶生態修復與濕地建設工程”計畫,洱海西部臨湖 15 米內全拆,用於恢復湖濱帶。
2018年5月30日,大理公布“湖濱緩衝帶生態修復與濕地建設工程”計畫,洱海西部臨湖 15 米內全拆,用於恢復湖濱帶。短短不到一個月,
1806家民宅及客棧被拆完。
一邊是網上,那些來不及打卡的遊客在問著:
“都2018年了,大理洱海邊的客棧開了嗎?”
一邊是詩意棲居戛然終止的“新大理人”,
收拾家當,不知從去從何,徒留一句:

 烏托邦,烏有的理想國。“大理烏托邦”,或許早已預示了它消亡的到來。
烏托邦,烏有的理想國。“大理烏托邦”,或許早已預示了它消亡的到來。大理,幾乎是年輕人最愛的打卡聖地。
人人都聽說過“大理烏托邦”的稱號,
卻不是人人都見識過這個“大理想國”。
這方歲月靜好的土壤,
滋養了太多放蕩不羈的自由靈魂。
上個世紀80年代,
大理只有古城,和一個個閉塞的小漁村,
人們乘坐渡船,零零星星往來,
一走就是大半天,漫長枯燥。
這裡曾是走出去的本地人,
不願再回來的地方。
直到第一個外國背包客的到來,
直到古城裡第一家咖啡店的開張,

蒼山洱海、風花雪月,
這是大理的招牌,
更是大理為異鄉人布下的迷魂陣。
緊隨背包客的步伐,
外國詩人、畫家、地下樂隊紛沓而至,
在古城裡打造了一個“嬉皮士王國”。
 1999年,當地人將洋人聚集的護國路改名為洋人街。我們在首圖藏了一個彩蛋,多金的你發現了嗎?
1999年,當地人將洋人聚集的護國路改名為洋人街。我們在首圖藏了一個彩蛋,多金的你發現了嗎?很快,國內先行者們亦蠢蠢欲動,
一路向西來到大理。
他們漫無目的地在古城裡閒逛,
無需遊覽景區,無需導遊帶領,
只是住著,什麼都不想,
全身心感受自由的氣息。
對他們來說,
大理是金庸筆下與世隔絕的武俠,
是《還珠格格》里“一簫一劍走江湖”、
“家家戶戶都有水”的遠方,
更是當下這片純粹的烏托邦之地。
很多人來了、走了,
又來了,又走了。
留下的,多是所謂的文青:
玩音樂的、寫字的、畫畫的,
無一例外,都是愛喝酒的。
 人民路138號,每天傍晚,樂隊在大理四中門口表演。
人民路138號,每天傍晚,樂隊在大理四中門口表演。
每個日子都在重複著:
日上三竿才起身洗漱,
穿過石板街道,尋一家書店,
或穿過羊腸小道,尋一片湖邊草,
安靜地坐著,看書、畫畫,
傍晚回到古城熟悉的酒吧,
跟著樂隊盡情演奏、搖擺。
沒人對明天有計畫,
沒人用“城裡人”的節奏劃分自己的生活。
大理,並非一個非去不可的地方,
只是一旦來過,必定念念不忘。

在外人眼裡,
大理是所謂的詩和遠方,
這種逃避不切實際、不負責任。
但對於決心紮根大理的人,
大理不是桃花源,
而是自己選擇的靈魂故里。

可惜好景不長,
如同國內其他景點的走紅一樣,
聲名日盛的大理烏托邦,
逐漸淹沒在蜂擁而至的人流中。
2013年,資本瞄準了洱海這片“寶藏”,
投資圈錢,餐飲、客棧遍地開花,

 2016年大年初三,雙廊被擠爆了,一房難求,本地人與遊客數量達到3000:80000,無處下榻的遊客跑到居民的堂屋裡,央求給睡一晚上。
2016年大年初三,雙廊被擠爆了,一房難求,本地人與遊客數量達到3000:80000,無處下榻的遊客跑到居民的堂屋裡,央求給睡一晚上。2016年底,大理持續暖冬,
洱海大面積藍藻水華大爆發,
一持續就是5個月之久,
上層不得不採取行動:
停業整頓、全力拆除違章建築。
洱海如此脆弱,
是人為所致,也是天生屬性。
這片斷層湖泊,湖岸狹長,
遺世獨立,沒有大江大河流通,
水源補充幾乎全依賴降水。
源近流短,決定了水體自更新緩慢,
環境一旦超負荷運轉,
洱海原本脆弱的生態就更加敏感。

無論對於世居此地的人,
還是新移民、遊客,
洱海治理是自下而上全民性的共識,
只是落到每人頭上的代價,各有各的沉重。
外來的資本,時機對了,發展上幾年,
政策嚴格下來,抗議一下,拍拍屁股走人。
而世代生活在洱海邊的居民,
默默承受著3年禁漁期的代價,
他們無處可逃,義無反顧地支持:

 大理
大理而對於早期就定居大理的文青而言,
“大理烏托邦”這五個字,
早在資本入駐前,就成了回憶。
後來那些逃亡大理開客棧的人們,
來不及全身而退,更是無路可退。
中國,還會有下一個大理嗎?
下一個烏托邦,又在哪裡?
大理 客棧 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