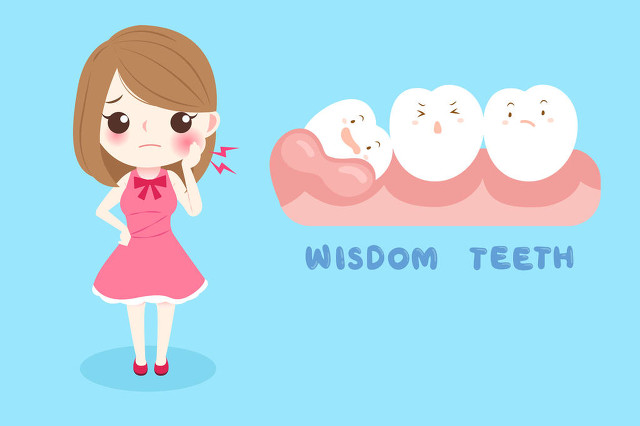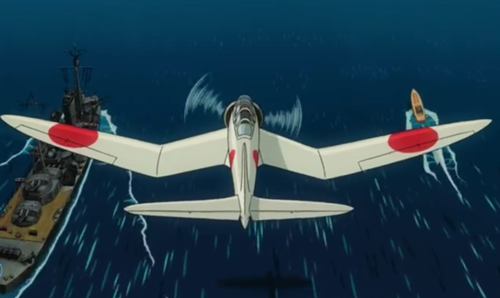中國歷史上有一種畸形審美情趣:男女著裝佩飾以“陰陽顛倒”為美。女子常著男人裝,而男子則“為婦人之飾”,尤其是上層社會的一些名流,過分注重其儀容的修飾與化妝,用面脂、唇膏、簪花等女用化妝品粉頭飾面,一度成為一種時尚。身為男子卻愛化女性妝、佩女性飾。
這種畸形審美情趣,古月清照認為與時下的“偽娘”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各朝各代中此文化無疑以隋唐五代最甚!
從史書上我們不難發現,隋唐五代時期的男子中多“小白臉”。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便是典型的“小白臉”。《舊唐書》上說張氏兄弟是“傅粉施朱,衣錦繡服”,那張昌宗更是被美譽為“人言六郎(張昌宗排行老六)面似桃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男子弄得油頭粉面,扮裝得像一個現代“人妖”,大概跟武則天、太平公主等大唐權貴婦人喜好“小白臉”有很大關係。武則天挑選陪侍美少男的標準就是“潔白美鬚眉”。
既然上層權貴婦人喜歡“小白臉”,朝野上下就競相仿效之,男子做美容、化女妝,裝飾打扮標新立異,日漸成為一大時髦。《新唐書》記載唐朝末年的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矜嚴盛飾”,不僅相貌雄奇、性情嚴謹,還喜歡修飾外表,每當他梳洗時,便命侍者前後置放兩面大鏡子自照。唐懿宗時代的詩人李山甫姿容秀美,頭髮長達五尺余,每次沐浴後便讓二婢女把長發“捧金盤承而梳之”,遇到有客人造訪時,常常會將其誤認作女子。
唐代小說家沈既濟最早借“狐仙”擬人的《任氏傳》一書中,描寫了一個風流才子韋崟,這韋崟打探到朋友新近物色到一位絕色美女(實為狐仙),“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唇而往。”從中可知在當時男子使用唇膏是件很平常的事兒。當然,韋崟之類的風流男子也慣於“傅粉施朱”,打點粉底再抹面脂,在武則天時期的男子中已經流行。
曾任唐朝宰相的路岩善於修飾,曾經成為時尚男子仿效的對象。路岩裹的幞頭(包頭的軟巾)式樣很美,很快就風靡一時。為標新立異,路岩就剪掉了幞頭紗巾的腳。於是知情者在街巷遇見仿效路岩原幞頭四處炫耀的,便會譏笑道:“路侍中(路岩曾任侍中,即宰相)早已不戴這式樣了。”
隋唐五代時期的時尚男子還流行“以香熏衣”。用香熏衣之俗,大抵始於漢代,至唐朝已經十分盛行。《舊唐書》上說曾任太平節度使的柳仲郢“以禮法自矜”,“廄無名馬,衣不薰香”。官吏不“以香熏衣”被史書上作為“以禮法自矜”的例證之一,可見當時男子薰香風氣的盛行。
這一時期的男子還流行戴簪花。簪花本是古代女子將花朵插戴在髮髻或冠帽上的一種裝飾美化,其花或鮮花,或羅帛等所制。在唐代的繪畫作品中有不少婦女戴簪花的形象,如《簪花仕女圖》等。但最晚在唐玄宗時便有男子簪花的記載。玄宗時期的汝陽王小名花奴,他曾為玄宗敲擊羯鼓,玄宗聽得欣喜便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又一次玄宗與曾任中書舍人的唐代文學家蘇頲等郊遊,蘇頲即興作詩,玄宗認為是美文,就將“御花”(玄宗自己頭上所戴)插在蘇頲的頭巾之上。由此可知,當時至少在宮廷中已經流行男子簪花。
男子簪花風俗,還能從這一時期的不少詩作中得到印證。杜牧便有詩曰“塵世難適開笑口,菊花須插滿頭歸。”這菊花是插在男子頭上的。大約自五代起,男子簪花已經開始流行,至五代後期更是蔚然成風,乃至成為官方禮儀制度的一部分。後梁開平年間,有個叫李夢符男子,“潔白美秀如玉人”,四時常插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狂飲,還作詩稱“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後唐人霍定每逢春遊曲江時,即花重金雇員偷采貴族宅院中的名貴蘭花“插帽”。閩主王延羲在遇害的當天,還在頭上插了幾朵花,從宮殿出來時,門帘三次拂落簪花,他“整花上馬”,卻遭侍衛殺害。
隋唐 娘炮 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