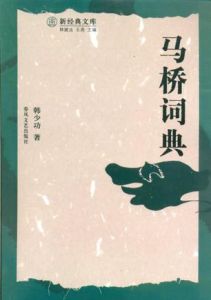《馬橋詞典》集錄了湖南汨羅縣馬橋人日常用詞,
 《馬橋詞典》
《馬橋詞典》基本情況
 《馬橋詞典》
《馬橋詞典》《馬橋詞典》出版後,有人批評該書抄襲了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作者韓少功因此起訴評論者侵犯其名譽權,並獲得勝訴。
作者:韓少功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類別:社會文化
出版時間:2003-12-01
印刷時間:2003-12-01
上書時間:2007-06-23
開本:32
頁數:401
裝訂:平裝
編輯推薦
語言是人的語言,語言學是人學。迄今為止的語言學各種成果,提供了人類認識世界和人生的各種有效工具,推進了人們的文化自覺。但認識遠沒有完結。語言與事實的複雜關係,語言與生命的複雜關係,一次次成為重新困惑人們的時代難題。在這本書里,作者力圖把目光投向詞語後面的人,清理一些詞在實際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能,更願意強調語言與事實存在的密切關係,感受語言中的生命內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較之語言,筆者更重視言語;較之概括義,筆者更重視具體義。這是一種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語言總結,對於公共化的語言整合與規範來說,也許是不可缺少的一種補充。
作品簡介
《馬橋詞典》集錄了湖南汨羅縣馬橋人日常用詞,計115個詞條。
 《馬橋詞典》
《馬橋詞典》《馬橋詞典》是韓少功的一部力作。它內容嚴肅,筆法獨特,不愧為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以詞典的形式蒐集了中國南方一個小村寨里流行的方言。這本詞典從純詞典的形式迅速過渡為一個個故事。其中講述了“文革”時期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知青”的生活的點點滴滴。
故事的大部分素材來源於韓少功的親身經歷,這部佳作捍衛了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時向千篇一律的泛國際化趨勢吹響了反抗的號角。
對韓少功而言,故事稱做詞典本身就是把這個詞的含義延伸了。每個詞的含義得到了充分的注釋,同時他們又作為引子引出詞語背後看似散亂的作者的思緒,這貌似不經意的思緒將一個個詞語連成完整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詞不是按照西方的字母順序排列的。
例如“江”這個詞條後面列出了具體的江名以及江名的由來——不知不覺你就會置身於知青們的故事中:如何與船夫賴賬,如何丟掉他們所窩藏的槍枝。讀了幾頁後,故事中的人物一一呈現,他們的市井生活構成了故事的點點滴滴。
作品分析
《馬橋詞典》這部長篇小說沒有採取傳統的創作手法,而是巧妙地糅合了文化人類學、語言社會學、思想隨筆、經典小說等諸種寫作方式,用詞、典構造了馬橋的文化和歷史,使讀者在享受到小說的巨大魅力的同時,領略到每個詞語和詞條後面的歷史、貧困、奮鬥和文明,看到了中國的“馬橋”、世界的中國。小說主體從歷史走到當代,從精神走到物質,從豐富走到單調,無不向人們揭示出深邃的思想內涵。
 韓少功
韓少功韓少功在《馬橋詞典·編撰者序》中說:“任何特定的人生,總有特定的語言表現。”每一種語言,都反映著特定生存狀態、民俗文化、以至更深層的生存哲學和思想理念。而作家對語言的這種特性和功能有深刻而切身的體會,所以他編成了這樣一部大詞典,用語言的故事講述著社會、生活、文化與哲理。
例如,在“馬疤子(以及1948年)”和“1948年(續)”中馬橋人用“長沙人會戰那年”、“茂公當維持會長那年”、“張家坊竹子開花那年”、“光復在龍家灘發蒙那年”等不同說法來表明公元紀年1948年,反映了馬橋人奇特的時間觀念和歷史觀。也揭示了一種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時間的歧義性”。而“蠻子、羅家蠻”的詞條里,追溯著歷史的淵源;“撞紅”的詞條里,由現存的習俗追溯到人類文明史中原始而野蠻的時代。這裡,語言體現人類追溯家族淵源的主題。
有些詞,更在作家簡潔精要的議論中折射著生存的文化與哲學。如馬橋人用“同鍋兄弟”代替同胞兄弟的說話,相應地,女子出嫁叫“放鍋”前妻稱“前鍋婆娘”,後妻稱“後鍋婆娘”。作家在這裡說:“可以看出,他們對血緣的重視,比不上對鍋的重視,也就是對吃飯的重視。”正所謂“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這正反映了艱難的生存狀態下人們樸實而簡單得令人心酸的生活追求,這種追求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積澱成了一種語言習慣、一種文化、一種思想觀念。這裡包含著一種辛酸,也包含著對這種原始的生存追求的敬意和信仰。
有些詞反映了馬橋人的文化生活,也反映了馬橋人,以至作者的文化觀念。在老百姓艱苦單調的日子中,唱歌、斗歌是他們唯一的娛樂與消遣。而唱男女情事的歌更是對他們人性慾望的一點滿足。萬玉因為唱不慣迎合政策的春耕頌歌而放棄逛縣城的美差、出風頭得榮譽的機會,臨陣逃脫。作者說:“他簡直有藝術殉道者的勁頭。”這裡包含立刻作者對藝術與政治意識形態關係的反思。
馬橋人
馬橋人以獨特的眼光看世界。“神仙府”、“夢婆”、“覺”、“醒”等這些詞正閃現這種慧眼的睿智的光輝。
“神仙府”里的人,風餐露宿,與自然為友,在天地間悠閒自得,在世俗常人的眼光看來,是不思進取、消極頹廢,但在馬橋人以神仙稱他們。這是頗有老莊哲學的風味的。而馬橋人把“科學”一詞定義為懶惰,他們認為城裡人發明一大堆所謂科學的東西代替人類就是因為懶惰。他們拒絕著外面世界現存的知識與觀念,固守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信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樸素的自然主義的生存哲學。
 《馬橋詞典》
《馬橋詞典》“夢婆”一詞給人們避之不及的精神病人一個如此感性而神秘的稱呼,並且認為“夢婆”是最接近真理的人。蘊含了一種敬畏而非鄙視。而作家把“夢婆”與英文的“lunatic”聯繫起來,總結了它們都注意夜晚與精神狀態的聯繫,更揭示了對隱藏在語言中的普遍人性、或者說人類的普遍文化經驗。而對“醒”“覺”的與常人相反的理解,再次印證了馬橋人難得糊塗的哲理——“甦醒是糊塗,睡覺倒是聰明。”世人追求聰明、自作聰明,往往聰明反被聰明誤,而馬橋人相信人在瘋癲與沉睡狀態的智慧,到底誰更明智些呢?
而“貴生、滿生、賤生”的說法,與其說是消極的處世態度,不如說是馬橋人在苦難人生中悟透了佛家至理。那是農民對貧困無望生活的極度厭倦與無奈,在這厭倦與無奈中練就的豁達與灑脫,是對生命的大徹大悟。
馬橋的語言
馬橋的語言反映著馬橋人的生活、歷史、文化思想。但韓少功從語言中看到了中國的馬橋、世界的中國,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從80年代初開始注意方言,這種注意是為了了解我們的文化,了解我們有普遍意義的人性。”
《馬橋詞典》講述的遠遠不是語言的故事,穿透紙背的,是作家對人類文明、對人性的深刻的哲理性思考,以及作家的濃厚的人文關懷精神。
語言覆蓋下的民間世界
韓少功在80年代的文化尋根小說創作中,已經比較自覺地確定了民間的表達立場,但從《爸爸爸》等作品來看,他仍然是用啟蒙的態度來批判民間的藏污納垢性。1996年初,他沉寂多年後發表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在對民間世界的創造性的營造和對小說形式的實驗性開拓兩方面都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
《馬橋詞典》在許多方面都延續了韓少功以往的創作風格,但在小說的敘事文體上卻開創了一種新的小說敘事文體--用詞典的語言來寫小說。“馬橋”是個地理上的名詞,據小說的敘事者介紹,“馬橋”是古代羅國所在地,就在楚國大夫屈原流放和投河的汨羅江旁。
故事以敘事者下鄉當知青的年代為主體,向上追溯到各個歷史時期的生活片段,向下也延伸到改革開放以後,著重講的是70年代馬橋鄉的各色人物與風俗情景。但這些故事的文學性被包容在詞典的敘事形式裡面,作家首先以完整的藝術構思提供了一個“馬橋”王國,將其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傳說、人物等等,以馬橋土語為符號,彙編成一部名副其實的鄉土詞典;然後敘事者才以詞典編撰者與當年插隊知青的身份,對這些詞條作詮釋,引申出一個個文學性的故事。韓少功把作為詞條展開形態的敘事方式推向極致,並且用小說形式固定下來,從而豐富了小說的形態品種,即在通常意義上的“日記體小說”“書信體小說”之外又多了“詞典體小說”。這部小說在語言上的探索更加成功些。
 韓少功
韓少功在以往小說家那裡,語言作為一種工具被用來表達小說的世界,而在《馬橋詞典》里,語言成了小說展示的對象,小說世界被包含在語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說,馬橋活在馬橋話里。韓少功把描述語言和描述對象統一起來,通過開掘長期被公眾語言所遮蔽的民間詞語,來展示同樣被遮蔽的民間生活。儘管他在講解這些詞語時仍不得不藉助某些公眾話語,但小說突出的是馬橋的民間語言,文本里的語詞解釋部分構成了小說最有趣的敘事。
如對“醒”的解釋,在馬橋人看來,醒即糊塗,他們從屈原的悲慘遭遇中看到了“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格言背後所包含的殘酷現實,這與魯迅筆下的“狂人”意象一樣,既是對先驅者的祭奠,又是對國民性的嘲諷,也包含了民間以自己的方式對三閭大夫的同情……所有這些,不是通過人物形象,不是通過抒發感情,甚至也不是通過語言的修辭,它是通過對某個詞所作的歷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學性的解釋而得到的。
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較強的詞條里,它主要的魅力仍然來自構成故事的關鍵字。像“貴生”一詞的解釋里敘述了“雄獅之死”,雄獅本是個極有個性的農民孩子,他誤遭炸彈慘死後,小說重點闡釋了一個民間詞“貴生”的含意,即指男子18歲、女子16歲以前的生活。在農民看來,人在18歲以前的生活是珍貴而幸福的,再往上就要成家立業,越來越苦惱,到了男子36歲女子32歲,就稱“滿生”,意思是活滿、活夠了,再往上就被稱作“賤生”了。所以,鄉親們對雄獅的誤死並不煩惱,他們用“貴生”的相關語言來安慰死者父母,數說了人一旦成年後就如何如何的痛苦,讓人讀之動容的正是這些語詞里透露出來的農民對貧困無望生活的極度厭倦,雄獅之死僅僅成了民間語言的一個註腳。
《馬橋詞典》是對傳統小說文體的一次成功顛覆,而它真正的獨創性,是運用民間方言顛覆了人們的日常語言,從而揭示出一個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們意識到的民間世界。
馬橋的人物故事大致分作三類:一類是政治故事,如馬疤子、鹽早的故事;一類是民間風俗故事,講的是鄉間日常生活,如志煌的故事;還有一類是即使在鄉間世界也找不到正常話語來解釋和講述的,如鐵香、萬玉、方鳴等人的故事。
第一類故事是政治性的,含有歷史的慘痛教訓。如對隨馬疤子起義的土匪的鎮壓、地主的兒子鹽早所過的悲慘生活,都是讓人慾哭無淚的動人篇章,閃爍著作家正義的良知之光。
比較有意思的是第二、三類,馬橋本身是國家權力意識和民間文化形態混合的現實社會縮影,各種意識形態在這裡構成了一個藏污納垢的世界,權力通過話語及對話語的解釋,壓抑了民間世界的生命力,第二類民間風俗故事正反映出被壓抑的民間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拒絕來自社會規範和倫理形態的權力,如志煌的故事,是通過對“寶氣”一民間詞的的解釋來展開的,在其前面有“豺猛子”的詞條,介紹了民間有一種平時蟄伏不動、一旦發作起來卻十分兇猛的魚,暗示了志煌的性格,而“寶氣”作傻子解,這個詞語背後隱藏了民間正道和對權力的不屈反抗,最後又設“三毛”詞條,解釋一頭牛與志煌的情感。通過這一組詞條的詮釋,把極度壓抑下的中國農民的所恨所愛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第三類被遮蔽的民間故事更加有意思,像萬玉、鐵香、馬鳴等人,他們的欲望、悲愴、甚至生活方式,就連鄉間村裡的人們也無法理解,也就是說,在權力制度與民間同構的正常社會秩序里,無法容忍民間世界的真正生命力的自由生長,這些人只能在黑暗的空間表達和生長自己,在正常世界的眼光里他們乖戾無度不可理解,但在屬於他們自己的空間裡,他們同樣活得元氣充沛可歌可泣。這種含義複雜的民間悲劇也許光靠幾個語焉不詳詞條和不完整的詮釋是無法說清楚的,但這些語詞背後的黑暗空間卻給人提供了深邃的想像力。
西方人的評價
韓少功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馬橋詞典》1996年出版,曾榮獲“上海市第四屆中、長篇小說優秀大獎”中的長篇小說一等獎。2003年8月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西方人對它格外看好,紛紛撰文對它進行高度評價,儘管各自的看法不一。
羅傑·蓋茨曼(RogerGathman)(德克薩斯州的一名作家)在該書出版時給《舊金山之窗》撰文評論說:如果不熟悉中國文學的讀者單看前15頁就可能看不下去,韓少功在作品開始時給人一種該書是部專題論著的印象。然而,故事不久就開始了,其中裡面有四個人的故事是不朽的:一個是住在將要坍塌的屋子裡靠蚯蚓和草維持生命的瘋子的故事,另一個是鄉村優秀歌手被認為是淫蕩者實際上是一個閹人的故事,還有一個是這個地方的丐幫幫主的故事,最後一個是這個地方最為著名的強盜的故事。每個故事中都浸透著韓少功特有的沉思風格。
彼得·戈登 (PeterGordon)在《亞洲書評》中寫道:作品缺乏明顯的情節,不過他採用的依然是敘述的方式。作者對作品的處理方式是迷人的和非常有技巧的。作品處處展示出敘述者對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沉思,這些沉思並沒有打斷其中的敘述。作者描述了馬橋這個地方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共存,馬克思主義與鄉下人信仰的衝突,書中栩栩如生的場景幾乎讓你可以觸摸得到。
戈登認為讀這樣的書如同觀賞牆上的壁畫,儘管每篇是獨立存在的,你只有看到相當多內容的時候,才能搞清楚這部書寫的是什麼。《馬橋詞典》在語言上非常有趣,它探索了語言影響文化和思想的方法。事實上,《馬橋詞典》不僅可以用來作為研究民族語言學的材料,它也可以用來作為研究人類學方面的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出了小說的意義。戈登說:當然,我希望他描述的東西是真實和精確的。
 《馬橋詞典》
《馬橋詞典》本·海倫瑞齊 (BenEhrenreich)在紐約的《鄉村之聲》中寫道:韓少功大膽創新的小說採用解構的方式來演義中國鄉村的歷史。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鄉村歷史,被作者熟練地來來回回地反覆刻畫,手法顯得遊刃有餘。作品描述的是世界的一個小角落,是中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這裡既有宗族間的械鬥,又有男女混亂的性愛關係,還有徘徊很久不願離去的幽靈。這本書如同書名所暗示的,材料以字典的形式組織起來。讀者既可以從詞條中看到當地歷史的變遷,也可以看到馬橋人身上的傳統烙印。
有的條目是一些長段落,有的甚至長達幾頁,作者就此將有關鄉村及它居民的傳說、逸事編織在裡面。有的條目是一些簡短語言學方面的思索。馬橋人的語言只有在馬橋這個地方才會有特殊的含義。馬橋人的語言反映出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當時的政治氛圍是:說話不小心就有可能被關進監獄。作者在作品中說:語言只是語言,不是其他什麼東西,它的重要性不應該被誇大。毫無疑問,這本書是一部傑作。
錢希騰 (QIANXITENG)(《哥倫比亞觀察家》的專欄作家)在《哥倫比亞觀察家》上撰文說:當朱莉婭·洛弗爾給韓少功寫信想要翻譯《馬橋詞典》時,韓少功同意了並補充說:我擔心翻譯可能會很困難的。因為《馬橋詞典》本身就是中國南方鄉村馬橋這個地方蕪雜的方言詞語的彙編。
這個地方曾是韓少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鄉接受再教育的地方。遠離家鄉,在偏遠貧窮的地方同農民一起勞動,韓少功努力適應當地的習慣和當地的方言。中國的語言,儘管漢字相同,但不同的地方,語法、發音甚至意義都大不一樣。在《馬橋詞典》中,作者以敘述的方式來解釋他的條目,從村民到這個地方的特殊環境再到這個地方獨有的習慣,作者既注重當地語言的形成又注重語言所反映出的馬橋人的價值觀。
貫穿作品始終的,是作者對當地方言在官方語言影響下所發生變遷的分析。韓少功用詞條羅列的方式,串聯著歷史事件,活靈活現地描繪出了馬橋這個鄉村世界的風土人情。在傳統意義上,它很難算得上一部小說,因為裡面沒有鮮明的以一貫之的中心人物,沒有起承轉合的故事。作者在創作中,追求文體置換,不拘泥於傳統,作品拋棄了固有的小說模式,給人的感覺多是片段性的,既像小說又像詞典,然而這本書卻充盈著豐富的時代精神和深刻的批判內涵。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評論家斯朱威拉(sjwillard)評論說:對美國或英國小說感到厭倦了的讀者應該讀一讀中國的這本小說。它無疑是一部傑作,韓少功在作品中娓娓道來的方式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作品的內容並沒有局限於“文化大革命”這段時間,講述者也描述了毛澤東時代之後馬橋所發生的巨大變革。講述者解釋說他原先打算給馬橋的每樣東西都寫一下傳記。他是無法做到那一點的,但是他在作品中還是極力保持著給每樣東西作傳的興趣。
斯朱威拉認為,這部作品由於沒有清晰的年表,導致作者在時間上前後來回跳躍,這樣容易讓讀者搞混,同時,韓少功沒有把講述者、作者、詞典編撰者明確區分開來,這也是讓人有疑問的。然而,它仍不失為一部非常有趣而又偉大的書。
相關新聞
韓少功《馬橋詞典》催生《上海之舞》
第三屆澳大利亞當代作家論壇日前在滬開幕,曾多次獲得澳大利亞國家級文學獎項的作家布賴恩卡斯楚蒞臨現場,並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卡斯楚告訴記者,非常欣賞中國當代作家韓少功,他的獲獎作品、家族史自傳《上海之舞》就深受韓少功《馬橋詞典》創作方式的影響。
布賴恩卡斯楚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候鳥》以生活在澳大利亞的中國掘金者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小說。此後,卡斯楚的創作與中國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其第四部長篇小說叫做《追蹤中國》 ,第七部小說更是命名為《上海之舞》。
卡斯楚向記者透露,這些創作都源自於家族的記憶,“我的父親是葡萄牙人,於1920年出生在上海,後遷往香港,而我則是在香港出生,從小就聽父親講述他在上海的生活經歷,對中國的事充滿了好奇”。《上海之舞》,敘述了卡斯楚家族早年在上海的生活經歷。他從父輩口中得知這些故事,還從穆時英、施蟄存、魯迅、戴望舒等中國作家的筆下,捕捉到了對上海的印象。卡斯楚說:“而在創作技巧上,給我影響最大的卻是中國當代作家韓少功,我非常欣賞他的《馬橋詞典》,《上海之舞》就借鑑了《馬橋詞典》的寫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