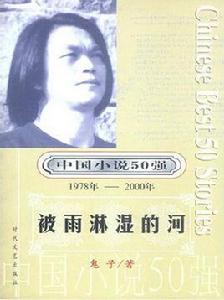內容簡介
《被雨淋濕的河》用一個成年女子的全知視角講述了曉雷一家的故事。小說開頭講述的是“我”從城裡離婚回家的那一天,陽光好得無可挑剔,可陳村的妻子卻在那天去世了。接著,作者追敘了陳村妻子死時的具體情形,然後才開始講述小說的主要故事。他母親因病去世,作為鄉村教師的父親,以中國農民最傳統的教育方式,要求曉雷讀書成材,但是遭到了曉雷的拒絕。雖然最後還是父親的命令換回了兒子的服從,但這服從卻帶來了更加激烈的反抗。曉雷很快就從師範學校逃了出來,加入了當今最時髦、最無奈、最不知道前途的南下打工的行列。
然而,迎接他的確實不像想像的美好,而是一系列靈與肉的摧殘。先是在別人的介紹下去了一家採石場。工作了一段時間過後發現,老闆是從第三個月開始發工資,好多工人因此幹了一段時間無法忍受準備走的時候,前兩個月的工資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老闆的額外之財。曉雷知道後,憤怒不可壓制,一氣之下把採石場那個拿著工人的血汗錢整天荒淫無度的老闆殺了。無奈之下,為了生存,曉雷不得不重新找活。他找到的第二個工作是在日本老闆開的服裝廠當苦力。剛進去就遭遇了一件讓心靈更加震動的事情。
為了追查一件服裝的下落,老闆竟要他的走狗當著所有職工的面脫一位嫌疑女工的褲子,而這位女工當時還懷著五個月的身孕。人格的被褻瀆、尊嚴的被剝奪,讓曉雷再一次站了出來,堅決做了一個“不下跪的打工仔”。這件事情被媒體曝光後,他沒辦法再在那個地方待下去,就回到了老家。父親工資被上級以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押扣,而父親沒有絲毫的反抗,這讓曉雷對父親的沉默和上級的無恥怒火中燒,於是他又策劃全部被扣押了工資的教師集體去教育局領導的新房示威,最後曉雷因為此事觸犯了領導,在他去一家煤礦打工時,因為礦主和教育局領導的親戚關係,將曉雷陷害致死,而曉雷的妹妹曉雨當了包身女且失蹤,陳村也不幸死去 。
創作背景
中國國歷來是個農業大國,20多年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也沒有能夠改變這種狀況。相對於其他行業的日新月異,農業是那么的滯後。正因為這樣,“三農”一詞頻繁地出現在各大媒體的頭條,在溫家寶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曾29次提到這個詞。這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對“三農”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說明了“三農”問題依然突出。孕育於現實母腹中的文學長期以來一直都在關注(或反映)“三農”問題。20世紀80年代,人們如饑似渴地讀路遙的《人生》是因為這部作品反映了計畫經濟時期農村青年面對的人生課題。作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的作品 。
該小說的題目之所以叫《被淋濕的河水》。是作者構思這小說的最初,就是想敘述一個老人的生命是如何走向枯竭的,就像那條河,原來是有水的,但後來的水漸少漸少,最後竟沒有了。老人的生命就如同那條河的生命。 所以他的生命最後了結在了那條幹涸的河床上。 現在的社會裡有著太多沉重的生命 。
人物介紹
曉雷
曉雷是農村青年,他是一個悲情的角色。他與高加林一樣無法認同父輩的生存方式,無法。與自身的生存境域相融匯。不同的是他不願意讀書,迫切要求脫離家庭。他逃出師範學校,以一個社會零餘人的身份,帶著孤獨的少年理想開始了自我價值的艱難追尋。當他發現充滿無序而喧囂的外面世界同樣背離了自己的理想時,他便自覺地進行著各種反抗。先是以惡制惡,以毒攻毒,殺死採石場的楊老闆,然後以俠義精神臨侮不屈,成為“又一個不跪的打工仔”。
回鄉後他聯合全縣的教師揭露當權者的陰謀。事件之後,他進了一家煤廠,但煤廠老闆與教育局長是親戚,曉雷被不動聲色地害死了。曉雷的人生卻是悲慘的,他最終死於非命。他的死作為事件本身是偶然的,但從他自身的性格和命運來推斷又是必然的。他想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改變社會秩序,以他頑強的意志力體現良知和道義,這是堂吉訶德式的方式,最終只能以失敗告終。
曉雷以一個青年人特有的勇氣和闖勁為自己的生存爭得一片天地時,他發現外面的世界其實很殘酷,很無情,他又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和這種殘酷無情鬥爭的時候,他必然會遭致徹頭徹尾的失敗。因為他始終沒有意識到,憑一己之力,和一個強大的社會利益集團抗衡,無論如何,他也不會取勝的。曉雷是眾多苦命打工仔中一個典型的代表。他的個人遭遇其實也是這一整個群體命運的真實寫照 。
曉雨(曉雷的妹妹)
曉雨在小說中儘管她沒有直接出現,但讀者可以想見,同是出身農村的女青年,與劉巧珍不同的是她受了些教育,沒有了劉巧珍那樣靦腆和單純的情懷,對都市有更多現實的憧憬,也有更多走進去的機遇。她讀完國中不甘心在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便來到城裡打工。與許多沒有技藝的同齡女孩一樣,她沒有選擇從事服務業,而是在一家美容店打小工,試圖以迎合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生存理想。她最後禁不起誘惑,做了人家的“包身女”(即二奶)。當然這種行為是要承受道德壓力的,這個人物的生存境遇以及她身上體現出來的人生意蘊同樣值得讀者思考 。
陳村(曉雷和曉雨的爸爸)
陳村,這個老實巴交、恪守傳統的教師,在面對家庭接二連三的打擊,早已承受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並被這沉重壓的頭髮全白,無法站直。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骨肉分離,陳村總是以“心疼”的方式將自我蜷縮在孤獨的空間,從不四處訴說,也不做任何的反抗。儘管他是一個受苦受難的角色,但是他畢竟經歷了諸多的世事,經歷了大半的人生,他執著的信念和對苦難的忍受中,看到了命運的頑強和韌性。他最終也沒有掙脫不濟的命運,在強大的外在勢力面前,他的力量同曉雷一樣,顯得異常渺小 。
“ 我 ”
“我”是從城裡離婚“回家的”鄉村教師。這裡所說的“家”便是鄉下。“我”在城裡的生活狀況不明朗。“我”覺得人世間的醜惡幾乎都雲集在看上去十分發達而美麗的城市中。城裡就像蜜蜂窩,她承認裡面有著許多可口的蜜糖,但也時常叫人蟹得滿身是傷 。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艱難
苦難,是文學一個亘古不變的主題。同時它也是人類成長史的見證以及人類生命史的見證。對於苦難的表述當然有無數的途徑,但是鬼子以其特有的深沉和悲憫將眾多底層人物所遭受的苦難給與了嚴肅的關注和溫暖的慰藉,在整個描寫底層的作品中獨樹一幟。 尤其是對城市農民工這一最具代表性的底層群體的塑造,更是深入人心。在《被雨淋濕的河》中,曉雷無疑是這類人物的代表。在城市改革全面啟動之後,創作的中心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工人問題開始不斷反映,城市農民工成了最具時代性、最富中國特色的群體。從他們身上體現的城鄉衝突、貧富衝突也是異常突出的。當然,從曉雷身上,我們也深深的體會到了來城市打工者所遭遇的異常深重的苦難。
在這樣以城市為中心的道德語境之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必然遭遇著嚴重的考驗,人性的關懷在最大程度的喪失。曉雷的那剛毅不屈但又挫折不息的形象,深深的刻在了每一位讀者的心中。作品中這種現實精神和現代敘述的完美結合,成了這部作品久久不能被淹沒的最大武器。作品中的個個不屈的靈魂,也在爭取自由、爭取尊嚴的道路上艱難的跋涉著一樣,其實,不論是誰,只要走著,就有希望,只要向前行進著,就會看到進步,或大或小,但是這進步卻會成為每一個人繼續前行的無限動力,催促著人們一往無前 。
死亡
小說一開始,作者就直接殘酷地讓人看到“死亡”:“我從城裡離婚回家的那一天,陽光好得無可挑剔,但陳村的妻子卻在那天去世了”。接著,作者又寫了另一個作品主人公曉雷目睹的“死亡”:一件因賭博而起的村裡的兇殺案,“這天,村里突然發生了一起血案。一個隨身帶著尖刀的小子,把一個也是村裡的青年給活活地殺死了。出刀的緣故是因為賭錢的時候對一張人民幣的真假引起了爭吵”。
第三次寫到“死亡”,是外出在採石場打工的曉雷因為老闆硬苛扣他三個月的工錢而與老闆發生衝突,楊老闆是橫豎不給錢,於是曉雷“操起了桌面上的一個酒瓶,閃電般砸在了他的後腦上。曉雷說那是一隻又長又大的酒瓶,但卻沒有發出什麼驚人的響聲。被打著的楊老闆,也沒有發出任何非凡的叫喊,他的身子只是默默地往旁一歪,就栽到了地上”。
第四次直接寫到“死亡”是曉雷的死。曉雷在煤場打工,在煤井下讓瓦斯給燒了,他是被人陷害的,“躺在醫院的曉雷卻斷斷續續地告訴他的父親,說他是被人謀害的。他說,他並沒有帶著火機和香菸”。躺在醫院的第四天,臨近黃昏時分,曉雷就死了。
第五次寫到死亡是寫兒子死後一夜白髮的陳村正準備去給兒子告狀,但沒走多遠就在一條幹涸了的河床上碰上了幾個著綠衣綠帽的警察,那幾個警察是前來抓曉雷的,說的就是曉雷在廣東打工的時候,打死了那名姓楊的採石場的老闆。身心交瘁、白髮蒼蒼的陳村,“在人們的眼裡突然晃了晃,像一根枯朽的樹樁倒在了腳下的河床上”,“就那樣再也起不來了”。
在小說的另外兩處,還寫了兩種非生命的“死亡”。在小說的開頭,寫“我”從城裡離婚回到鄉下的家裡,還有幾個地方也提到我對自己原有婚姻和愛情的絕望,這是寫愛情和婚姻的“死亡”。小說的結尾,寫到一條幹涸的河,“那是一條曾經在歲月里流水洶湧的河,可是這幾年,河裡的水漸小漸小,最後竟沒有了”。這是寫河之“死”,這是大自然的“死亡”。在這篇僅僅 30000 字的中篇小說里,7 次直接寫到“死亡”,不能不說觸目驚心。可以這么說,整篇小說都被死亡氣氛籠罩,而且這種氣氛不是象徵性,而是寫實性的。作者一直在冷靜平實的敘述中,讓人感受和觸摸死亡。人生的有限性、生命的死亡是悲劇的基礎。觸目驚心的“死亡事件”的直接敘述清晰地凸顯了“生死問題”和“生死意義”,這是鮮明的悲劇意識,讓讀者不得不去思考 。
藝術手法
“ 時間倒錯 ” 的時序安排
在敘事時間上,《被雨淋濕的河》最能體現鬼子敘事風格的就是時序的安排。時序是故事的時間順序與文本中的時間順序之間的關係。熱奈特將敘事文本的時間和故事的時間之間的複雜關係分為三種,時序是其中之一。他還將故事時序與敘述時序間各種不協調的形式稱為“時間倒錯”。倒敘和預敘是“時間倒錯”的兩種類型。“在敘述過程中,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是:如果事件還沒有發生,敘述者就預先敘述事件及其發生過程,則構成‘預敘’”,“事件時間早於敘述時間,敘述從“現在”開始回憶過去,則為‘倒敘’。”也就是說,預敘是事先講敘或提及了以後事件的發展,倒敘則是對故事發展到現階段之前的事件進行事後追敘。《被雨淋濕的河》中即出現了倒敘和預敘,使用了“時間倒錯”的時序安排。
小說開篇採用了倒敘的手法,第一句話寫道:“我從城裡離婚回家的那一天,陽光好得無可挑剔,可陳村的妻子卻在那天去世了。”接著,鬼子追敘了陳村妻子死時的具體情形,然後才開始講述小說的主要故事。主人公的苦難接踵而至。曉雷逃學南下打工,殺死拖欠工錢的採石場老闆;曉雨當了包身女且失蹤;曉雷慘死於礦難之中,陳村也不幸死去。由此可見,採用倒敘手法展現的事件與主要情節缺乏必然聯繫。或者說,倒敘的事件即陳村妻子的死,其功能在於確立整個故事的死亡基調,營造悲劇氛圍。
故事由陳村妻子的死亡開始,以陳村的死亡結束,悲劇氣氛始終貫穿其中,這一開篇倒敘事件的安排無疑起到了渲染氣氛的效果,加強了作品的震撼力,同時可以使人產生種種疑惑,如“陳村是誰?”“陳村的妻子是為什麼去世了?”這樣的懸念效果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與倒敘形成對比,《被雨淋濕的河》也使用了預敘的手法,如陳村看到曉雷揭發教育局長貪污教師工資的公開信時,“他悶悶地說了兩句完了完了,這小子要完蛋了!”陳村的這句話預示著曉雷的一場大悲劇即將降臨,此後的故事發展就是這一預言的實現過程,曉雷因被人陷害遭遇了煤礦事故,不幸以死亡告終。這一預敘手法產生的效果即是引起讀者的閱讀期待,極大地增強了讀者的閱讀動力。陳村這一人物事先告知讀者曉雷接下來會“完蛋”,這就促使讀者期待進一步追蹤故事將會如何發展,好奇於曉雷“完蛋”這一事件的經過,文本中的時序安排在無形中就成了讀者的閱讀動力。可見,敘事話語的研究已不僅局限於文本本身,也與讀者聯結起來了。
第一人稱 “ 我 ” 的限知視角
熱奈特把視角作為敘事語式即敘述信息調節的形態之一,在《敘事話語》中他區分了三大類聚焦模式即視角的三種類型:第一,“零聚焦”或“無聚焦”,即無固定觀察角度的全知敘述,其特點是敘述者說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敘述者>人物”;第二,“內聚焦”,其特點為敘述者僅說出某個人物知道的情況,“敘述者=人物”,其中包含固定式內聚焦、變換式內聚焦、多重式內聚焦三個次類型;第三,“外聚焦”,即僅從外部客觀觀察人物的言行,不透視人物的內心,“敘述者<人物”。敘事學家一般把視角分為全知視角、限知視角和純客觀視角三種。《被雨淋濕的河》採用的是“敘述者=人物”的“內聚焦”方式,即所謂的限知視角,敘述人“我”是小說中的人物,同時也作為旁觀者和見證者,講述別人的故事。小說的整個故事都是通過“我”這一敘述人轉述出來的,“我”在有限的範圍內敘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訴說發生在身旁的故事。這一敘述視角的特別之處在於,敘述人“我”的故事完全是虛的,“我”的存在只為更好地呈現主要人物陳村和曉雷的悲劇故事,這即是“鬼子式”的視角選擇。鬼子熱衷於第一人稱“我”的視角選擇,“‘我的目光’是鬼子小說敘述的一大特點,這不僅因為小說中大多出現“我”這樣一個敘事人角色,還在於鬼子把所有的敘事都設法轉化成“我”的敘述,都變成我的目光之中的世界。”
小說人物的經歷與命運從“我”的口中轉述給讀者,而“我”的視界不是全知全能、居高臨下的,而是限知的,從這一限知的角度去敘述故事就加強了事件的親歷感與真實感。如文中寫道:“後來是曉雷告訴我,說他拿著我給的三百塊錢,第二天就跑到廣東那邊打工去了。”“我”當初並不知道為何曉雷問“我”要那三百塊錢,不知道曉雷後來去了廣東打工,更不知道在他身上還發生了種種不可思議的事件,而這些事情的原委都是“我”事後從曉雷口中得知再轉述出來的。“我”這一敘述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故事與人物視點的一致性,人物和讀者可以直接進行交流,讀者對人物命運的發展更為直接貼切,這就縮小了敘事者與讀者的距離,增強了故事的真切感。曉雷南下打工時經歷的殺人、下跪等驚心動魄的事件在敘述者平靜的轉述中顯得歷歷在目,主人公陳村和曉雷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也不會讓人覺得虛假。對於讀者而言,故事有了“我”這一敘述人型視角的限知表述,就更具真實感與說服力。
華萊士·馬丁認為,“敘事視點不是作為一種傳送情節給讀者的附屬物後加上去的,相反,在絕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視點創造了興趣、衝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被雨淋濕的河》視角人物的選擇充分體現了這一觀點。文中敘述者“我”是一個剛從城裡離婚回鄉的中年婦女,是一個女性視角的人物。小說一開篇,“我”這個女人和主人公陳村之間模糊不清的暖昧關係,就使文本製造出了懸念效果。這一敘述者的女性性別顯然有悖於作者的真實性別,鬼子這樣的視角安排自有其目的所在。他坦言:“這是一種手段,通過這手段,我可以把許多社會的問題推到故事的背後。另外,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保持一種敘述過程要下雨的感覺,很沉悶的很潮濕的感覺,而女性的敘述能夠給人這種感覺,能夠引起人的某種同情和關注。”因女性更為關注的是家庭問題,社會現實問題自然被推到故事背後,使讀者的關注點轉變為家庭,身為女性的“我”在敘述另一個家庭的悲劇故事時顯得自然、平靜,不禁流露出女性細膩的同情之感,故事情節隨後的發展也始終離不開女性特有的觀察方式。鬼子這一女性敘述人視角的選擇同時證明了現代敘事的敘述人和作者往往是剝離開來的,對於作品而言,作者只是一個隱性的存在。表面上看,作者已隱退到故事之後,實則仍是強有力的掌控者,故事的視角控制始終是作者操縱敘事的結果。
聲音
小說中的“聲音”是敘事的成分之一,它是一個用於敘事的方法,敘述者可以運用聲音講述或展示故事,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則是聲音的製造者。現代小說創作十分重視讀者對敘事文本的參與性建構,其創作較為傾向於運用展示型文本的聲音即作品中人物敘述者的聲音,影響讀者對人物和故事的理解。《被雨淋濕的河》採用作品中的人物“我”來發出聲音,其目的就是為了使文本與讀者更貼近,這樣讀者可以更好地進入故事之中,文本也能產生特有的審美效果。然而,小說中的聲音往往是多重的,即具有多層次性,人物敘述者的聲音可以包含作者的聲音。詹姆斯·費倫在《作為修辭的敘事》中指出,“作者聲音的內在不必由他或她的直接陳述來標識,而可以在敘述者的語言中通過某些手段———或通過行為結構等非語言的線索———表達出來”。
《被雨淋濕的河》中,敘事表層上是由一個中年女人承擔敘述人,但是在敘述人的敘述過程中不自覺地出現了作者的情感態度,發出了另一種聲音。也就是說,人物敘述者的限知視角變成了作者的全知視角,這種視角變換的手段暴露出了作者這一“隱藏敘述人”的蹤跡。鬼子運用這種敘述裂縫使文本發出了“隱藏敘述人”的聲音。如小說在“我”轉述服裝廠老闆命令全體員工下跪的情景時有這樣一段敘述:老闆像頭張狂的野獸,朝混亂的人群兇猛地撲了過來,他一邊推著他們,一邊不停地吼叫著站好!站好!統統給我站好!像一群左衝右突的牛群,民工們又給老闆站成了一支奇形怪狀的隊伍。老闆隨後跳到了一台機車的檯面上,他順著一腳又踢翻了旁邊的一台機子。就在這時,他朝民工們吼出了跪下,統統的給我跪下……驚慌的情緒以狂風的姿態在人們的臉上變幻著……轉眼間,那條畸形的隊伍像一堵擋不住黑風的破牆,紛紛接連地倒了下去。
顯然,這段故事的敘述語氣基本上不符合轉述者“我”的人物身份,而根據曉雷的受教育狀況,這樣的聲音也不可能來自曉雷。“我”只是一名居住在鄉村的中年女性,也沒有親眼目睹過主人公曉雷打工時發生的事件。所以,按敘述者的個人認知和經歷推斷,像“老闆像頭張狂的野獸,朝混亂的人群兇猛地撲了過來”,“驚慌的情緒以狂風的姿態在人們的臉上變幻著”,“畸形的隊伍像一堵擋不住黑風的破牆”,這樣的敘述語句不可能出自“我”的口中。“我”只是作為曉雷故事的轉述者,但卻對這一下跪場面進行了細緻的敘述,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實際上,小說中的“限知視角”已不自覺地轉變成了“全知視角”,這樣的聲音正來自隱藏敘述人,這一視角轉換過程使文本出現了敘述裂縫,作者介入其中就能更好地刻畫主要人物的性格發展。曉雷不向老闆下跪這一事件是刻畫其性格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如果只採用敘述者的限知視角必然無法對這一事件進行詳細的描寫,所以鬼子這一隱藏敘述人聲音就很完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不僅使讀者與作者建立起情感聯結,也使敘述者的聲音得到了強化。鬼子超越“我”這個人物敘述者,自己開始參與敘述,這樣文本在敘述上就出現了敘述的雙重聲音,一個是人物敘述者的,另一個是隱藏敘述人的,而小說中的人物已不再是獨立行動的主體,而是隱藏敘述人的敘述對象,一切故事都暗藏著隱藏敘述人的聲音。綜上所述,《被雨淋濕的河》呈現了鬼子小說“敘事話語”的獨特性。
無論在敘事時間、敘述視角和敘事聲音上都體現著鬼子本人的巧妙構思和敘事策略。“時間倒錯”的時序安排,增強了讀者的閱讀動力;第一人稱的“限知視角”,增加了文本的逼真感;“隱藏敘述人”的聲音使作者退隱,讓讀者與文本的距離更為接近。由此可見,鬼子對小說“敘事話語”的安排極為精心,從而形成了“鬼子式”的敘事風格,拓寬了文本的審美空間 。
作品評價
《被雨淋濕的河》“涉及逃離土地的青年如何在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找到新的生存起點這一嚴峻問題。該篇小說的敘事是憂鬱的、沉重的:民工歧視、賣淫、勞資矛盾、腐敗這些社會現實就透過曉雷的苦難人生折射出來,所有的苦難把人推向了絕境” 。(梁復明梧州學院中文系講師、秦凌燕梧州學院中文系講師)
作者簡介
 被雨淋濕的河
被雨淋濕的河原名廖潤柏,仫佬族,廣西羅城人。1989年中國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廣西文學院副院長,小說家。200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主要作品有《瓦城上空的麥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濕的河》、《大年夜》、《活埋》、《鹽水花生》、《賣女孩的小火柴》、《貧民張大嘴的性生活》。曾獲1997《小說選刊》年度優秀小說獎、1999《人民文學》年度優秀小說獎、2000—2001雙年度《小說選刊》優秀小說獎和第二屆魯迅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