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806-1873)
密爾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和經濟學家,從一定程度上說也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理論家,甚至還是一個政治活動家,曾長期在東印度公司供職,後來又做過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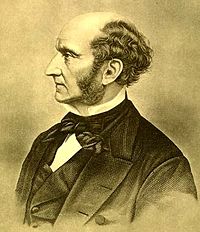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國議會的議員。密爾出生於一個教育環境良好的家庭,其父是著名實證主義哲學家詹姆斯·密爾,密爾的思想受到他的父親以及其它英國和法國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者柏克萊、休謨、邊沁、孔德等人的影響。密爾著作較豐,除《論自由》外,還有《邏輯體系》 《政治經濟學原理》《代議制政府》 《功利主義》以及《威廉·漢彌爾頓哲學的批判》等。密爾是古典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自由主義的幾乎所有原則在密爾的著作中都有論述,這本《論自由》則是密爾表達其自由主義人權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它與洛克的《政府論》(下篇)、羅爾斯的《正義論》並稱為自由主義三大經典著作。莫奎爾(J.G..Merquior )在論述自由主義發展歷史時,稱密爾為“自由主義之聖(the Libertarian Saint)”,還有人把《論自由》的發表作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最後完成的標誌,由此足見密爾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論自由》發表於1859年,其時,資本主義制度早已在英國確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基本上實現了自由,很多理論家已經為經濟自由作了充分的論證,在這種背景下,密爾的這部著作的要旨在於論證個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的自由,一句話,這本書討論的不是經濟自由,而是政治自由(即密爾自己說的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P.1)。這部著作在1903年就被嚴復翻譯過來,定其名為《群己權界論》,這個譯名很精闢地概括了本書的主要論題,即個人自由與他人的自由以及社會利益的界線劃分,就是說個人的自由及其限制,相應的,在社會、國家方面就是對個人自由的干涉的限度。
主要著作
密爾著作較豐,除《論自由》外,還有《邏輯體系》《政治經濟學原理》《代議制政府》《功利主義》以及《威廉·漢彌爾頓哲學的批判》等。密爾是古典自由主義最重
 著作
著作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自由主義的幾乎所有原則在密爾的著作中都有論述,這本《論自由》則是密爾表達其自由主義人權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它與洛克的《政府論》(下篇)、羅爾斯的《正義論》並稱為自由主義三大經典著作。莫奎爾(J.G..Merquior)在論述自由主義發展歷史時,稱密爾為“自由主義之聖(theLibertarianSaint)”,還有人把《論自由》的發表作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最後完成的標誌,由此足見密爾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自由的概念
密爾的引論中開宗明義地交代了本書的論題,即他在本書中所要論述的自由的概念:“這篇論文的主題不是所謂意志自由,不是這個與那被誤稱為哲學必然性的教義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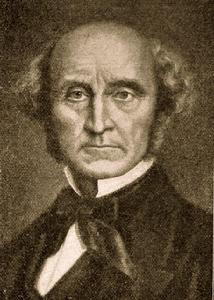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另一個需要警惕的方面是所謂“社會的暴政”,它是指公眾而不是政府以社會習俗而不是多數人的意見的名義對個人自由做出的限制,密爾說,“當社會作為集體而凌駕於構成它的各別個人時,它的肆虐手段並不限於通過其政治機構而做出的措施。”“這種社會暴虐比許多種類的政治壓迫還可怕,因為它雖不常以極端性的刑罰為後盾,卻使人們有更少的逃避辦法,這是由於它透入生活細節更深得多,由於它奴役到靈魂本身。”
然而在個人自由和社會權威凌駕於個人的限度之間劃出一個界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密爾說,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力主一條極其簡單的原則,使凡屬社會以強制和控制方法對付個人之事,不論所用手段是法律懲罰方式下的物質力量或者是公眾意見下的道德壓力,都要絕對以它為準繩。”“這條原則就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各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這就是說,對於文明群體中的任一成員,所以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為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於本人自由,對於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這裡密爾明確地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即除某一行為正在傷害或必會傷害他人或社會的利益外,做出這一行為的自由不應受到限制。這是全書的核心論點,在後面還會詳細談到。
密爾在引論中強調,他的自由原則只適用於理智健全的成年人,“自由,作為一條原則來說,在人類還未達到能夠借自由的和對等的討論而獲得改善的階段以前的任何狀態中,是無所適用的。”不僅對於理智不健全的人,甚至對於作為整體來說尚未進步到可以借說服或勸告來指引他們去自行改善的程度的社會或民族,自由原則也是不適用的(密爾在這裡使用的論據是功利主義原則)。從這裡可以看出密爾把他的自由原則打開了一個缺口,他的自由只是針對文明社會的。確實,對於野蠻社會沒有什麼道理可說,但是這個例外為密爾的祖國——大英帝國的對外擴張提供了堂而皇之的藉口。
接著密爾又提出一個例外:“還有許多積極性的對他人有益的行動,要強迫人們去做,也算是正當的:例如到一個法庭上去作證;又如在一場共同的自衛鬥爭當中,或者在為他所受其保護的整個社會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聯合工作當中,擔負他的一分公平的任務;還有某些個別有益的行動,例如出力去拯救一個人 的生命,挺身保護一個遭受虐待而無力自衛的人,等等。總之,凡顯系一個人義務上當做的事而他不做時,就可要他對社會負責,這是正當的”。密爾的自由原則以及兩個例外的價值基礎都是功利主義,這一點密爾在引論里說得很清楚:“在這篇論文中,凡是可以從抽象權利的概念(作為脫離功利而獨立的一個東西)引申出來而有利於我的論據的各點,我都一概棄置未用。的確,在一切道德問題上,我最後總是訴諸功利的;但是這裡所謂功利必須是最廣義的,必須是把人當作前進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為根據的。”密爾的功利主義理論基礎在他的這部著作中隨處可見,我們在後面的述評中再來討論密爾自由理論的功利基礎。可以說他的自由主義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
在作了以上簡要的論證之後,密爾在引論的最後概括出了他的自由的範圍:“這個領域包括著,第一,意識的內向境地,要求著最廣義的良心的自由;要求著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著在不論是實踐的或思考的、是科學的、道德的或神學的等等一切題目上的意見和情操的絕對自由……第二,這個原則還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指定自己的生活計畫以順應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歡的去做,當然也不規避會隨來的後果……第三,隨著各個人的這種自由而來的,在同樣的限度之內,還有個人之間相互聯合的自由;這就是說,人們有自由為著任何無害於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聯合,只要參加聯合的人們是成年,又不是處於被迫或受騙。”密爾並且認為,對於自由的侵犯,不僅可能是法律上的,在當時的英國,更重要的還是道德上的,即對於屬於個人自由範圍的事務的不適當的道德譴責。這涉及到密爾對於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的劃分,這在後面還會提到。
密爾的這篇引論不是一個簡單的導引,它概括了本書的主要原則和理論根據,高度地概括了密爾的自由主義人權思想,是本書絕對不能忽視的一個部分。
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
第二章的論題只是本書主要論題的一個分枝,在這一章里還沒有涉及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力的劃界問題,只是對普遍承認的個人自由的內容的理論證明,密爾說,“這一分枝是思想自由,還有不可能與它分開的與它同源的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即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在英國這樣的立憲制國度里,言論、出版之類的自由不僅得到普遍承認,甚至還得到了憲法的保障,立憲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但是,並不能因此對以公眾的名義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放鬆警惕:“我所拒絕承認的卻正是人民運用這種壓力的權利,不論是由他們自己來運用或者是由他們的政府來運用。這個權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並不比最壞的政府較有資格來運用它。應合公眾的意見來使用它比違反公眾的意見來使用它,是同樣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假定全體人類減一執有一種意見,而僅僅一人執有相反的意見,這時,人類要使那一人沉默並不比那一人要使人類沉默較可算為正當。”“假如那意見(少數人的意見)是對的,那么他們是被剝奪了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假如那意見是錯的,那么他們是失掉了一個差不多同樣大的利益,那就是從真理與錯誤衝突中產生出來的對於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
這即是說思想自由不在於持有某一意見的人數的多寡,這就是我們已經認作老生常談的一句話: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但是密爾的觀點是,不論這少數人所持有的觀點最後證明是否正確,都不能剝奪他們持有並公開主張它們的權利。
密爾分兩種情況分別對此加以論述,一種是當多數人的觀點可能不正確的時候,那么少數人的意見尤顯珍貴;在另一種情況下,即多數人的意見確是正確的時候,少數人的錯誤意見也應該得到保護,允許自由表達。“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所力圖窒閉的意見是一個謬誤的意見;假如我們確信,要窒閉它也仍然是一個罪惡。”
第一種情況,“所試圖用權威加以壓制的那個意見(少數意見)可能是真確的。”
密爾說,壓制不同意見的人要么假定了自己意見的不可能錯誤性,要么就算認識到自己意見的可錯性(fallibility),也很少想著有必要對自己的可錯性採取什麼預防辦法,很少有人會認為自己一向確定的意見竟然可能是錯的。而事實上,“所謂世界,就每個個人來說,是指世界中他所接觸到的一部分,如他的黨、他的派、他的教會、他的社會階級。”每個人的所知都是有限的,沒有人可以確定地掌握一切真理,對於整個時代來說也是一樣,“這一點是自明的,也像不拘多少論據就能夠表明的那樣,時代並不比個人較為不可能錯誤一些……現在流行著的許多意見必將為未來時代所排斥,其確定性正像一度流行過的許多意見已經為現代所排斥一樣。”密爾在真理問題上所秉持的懷疑主義原則是他得出言論和表達自由的主張的重要理論前提,密爾的基本出發點是:“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所力圖窒閉的意見是一個謬誤的意見。”真理應該在與反對意見的爭辯中確立其地位,而不能不經辯駁就徑直確立其為真理,密爾說:“對於一個意見,因其在各種機會的競鬥中未被駁倒故假定其為真確,這是一回事;為了不許對它駁辯而假定其真確性,這是另一回事。”人類若要一步步接近真理,就必須將所有理論都向一切反對意見開放,“借著討論和經驗人能夠糾正他的錯誤。”只有不斷聽取不同意見才能保證經常的正確。
密爾特彆強調,可能錯誤性對於一切意見都是適用的,任何出於對某一理論的預設的正確性的主張或者有用性的主張而對反對意見的限制,都是不符合自由原則的。密爾反對了兩種對限制自由的辯解:一種是說即使某種意見可能有錯,但它確是有用的,那么也不允許反對意見的質疑;另一種是說某些絕對的真理(如上帝)是不能夠被反對意見質疑的。
密爾對這兩種意見都進行了駁斥。對於第一種,密爾說,“一個意見的真確性正是其功利性的一部分……沒有一個與真確性相反的信條能是真正有用的。”對於第二種,他說,“正是在所謂不道德或不敬神的場合上,一代人曾經犯了引起後代驚詫和恐怖的可怕錯誤。”並舉了一個我們都很熟悉的人類文明的悲劇——蘇格拉底之死的例子,悲劇之所以產生,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公眾對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盲信和對反對意見以及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的不能容忍。
值得注意的是,密爾本人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但他同時主張對異端和無神論者抱以足夠的寬容,他用大量篇幅論述了宗教寬容問題。寬容是自由主義的內在品質,這一點明確地反映在絕大多數自由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著中。但是其本身就是基督徒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主張宗教的寬容並不是因為他們同意非基督教的教義,而是要把這些謬誤暴露在公正的評判面前。
第二種情況則是:“不再假定任何公認意見都會謬誤,而姑且冒認它們皆系真確”。這裡只是一種假設,因為密爾在前面已經論述了任何意見未經充分討論和經驗證實是不能被認作正確的,所以密爾用了“姑且”“冒認”這兩個詞,即使在假設某些意見確係正確的情況下,允許反對意見的充分表達也是必要的。密爾說:“凡持有一種堅強意見的人,不論怎樣不甘承認其意見有謬誤的可能,只要一想,他的意見不論怎樣真確,若不時常經受充分的和無所畏懼的討論,那么它雖得到主張也只是作為死的 而不是作為活的理論——他只要想到這一點,就應該為他所動了。”
密爾第二部分的論據是,一種意見縱然是絕對正確的,如果不允許對它的反對意見得到充分表達,那么這種真理就不能在與錯誤意見的鬥爭中更加站穩腳跟,“在每一個可能有不同意見的題目上,真理卻像是擺在一架天平上,要靠兩組互相衝突的理由來較量。”譬如地心說和日心說,如果一個人只是聽別人說日心說是對的,地心說是錯的,而不知道日心說為什麼是對的,地心說為什麼是錯的,那么他不算真正懂得了日心說的根據。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在道德、宗教、政治、社會關係、生活事務等方面,道理都是一樣的。
對於那些錯誤的意見來說,如果不讓我們知道這些意見是什麼,我們又如何能知道它是錯誤的呢?如要確認一個意見為錯誤,“就非把它們自由地陳述出來並置於它們所容有的最有利的光亮之下不可。”
以上只是說的對於哪怕是確定的真理缺乏自由討論在認識上的危害,接著密爾還論述了缺乏自由討論在道德上的危害。他說:“在缺乏討論的情況下,不僅意見的根據被忘掉了,就是意見的意義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鮮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沒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陳套中保留下來的詞句;或者假如說意義還有什麼部分被保留下來,那也只是意見的外殼和表皮,其精華則已盡失去了。”密爾在這裡顯然說的是基督教的真理,對於教徒來說,對教義缺乏活生生的理解,就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這樣的教義在普通的信徒那裡沒是沒有紮根的,在他們心中並不成為一種力量。被教條化的理論是沒有活力和生命力的,對人們的生活也沒有現實的指導意義。聯想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目前在中國的境地,與密爾所批判的缺乏自由討論的教條有何二異?事實上任何意識形態都難免以國家的權威來代替自由的討論,占優勢的意見為自己主張的理由常常不是它的理據,而是它占優勢這件事實本身。
相反,那些處於不利地位的理論,由於常常遭受責難,不得不時時為自己尋找辯護的理由,倒反而能保持住長久的生命力。一種理論一旦對它產生質疑的人越來越少,它的生命力必然逐漸衰退。這是很深刻的思想。
在論述了少數人的意見和多數人的意見的兩種對立情況之後,密爾接著提出第三種情況,就是多數人和少數人的意見各有一部分是真理,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的討論也是必需的,因為一個理論包含部分的真理,其另一部分必然是謬誤,而另一種理論也許正在這種謬誤方面是正確的,這就需要不同理論之間的相互補益,各取其當。這樣才能在權衡中得到一個較為正確的理論。
在這一章的最後密爾總結了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四個根據:歸納起來就是,一,被壓制的少數意見可能是正確的;二,普遍的意見可能是部分錯誤的,它需要少數意見的部分真理來補充;三,即使少數意見是錯誤的,它對於激發真理的活力、反襯真理的正確性也是必需的;四,只有在於謬誤的對峙中,真理才能深入人心,真正為人所理解。
自由與個性
在第二章中密爾論述的是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思想自由屬於純意識的領域,只可能關涉到個人自身,表達自由雖然可能影響到他人,但它是思想自由的直接結果。第三章論述的則是個性的問題,即一個人是否享有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的自由。密爾認為,一個人在持有一種觀點上既然享有絕對的自由,那么就按照這種觀點行動來說,應該享有同樣的自由,只要這種行動不危及他人的利益。“既然說當人類尚未臻完善時不同意見的存在是大有用處,同樣在生活方面也可以說:生活應當有多種不同的試驗;對於各式各樣的性格只要對他人沒有損害應當給以自由發展的餘地;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應當予以實踐的證明,只要有人認為宜於一試。總之,在並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個性應當維持自己的權利,這是可取的。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卻以他人的傳統或習俗為行為的準則的地方那裡就缺少著人類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這個因素同時也是個人進步和社會進步中一個頗為主要的因素。”
個性以及個人的行動自由普遍被人忽視。人們常常認為跟隨習俗、跟從大多數人的做法總不會有錯,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個性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沒有認識到“首創性”的價值。密爾引用了德國政治理論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一句話:“人的目的……乃是要使其各種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調和的發展而達成一個完整而一貫的整體” 。這就是要充分發展人的各種能力和個性,而發展人的個性所需要的是兩樣東西:“自由和境地的多樣化”,就是行動的自由和生活環境的多樣化。
密爾不否認社群的價值,因為社會的經驗對個人的發展總是有一定指導意義的,但是這種指導是很有限的,別人的經驗也許太“狹窄”;也許不一定適用於自己;就算社會經驗既是好的又是適合於他的,盲目的跟從也不會起到教育作用,對人的發展毫無用處。密爾極其精闢地評論到:“凡是聽憑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屬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選定生活方案的人,除需要一個人猿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它能力。”
密爾主張不僅要賦予個人按照自己意志行動的自由,還要著力培養人的欲望和衝動(積極自由),因為這是個性的集中表現。這是針對當時英國的社會狀況來說的,在密爾看來,當時的英國社會,“已經相當戰勝個性了;現在威脅著人性的危險並不是個人的衝動和擇取失於過多,而是失於不足。”在一個缺乏個性的社會,對個性的闡揚則顯得格外必要,我們可以聯繫一下中國的情況,在八十年代之前,整箇中國幾乎沒有個人的自由,國家和社會強調的都是平等、一致、趨同,強調的是社群的內在價值,人的個性完全消解在社會的共性中,鮮有的特立獨行之人,其下場也是有目共睹;然而歷史已經證明,正是這些特立獨行的人為社會的發展、改進提供了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卻被一群沒有個性的人扼殺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的暴虐”。這正是密爾所擔心的。“今天敢於獨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這正是這個時代主要危險的標誌。”現在的中國社會,對個性的強調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但是無論從社會環境還是社會意識來看,距離密爾所說的個性的社會還遠得很,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媒體,處處都在以同一種聲音教導人們朝著同一化的方向上發展,社會上也還有相當多的人沒有意識到個性的重要,甘願被強勢意識形態和大眾意志牽著鼻子走,一個極其典型的例子是每年中央台的春節聯歡晚會,實在難以想像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裡有10億人在同一時間坐在電視機前收看同一台節目!
個性自由是個人發展的前提,密爾說,比別人具有較多個性的人,即天才的發展不僅對於自己,而且對於他人、對於社會都有好處。“永遠有些人不但發現新的真理,不但指出過去的真理在什麼時候已不是真理,而且還在人類生活中開創一些新的做法,並做出更開明的行為和更好的趣味與感會的例子。” “這些少數人好比是地上的鹽,沒有他們,人類生活就會變成一池死水。還不僅是靠他們來倡導前所未有的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們。”相反,多數人的意見往往成為沒有個性的、平庸的意見。
除了功利主義的根據,密爾還看到了對個性的倡導的事實前提,即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這使得個性發展成為可能更成為必要,密爾是這樣說的:“一個人只要保有一些說得過去的數量的常識和經驗,他自己規劃其存在方式總是最好的,不是因為這方式本身算好,而是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方式。人不像羊一樣;就是羊,也不是只只一樣而無從辨別的。”論述何等的精彩!
密爾特別以東方社會為鑑提醒人們斫喪個性的可怕,他認為東方社會,尤其是中國,是一個沒有個性的社會,幾千年前中國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由於對個性的抹殺,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沒有進步,而終於被西方趕上。當時的英國個性的喪失雖然還沒有到東方世界那樣嚴重的程度,但也存在著阻礙個性發展的種種因素,所以密爾號召人們起來反對社會的同化。最後,密爾以這樣一句話作為這一章的結束語:“人類在有過一段時間不習慣於看到歧異以後,很快就會變成連想也不能想到歧異了。”
在考察自由主義發展歷史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個性與自由的結合是密爾自由理論頗具特色的一部分,嚴格說來,個性的概念與自由主義沒有必然的聯繫,自由是一個個人言行與外部限制的關係問題,個性則是個人內在特質和內心自由問題,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個性的概念可能導致積極自由的觀念,因此,英美自由主義傳統一般不強調個性的問題,密爾對個性的強調來源於德國哲學家洪堡的影響,但是將個性與自由主義如此緊密地結合起來則是密爾的理論獨創。
自由的限度
在本書第四章,密爾才真正提出了他的核心問題:“這樣講來,個人統治自己的主權又以什麼為正當的限制呢?社會的權威又在哪裡開端呢?人類生活中有多少應當派歸個性,有多少應當派歸社會呢?”即個人自由和社會權威的界線問題。密爾緊接著對兩者作了最粗略的劃分:“凡主要關涉在個人的那部分生活應當屬於個性,凡主要減小在社會的那部分生活應當屬於社會。”密爾說,之所以對他極力倡導的個人自由要做出限制,是因為處於社會中的每個人對他人、對社會都負有一份責任,即不得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對於不涉及到他人的純私人領域的問題,別人和社會都絕對沒有任何干涉的權力,這是一條一般原則;而對於涉及到他人或社會利益的非屬純粹個人領域的言論或行為,社會則有權力根據功利的原則做出評判,即在這些行為對別人或社會產生的利益與損害之間作出權衡。但是本文的要點不在於論述這種權衡的標準,而在於強調在不涉及他人的領域,個人有完全的自由,“當一個人的行為並不影響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們願意就不需要影響到他們時(這裡所說有關的人都指成年並具有一般理解能力的人),那就根本沒有蘊蓄任何這類問題的餘地。在一切這類事情上,每人應當享有實行行動而承當其後果的法律上的和社會上的完全自由。”對於個人是這樣,對於若干個人自願組成的團體也是一樣,只要某一行為是出於這個團體的共同意願,而且不涉及團體之外的人,那么別人對這些行為也不應加以干涉。
密爾的這個原則往往會被人誤解為“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對此,密爾完全不同意,他說他對個人道德的重視不亞於社會道德。不得干涉他人,只是最低的道德要求,違反它,一定是不道德的,但是也不能說僅僅遵守這條原則就是一個道德的人了,對於他人的福祉,還是應該在道德上給以關注。但是這種關注也絕對不能超越那條一般原則,即只能通過勸說的方式,而絕對不能使用強制力,否則就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即使這種強制能給他帶來好處,但是這種好處足夠被因為破壞那條自由原則而帶來的壞處完全抵消。“一個人因不聽勸告和警告而會犯的一切錯誤,若和他容讓他人逼迫自己去做他們認為對他有好處的事這一罪惡相權起來,後者比前者是遠遠重得多的。”密爾事實上是劃定了社會規範的高限與低限:個人不得傷害他人的權利與利益,這是社會規範的低限,是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是社會秩序的根本。但是,個人是否以某種高尚的道德規範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則完全是個人的選擇問題。
與密爾的自由原則相聯繫的是他的關於私人道德和公眾道德的區分。在只涉及個人自身的行為中,只有所謂的私人道德,如情趣品味、生活格調等等,其實在密爾看來,像愚蠢與聰明、品味的好壞、格調的高低這些問題根本不是道德問題,它們至多對別人造成“觀感上”的影響,如讓人看著不舒服、讓人鄙視,而不會給別人的利益造成損害,所謂私人道德的“道德”兩個字是加引號的;而真正的道德是公眾道德,即只有在涉及他人的情事上,才存在真正的道德問題。這就排除了從道德的角度對純粹私人領域的事務進行干涉的理據。就更不要說法律上的干涉了。
有些人反對說,一切看似純粹私人的行為都可能影響到別人的利益,密爾並不否認這一點,但是他強調,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涉及他人利益,並不是抽象地看行為本身的性質,而是要看它的具體後果,就拿懶惰來說,這本是屬於私人領域的事情,但是如果一個人因為懶惰而沒有能力養活他的子女,那就是沒有盡到社會責任,因而對別人的利益有所關涉,已經不屬於純粹私人領域的行為了。密爾反對的是這樣一種主張,即由於某種私人行為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影響到別人的利益而將這種行為完全禁止。
密爾反對公眾干涉純粹私人行為的一切論據當中最有力的一點是,對於個人來說,自己的事務只有自己才是最佳裁判者,因為只有本人才會真正關切自己的切身利益;別人的評判無非是出自一種情感,別人只是習慣性地反對他們看不慣的行為,至於這種行為對行為者本身是否有益,他們是不會真正關心的。因而,從每個個人的利益、進而從整個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對私人行為施加任何干涉都是不當的。
本章的最後密爾提出了一種比較複雜也比較困難的情況:一種公眾行為,如果不加禁止,則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直接或間接危害社會,而如果加以禁止則會侵害別人的自由。如售酒行為,如果買酒的是酗酒者,那么這種商業行為肯定會對社會造成危害;而如果買酒是其它有益的用途,那么就不會侵害他人或者社會的利益。對於有些人主張的禁酒令,密爾是堅決反對的,因為這無疑剝奪了非酗酒者購買酒類作其它用途的自由;而對售酒行為毫無限制也是密爾所反對的。他主張對這種行為只要加以必要的限制就可以了,但是絕對不能完全禁止。
兩條自由原則的套用
《論自由》的最後一章是對上文所說的自由的原則的套用的一些示例,實際上就是討論具體情況下在他的自由的兩個原則之間如何選擇的問題。這兩條原則是:“第一,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麼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第二,關於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為,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並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假如社會的意見認為需要用這種或那種懲罰來保護它自己的話。”第一個示例:某些合法的行為不可避免地會合法地影響到他人的利益,如在謀取職業的競爭中,某些人的成功必然伴隨著另一些人的失敗,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的行為顯然影響到別人的利益,但是密爾說,為著人類的普遍利益,還以聽任人們就以這種結果去追求他們的目標而不加以阻止為較好。即根據功利的原則,一些人的成功所帶來的社會利益要比失敗者失去的利益多得多。
第二個示例是貿易自由的問題,因為貿易總是一種社會行為,在貿易行為中的價格、產品質量等等問題,密爾認為雖屬公眾領域,但也不應加以限制,其理據是經濟的自由,依然是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但是另一些貿易行為,如前面提到的售酒以及出售毒藥的行為,因為它們涉及到其它人的個人自由,是可以加以限制但不能禁絕的。
第三個,由上面的出售毒藥的問題引出的一個新問題,即“警察職能的恰當限度”問題,也就是說,為防止犯罪或事故可以侵犯自由到什麼程度。即如果一個個人行為並非正在侵犯他人或社會的利益,但是存在這種可能,那么警察職能對這種行為應該適用到什麼程度?甚至對於只影響自身利益的行為也存在這種情況,有些人不知道他的行為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按照常理的假設是,如果他知道了,他就不會這樣去做,這時社會可以對他做什麼?
密爾對這個問題的解決仍是訴諸他的功利原則,對可能侵犯他人或社會利益的個人行為,依據自由原則,對行為本身仍然不能加以限制,但是可以採取預防措施,即採取所謂“預設的證據”的手段,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必須履行一定形式的手續,如簽名蓋章、要求有見證人等等。這種方式適用於像出售可能用作犯罪手段的工具之類的情形。美國的槍枝管理就是採取了這種事先預防的方法,在美國,槍枝雖然可以自由買賣,但是買賣的時候必須進行登記,這樣便於事後追究責任。而在中國則完全剝奪了普通公民擁有槍枝以備自衛的權利。
如果是只對自身利益可能產生危害的行為,社會只應給以勸告,只有當來不及勸告的時候才可以暫時使用強制手段。密爾舉了個例子,一個人正要走上一座不安全的吊橋,當來不及向他說明走上這座橋的危險時,警察可以使用強制力將他拉回。
密爾最後得出結論:對於純粹關涉個人自身的錯誤行為可以通過事先預防或事後懲罰的方式進行干涉,但不能進行直接當下的強制干涉,因為這些行為本身只是私人的,社會只能就其可能性加以適當的預防或者就其結果進行適當的懲罰,不然難免會導致武斷的錯誤而剝奪個人的正當自由。
第四個示例,某些行為雖然只關乎自身,但在道德上確是值得譴責的,這種行為如果任其泛濫則對社會風氣是極大的損害,對於這種行為本身,因為它仍然在第一條原則的限度之內,所以還是不應加以干涉,但是對於勸導這種行為或者以為這種行為提供便利條件為職業的行為,是否應當加以干涉?譬如賭博、賣淫,對於私下的賭博、賣淫,自然不可加以限制,但是對於以設定賭場和開設妓院為業職業的人,是否應該加以懲罰呢?這在密爾看來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他說:“這個情事正是那些恰恰站在兩條原則分界線上的情事之一,不容易一下子就看清應當歸於兩條中的哪一條。”而密爾在本書中對於此類行為也沒有給出確定的意見,這個問題可供我們思考和討論。
還有一種情況是若干個人組成一個團體,那么這個團體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具有與個人一樣的自由?密爾認為這個團體只要是自願結成的,那么在成員的意願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是可以做只關涉到這個團體自身的任何事情,就如同個人一樣。但是對涉及團體外第三方的利益甚至是成員的基本利益的行為應該不予承認,如果一個團體的教義是將個人的自由全部交給別人,那么這個團體是不被允許的,因為“自由原則不能要求一個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個人被允許割讓他的自由,這不叫自由。”這個團體的成員還應該享有自願解除這種組合的自由,婚姻就是這種典型的組合,人們解除婚姻的自由與結成婚姻的自由不應有所區別。
接下來密爾分析了幾種對自由原則的誤用,即“在不應當給予自由的地方給予了自由,而在應當給予自由的地方往往不給予自由。”典型的情況是以他人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為藉口而代替他人作決定,這在家長式的政府和家庭表現得最為明顯。國家常常以臣民的事就是他的事為藉口,家長往往以子女的事就是他的事為理由剝奪個人的自由。這是一種誤用。
在另一方面,國家又在一些事情上錯誤了給予了自由。在密爾看來,強制教育應該是國家的義務,如果聽任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自由選擇受教育或不受教育,那么國家就沒有盡到義務。積極自由論者認為國家強制教育之類的行為不僅沒有剝奪自由,反而是給予公民以積極的自由,關於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以及強制教育的問題,後面的評論中還會談到,這裡先不多說。
全書的最後,密爾討論了不侵犯個人自由的政府干涉問題。密爾認為,即使政府的干涉不至侵犯個人的自由,這種干涉也是不允許的。這有三種情況,一是個人對自己的事務的了解總要勝過政府,因此,由自己來辦會更好些;二是即使由政府來辦可能更好,也應該由個人來辦,因為這樣可以提高個人的能力,密爾說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發展的問題而不是自由的問題;第三就是政府包辦一切事務,那么一個社會容易形成對政府的依賴,這樣的政府也容易滋生禍患。對第三種情況密爾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主要觀點是政府應該最大限度地把權力下放給個人,而政府應該做的是收集信息並向個人發布,即權力應該分散,而信息應該集中,因為個人收集信息的能力畢竟有限,只有政府有條件廣泛收集信息並提供給行動者。超出這個範圍,政府的干涉越少越好,“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結蒂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
《論自由》中所體現的自由主義思想的評論
密爾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古往今來諸多自由主義大家雖然在很多關涉自由主義基本原則的問題上取得共識,他們的理論也因為這些內在的一致性而得以統一在自由主義的大旗下,然而,不同的自由主義者,其理論出發點、關注的問題、強調的重點不可能完全一致,事實上,有多少自由主義思想家,就有多少種自由主義學說,有多少部自由主義著作,就有多少種自由主義理論。密爾的自由理論自然也有它的獨特之處,有些是密爾本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某一發展階段的共同特點,有些則是密爾個人獨有的特色,後者如前面提到過的對與個性與自由的聯姻關係的強調。密爾自由理論最突出的,也是他所代表的功利主義自由學派的共同的特點是將自由的價值訴諸功利,將功利原則視為自由原則之所由出。自由主義的功利學派是在對自由原則的根據的上與權利學派持有完全不同的觀點的學派,近代最早倡導自由的理論家如洛克大都從天賦權利的角度論證自由,以密爾為代表的功利學派對這種論證方式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在功利學派看來,以人的自然權利來論證自由,首先遇到的困難是自然權利概念本身的含混,什麼應該是個人的權利,什麼不應該是個人的權利,從自然權利的觀點出發很難有確切的標準;其次,權利原則帶有明顯的革命傾向,在理論上是專斷的,在行動上是激進的,法國大革命就是這種理論的實踐結果,它完全不顧它所鼓動的革命行動可能造成的後果,這是事事必訴諸功利後果的密爾所不能接受的(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密爾的自由主義並不像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在重印序言中所說的是“急進”主義的),功利主義是密爾最高的也是絕對的原則,密爾自己說:“的確,在一切道德問題上,我最後總是訴諸功利的。”對自由的倡導本身就是出於功利的考慮,而不是像權利論者將個人自由訴諸抽象的個人權利。密爾在引論中就說道:“凡是可以從抽象權利的概念(作為脫離功利而獨立的一個東西)引申出來而有利於我的論據的各點,我都一概棄置未用。”對於自由原則的例外情況,密爾所用的根據也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功利主義。如侵犯他人利益的行為為什麼超出了自由的限度,是因為它損害了他人或社會的利益;對於一個人負有義務應當做的事如果沒做,政府就應該強迫他去做,也是因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會造成較大的損害。密爾的兩個自由原則之間的界線,也完全是一個功利的權衡問題。
第二個特點,密爾的自由理論建立在兩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之上,即個人的理性和信息的充分。密爾之所以倡導個人自由,在必要性上是出於功利主義的考慮,而在可能性上則是作了上述兩個假設。因為人是理性的,為個人的利益考慮是每個人的自然本能,而且每個人都最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怎樣行動能夠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而政府、社會不僅無需,而且不應該干涉個人事務。也正是因此,密爾把理智上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和理智上有缺陷的精神病人排除在自由原則的適用對象之外。但是密爾的這兩個假設是不牢固的,因為並不是每個成年人都是理智健全的,更不可能每個人都是信息充分的。前面提到過一個人過一座危險的橋的例子,他不知道那是一座危險的橋,這時使用強制力把他從橋上拉下來就不是對他自由的侵犯;密爾也承認有些人不一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也不一定知道怎樣做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時,政府或社會給以一定的干涉就是正當的,像自願賣身為奴這種情況,雖然是自願的,政府仍然應當禁止,因為密爾認為,自願賣身為奴的人不知道自己最需要的乃是自由。問題在於,密爾一方面說個人的事務只有自己最了解,另一方面又要對不了解自己事務的人進行干涉,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矛盾。一旦以個人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為藉口,一切專斷的干涉都可以成為正當,這是這個矛盾必然導致的後果。
第三,密爾在《論自由》中所談的自由是20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柏林在《兩種自由概念》中所說的消極自由。消極自由就是免於……的自由(be free from),積極自由則是去做……的自由(be free to)。自從柏林提出這種劃分以來,理論家們總喜歡把各種自由加以分類,我們也可以來看看密爾所說的自由是消極自由還是積極自由。消極自由的典型表述是“不受限制”,積極自由的典型表述是“做自己的主人”,在柏林本人看來,真正的自由只是消極的自由,積極的自由完全可能邏輯地推導出非自由的結論,而在很多場合,對積極自由的強調超過了消極自由,目前中國的自由觀也可說是積極的自由觀,它強調自由就是能夠把握自己的生活,其前提就是對客觀必然性的把握,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從密爾的論述來看,他的自由觀完全是一種消極的自由,即免於他人干涉的自由,至於做自己的主人,毋寧說是發展的問題而不是自由的問題。有人拿出密爾在引論里的一句話作為積極自由的論據:“唯一實稱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處的自由。”這看來似乎是對積極自由的倡導,而其實密爾的意思是,“唯一實稱其名的自由,乃是我們按照自己的道路不受干涉地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處的自由。”這仍然是免於干涉的消極自由。
對於密爾所主張的國家強制教育,也很容易被理解為積極自由,即國家給予公民強制教育,是為了使每個人都能夠掌握更多的知識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而在密爾看來,國家強制教育是自由的一個例外,是對自由的一種不得已的侵犯,因為它比較符合功利原則。強制教育無疑剝奪了公民選擇受教育與不受教育的自由,而根本不是一種自由的賦予。又有人說,國家強制教育是有物質保障的,它為因貧窮而無力受教育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條件,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對自由的剝奪,但是,我認為,這仍然不是一種自由的賦予,而是對自由的條件的賦予。自由不等同於自由的條件,自由只在於免受他人意志的干涉。有人說,我想像鳥兒一樣在天上飛,可是我不能,所以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可以這樣問一句:有人限制你像鳥一樣在天上飛了嗎?如果你長了翅膀,一樣可以在天上飛,只是現在你沒有翅膀,這不是你沒有在天上飛的自由,而是你不具備自由地在天上飛的條件罷了。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對密爾的自由觀作出結論:密爾的所論述的自由乃是柏林所說的消極自由,因而也是真正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