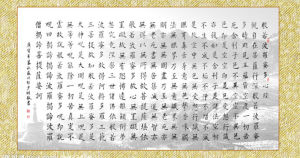心經略說
以一九八七年於美國維州蓮華精舍錄音為基礎
心經兩種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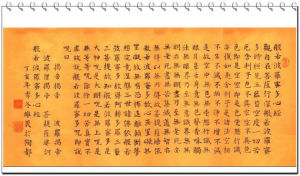 波若波羅蜜多心經
波若波羅蜜多心經玄奘大師承受本經的殊勝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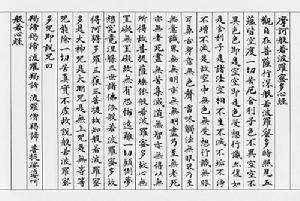 波若波羅蜜多心經
波若波羅蜜多心經經 題
【(摩訶)波若波羅蜜多心經】常念《心經》的經題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括弧中的「摩訶」,見余譯,「摩訶」就是大、多、殊勝三方面。意義很多,往往就不翻了。「大」不是大小的大,就是說這個道理是極其究竟,徹底,離開我們世俗的相對的這些概念。這是一個絕對的大,不是對比。這個火爐和房子比,說房子大,房子和樓比,它又小了。世間上哪有什麼大小,小的就是大的,大的又是小的,都是相對的,這個大不是比較的,是絕對的,「多」、「勝」也都是這樣。「般若」也是梵文,我們可以把摩訶般若翻成大智慧,這都很勉強。因為翻成我們的話表示不足,翻成智慧就很容易和漢文的智慧這個名詞相混。我們常說的智慧,再說就是聰明,再一混變成伶俐。世上這種聰明伶俐成了智慧了?恰恰相反,世智辯聰是我們學佛的八種障難之一,跟聾子瞎子神經病是一樣的,成為學佛的障難呀!這樣混淆就失掉了原文的意思。經中的智慧,是一種怎么能夠了悟實相,契入證入實相的智慧。實相是什麼,我能夠悟;我不但能悟,而且能夠證。也可以這樣說,實相就是佛的知見。所以《法華經》說,十方的如來,「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只是為了一件大事,一個大的因緣,所以出現於世。什麼事?就是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就是要向眾生開顯佛的知見,宣示佛的知見。眾生聽到這些開示,就能開悟明了佛的知見,入佛知見就契入,證入。眾生本來是凡夫的知見,所以大事因緣是什麼呢?告訴我們什麼是佛的知見,我們就從我們的知見逐漸的:有的快,有的慢,快就是頓法,慢就是漸法,把我們原來的知見捨棄了,換成了佛的知見。般若是什麼呢?就是這樣的智慧,你能夠明了,了解,悟到佛的知見是什麼,然後就做到、證實到佛的知見。說句很粗俗的話,佛的思想(當然佛不是想,這是打比方的話),成了你的思想了。不是一個勉強的,這個事情就像要追隨一個領袖,要把領袖的思想變成自己的思想,那你就自然地、忠實地接受領袖的領導。現在要比這個例子更深一步,是知和見。佛之所知,佛之所見,把佛的知見轉成了我們自身的知見。而佛知見是我們本有的,只是我們現在是迷惑了,所以成為眾生知見。般若就是這樣一種智慧,不是一般的聰明。你能拿諾貝爾獎金,你能寫出多少好文學作品,都不是般若。般若一體而有三義:(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一)實相般若是觀照與文字的本體,實相不是有相,不是無相,不是非有相,不是非無相,不是也有也無相,永離一切幻妄的相。可是體性不空,遍為諸法作相,具足過恆沙等等性德的妙用。六度萬行都是本性所具所起。(二)觀照般若如實相之本體而起照用,照時仍是寂然不動。(三)文字般若如實顯示本體與觀照。以上三者即一,實相是觀照與文字的體,觀照是照實相照文字,文字是表達實相及觀照。學人從文字般若入手,而起照用,一旦契悟,入於實相。實相是體,文字是相,觀照是用。「波羅蜜多」是梵文。可以譯為「彼岸到」和「度」(即六度之度)。生死岸中很苦,這一生變人道,不信佛的人來生保人身不容易。你要是儒家,仁、義、禮、智、信這五種都具足;或在佛道里要守五戒,若不達到這個水平,人身保不住。信佛的人很少。有仁、有義、有禮、有智、有信,這也是稀有的人。既然稀有,就是說來生能變人的人很稀有,所以很苦。變畜生,落湯的螃蟹,在鍋里活活地蒸死。雞、豬、羊等等動物,都得被殺。並且子子孫孫注定了都是被人吃的。誰願意自己的孩子被人吃,但豬等就注定了。變成鬼就更苦了,鬼比動物還苦,喉小腹大,不能飲食。重罪的鬼判入地獄,鬼在地獄中是極苦的,一日之中生死千萬次。六道中比人好點是修羅。阿修羅很聰明,很能幹,很有神通。但是他心不純,不善,他嫉妒。另一類是皈依正法作護法、是好的。還有一類嫉妒釋迦牟尼佛,總想破壞,怕人皈依釋迦牟尼佛減少了自己的民眾。這類阿修羅嫉妒障礙破壞佛法,死後墮地獄。六道中最高是天界,外道想升天,但升天還是在六道裡頭。外道以升天做為解脫,佛教以升天看成墮落。因為本來是佛,你現在跑到天界裡去了,沒出六道,早晚一天要轉入三惡道,很可悲。不能以眼前的幸福認為問題都解決了,未出六道早晚還會變豬、變狗、入地獄,所以在六道中同處於墮落,這是此岸。(是指生死六道輪迴這一邊)。諸佛以大智慧,勇猛修行,覺悟正道,永離苦趣,證入涅盤,這是彼岸。一切都寂滅了,寂滅就得到真實的樂。所以佛菩薩是常樂我淨,所以涅盤是彼岸。中流就是煩惱流。為什麼我們度不過去?煩惱無盡就度不過去,能越過這些煩惱就到彼岸了。到了彼岸,就是從生死這一岸到本自無生也就無滅、常樂我淨、寂滅為樂、圓滿無礙的境界,稱為彼岸。「波羅蜜多」原來直譯為「彼岸到」,現翻成「到彼岸」。所以,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就是大智慧到彼岸。「心」,經題中「心」字的涵義有兩個:一個是中心,心要與核心的意思。佛說般若二十二年,佛說法一共四十九年,幾乎用了一半的時間,足見般若的重要。經中說:「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如盲,般若為導(又雲般若為目)。」般若經很多,《大般若經》六百卷,而這個經最短只有二百多字,如同般若中的心,心是中心的意思,核心和心要的意思。例如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心。大乘佛法是全部佛教的核心,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而《心經》是般若經典的核心,所以稱為《心經》。二者,心是指明當人的本心,人人都有一個真心,但我們現在本有的真心被妄心所遮蓋。現在這個我是個妄我,不是真的我。我們現在不實,我們在上當受騙。我們的真心,釋迦牟尼佛在成佛的那一剎那就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任何一個眾生,不但在座的你我,任何一位,就如飛的蒼蠅,小小的螞蟻,以至於作為地獄中的鬼,都有和佛一樣的智慧,和佛一樣的德相。這是我們的本心,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的那個心,就是我們的本心,是我們妙明真心。這一點是我們學佛的最要緊的信念和基礎。要相信自己的心。這是釋迦牟尼佛成佛時說的第一句話,對於這一句話不相信,雖能信佛說的其他的話,你就沒信到根本上,而是信到一些枝葉問題上。要相信這個心。佛接著說:「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我們有這個心,為什麼你沒有佛那么大的功德和神通妙用?就因有妄想、有執著,自己把自己束縛住了,所以就不能證得。所以我們的一切經典,一方面顯明這個真心,叫你恢復你的本心;一方面是幫助你掃除這些妄見,去掉這一切妄,你本有的真就自然顯現,所以跟道教不一樣。道教叫九轉丹成,煉丹,修嬰兒,一次又一次的屍解,要修出一個什麼,證出一個什麼來。佛教是說,我們本來就是,眾生只是錯了,只是睡著了,正在做夢,種種顛倒。你把夢醒了,叫醒你,一醒就完事了。「如夢幻泡影」,在夢中被老虎吃了,何須找人幫助打老虎,只要拍醒你就沒事了。本來沒有老虎嘛!就是這么個事。所以我們要明白,我們都有本心,我們的修行方法也就是如此,不是真的把老虎趕走,趕走老虎乾什麼?老虎是虛妄的,你夢裡才有老虎呢,你醒了之後明白了,原來是個夢。所以這是般若之心,所指是我們的真心。這個「心」字在《金剛經》中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如是生清淨心」,「應生無所住心」。在《觀經》中「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以上兩經中的「心」字,即是本經經題中的「心」字。蕅益大師在《心經釋要》中說:「此直指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即是三般若也」。既然我們當前一念介爾之心就是三般若,足見一切般若經典和一大藏教無非顯明當人各各的自心。而《心經》正是一大藏教的核心,所以直截了當稱為《心經》。大師又說:「實相般若……達此現前一念即實相。」「觀照般若……照此現前一念即實相。」「文字般若……顯此現前一念即實相。」「是故此心即三般若,三般若是一心。此理常然,不可改變,故名為經。」大師開示精妙絕倫。《華嚴經》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故當人本心與佛無別,若能了達現前之念即是實相,亦即了達當人之心即是佛心,心佛兩者毫無差別,若能了達即是實相般若。若能觀照現前一念,雖是水上生波,但全波無不是水,凡有動念何非實相。這即是觀照般若。文字般若只是顯示本體與照用,顯明當前一念即實相。「經」。「經」是通名,「般若波羅蜜多」是本經獨有之名,稱為別名。經的涵義是貫攝常法。貫通古今(貫),廣攝一切(攝),此理常然(常),永為法則(法)。可見經題概括很深的意思。古云:「智者見經題,便知全部意。」有智慧的人看見經題,這個經的全部意思也就知道了。
經 文
【觀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這是大士的兩個名號。《普門品》是觀世音菩薩,正好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昨天來了一位核電站的朋友,他母親信佛很虔誠,常念觀音。他開飛機突然發生障礙,在很危險的時候就聽見有人告訴他,你應該如何操作,他完全照著做,結果平安降落。所以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庇護我們一切苦難中的眾生。這人的媽媽念觀世音菩薩得到觀世音大士的加被。大家只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功德都不可思議。哪怕平時不念佛的人,在急難之中,臨時抱佛腳都有用。你只要肯念,就會有明顯的感應。我們這蓮華精舍有一個同學,他是留學生,從美國回國不久,結婚了。一次坐飛機,覺得今天飛機很不平穩,等一會兒就看見駕駛員從駕駛艙的門裡出來了,向大家宣布:「今天飛機的機械出了故障,我沒有本事使飛機到達目的地了。所以大家你們各自決定吧!願意跳傘的就跳傘,願意如何的從便,總之我是沒有辦法了。」說完了,他就回到他的駕駛艙。全艙的人先一聽很意外,思想還沒轉過來,等思想一轉過來一片哭聲,命在旦夕。這個留學生說,當時第一念是知道這事危險了,但心裡想的倒不是自己怕死。第一想到的是新婚的愛人和孩子,我死了他們怎么辦,剛結婚,孩子還小,先動了這一念,再動一念是什麼呢?他突然想到,我們中國不是有菩薩嗎?當時他的思想活動就是這樣,一聽這話知道是要死,首先想到老婆孩子很可憐,再一想中國有菩薩,就念起觀音菩薩來了。他雖然不信,可是在這種生死關頭的念,往往比平常在佛堂里念要懇切。只是一片求救的心,念著!念著!他就看見觀世音菩薩現身了。他就大聲喊說:「大家不要哭,你們哭沒有用。」他就把自己看到的事情一說:「我已經看見觀世音菩薩了,決定是有,我們大家一塊兒念。」這時大家一想,現在也沒有別的辦法,沒有別的道路,大家就念吧!所以全艙就都念了,念著念著,大家不知念了多少時間了。就都一心去念了。念得很誠,很專一,也很自然,漸漸覺得飛機平穩了,很平靜,很平靜,大家閉著眼睛不知道,只是一心的念,忽然接飛機的人把艙門打開來接他們了,到了!大家喜出望外,飛機已經著陸了。而駕駛艙的門不開,別人把駕駛艙打開,看見開飛機的人昏死過去了,他穿的飛行服都汗透了,當然有醫生急救了。他睜開眼第一句話,「你去問後艙的人乾什麼來著?今天我是絕對沒有辦法把飛機著陸了,不知他們做什麼了。」機場人問客人:「你們在後邊乾什麼哪?」他們說:「我們在念菩薩。」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所以《大乘無量壽經》說:「若有急難恐怖,但自皈命觀世音菩薩,無不得解脫者」。很多很多證明,有許多事情甚至超過古代的《觀音靈感錄》。我知道得很多,但沒有時間去寫,因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要把這些寫下來可以寫很厚的一本書,都是很直接的,不是輾轉道聽途說的。本經大士名號是「觀自在」,「觀自在」表示觀照般若已經自在無礙了。再者,觀什麼呢?先師夏老說:「觀自,身體是自否?那是假的。」所以要觀真我,即是觀自性,自家的主人翁在不在,是不是在做主,是不是被妄心所蒙蔽。夏師又說:「如不知觀自己,不知自在不在,則不能算入門。」「菩薩」全名是菩提薩埵。菩提是覺悟,薩埵是有情,合起來是覺有情。把菩提薩埵簡化稱為菩薩。所以看見名字就知道,不但自利更要利他了,不是自了。蕅益大師說:「智契實相則自利滿足,智宣文字則利他普遍,故名菩薩。」這是能行般若波羅蜜的人。【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前面說了,在法會上釋迦牟尼佛入定,觀世音菩薩也在行很深的般若波羅蜜多。「深」就是深淺的深。加一「深」字就分別於小乘也能修習的通(天台宗通教指大小乘相通之道)般若,而是只有大乘才可以明白入手的般若。唯有大乘行人才能信受奉行,所以稱為深般若波羅蜜。在修行深般若的時候,「照見五蘊皆空」。「照」即觀照般若的照。「蘊」是蘊藏,遮蓋的意思。我們剛才說了,人人有佛性,為什麼佛性不顯呢?就是因為這五樣給遮蓋住了。五蘊是色、受、想、行、識。色蘊是物質這方面,一切萬物,凡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舌所嘗、身所覺,以及意所想到的東西都是色蘊。受蘊,例如,我們現在看見了風扇,看見有一個東西,這個就是色蘊,我們一看,腦子就有所領受,內心生起一種領納的作用,來領納樂境(樂受)、苦境(苦受)及不苦不樂境(舍受)。想蘊就是種種思想,當內心與外境接觸時所引起的思想活動,如了解、聯想、綜合與分析。而我們這個想是念念不斷的,念念遷流就是行蘊。識蘊是我們能夠了別、認識,例如上述風扇轉動發聲,人最初只聽到聲音,隨即知道是聲音,這是耳識;同時傳達到意,能分別了知這是風扇轉動所發的聲音,這就是意識;意識是了別,這個了別的念頭相續不斷,似水長流,前浪後浪滾滾不停就叫作行蘊。所以行蘊以遷流為義。至於受蘊,當聽悅耳順心之聲就歡喜,聽到刺耳違心的聲音則煩惱,所以它以領受為義。受想行識四蘊屬於心的,因為心、身兩方面,心上的障礙更多。所以五蘊里,四個說的都是心,都是精神方面的,只有一個色蘊是有關物質方面的。五蘊都遮蓋我們本性,是妙明真心的障礙。「照」,無心就叫作照,有心叫作想。我們也念《心經》,也能講經,法師也能說五蘊皆空,但是他並沒有度一切苦厄。因為他不是照,他是有心叫作想。觀世音菩薩他是照,他能照見五蘊皆空。照的意思是離開我們的妄念,像鏡子照東西一樣,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根頭髮也不會給你照錯,毫髮不爽。但是鏡子沒有分別,沒有愛憎,不留痕跡。照像的底片照了一張,再按一下就不行了,留了痕跡,再照就照重了,就毀了;鏡子沒有這樣的事,你照一千次、一萬次,都是一點兒也不會錯的,他就是無心。你這個「像」,你東西沒來的時候,它不會來迎接你,東西走了以後,馬上就不再留一點痕跡。這就是它沒有取捨,沒有愛憎;也不是說白種人我就多照你的優點,黑種人我就不照你的優點,都沒有分別。它無心,無心所以清楚,這就叫作照。也就是觀照般若。觀世音菩薩「照見五蘊皆空」,蕅益大師說:「五蘊無不即空、假、中,四句俱離,百非性絕,強名為空耳」。也就是說,五蘊沒有任何一蘊不是空諦、假諦、中諦。提出五蘊皆空,這是空諦,但有五蘊的假名,這是假諦,兩方面合起來,即空即假,便是中諦。因之它們也就離開了「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這四句,既離開了四句,便自然不墮百非。現稱之為空乃勉強之說,實際應說是第一義空。「度一切苦厄」,苦是痛苦,厄是窮困疾厄。苦有各種各種的苦,基本的,人生有八種苦,生、老、病、死,都是苦。在母胎的時候很苦,出生與剛降生的時候都很苦,這是生苦。等到老了,跟老年人談談,也就要訴苦了,美國人說,兒童像在天堂,老人像入牢獄。這兒有病,那兒酸了,這兒疼了,吃東西也不行了,聽東西也費勁了,行走也困難了,甚至腦力也衰了,好多年青時所能享受的,這時候都享受不到了。老是一苦。死是一苦不用說了,說我難受得要死,那就是說死是最難受的。佛說:如活的烏龜,你把它的殼兒扒下來;一隻活的牛,你把它的皮剝下來。人之死所受的痛苦是難免的,還有病苦,「病來方知健是仙」。可見一生病便不是神仙而是受罪了。在生老病死四苦之外,還有怨憎會苦,這個人就是跟我有意見,怎么也不行,偏偏碰到一塊兒,或做你的上級,或做你的朋友,做你的鄰居,甚至於成為你的眷屬。為什麼有的人離婚,這是怨憎會,與別人都很好,就是這兩個人要吵,這是很苦的一件事,怨憎相會。有的人一生怨憎相會,所碰到的都是不如意,到處都有人事問題,到處很苦惱,非常苦。這是八種苦中的一種,「怨憎會」,相怨相憎,偏偏相見。有的人最好不見,偏偏天天見面,偏偏要來找毛病。這是怨憎會,人生不免,知道這個我們就心平氣和了。「愛別離」又是一苦,你最喜歡,你最愛的人偏偏要別離,所以生離死別,死別當然是最後一次,但是生離的情況大家都會遇到,相愛的人偏偏要別離。「求不得苦」,不管是誰,你總會有一件事是你要求而求不到的,例如成吉思汗,他那么大的武功,什麼敵人都被他打敗了,他想求的事情還是求不到。他想求不死,找多少道士,最後給他做了個結論,這不死是不可能的。求不得苦,終有求不得的。一個根本的苦是「五蘊熾盛」,色受想行識這五種東西蔭蓋了你,它很盛,使你的妙明真心不能顯現,因此你有煩惱,這是苦的根本。所以稱為八苦,八苦交煎。觀自在菩薩在修習甚深的大智慧到彼岸時,以般若妙慧觀照五蘊,了達五蘊並非實有,當體即空,又不是空無,乃是第一義空。於是「度一切苦厄」,使自己身心出離分段與變易兩種生死的苦因和苦果,也令全法界眾生同出生死的苦因苦果(根據《心經釋要》)。初機聽到這話,不易信受。自度生死還易信,怎么能令法界全體眾生同出生死呢?應知菩薩發心,便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在修耳根圓通「寂滅現前」時,便得兩種殊勝,上與諸佛同一慈力,下與眾生同一悲仰,證入了三無差別的本心,自心與眾生無別。所以自身心出生死,眾生同出生死。般若妙用難思,這就是波羅蜜多。【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在首尾三分俱全的譯本中:修習般若波羅蜜多深妙行的人應當怎么修習呢?他提一個問。觀自在菩薩答覆舍利子所提的問題,所以首先稱他的名字,舍利子。由於關鍵是照見五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