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李德裕
李德裕李德裕(787—849),字文饒,唐代趙郡贊皇(今河北贊皇縣)人,與其父李吉甫均為晚唐名相。唐文宗時,受李宗閔、牛僧儒等牛黨勢力傾軋,由翰林學士出為浙西觀察使。太和七年,入相,復遭奸臣鄭注、李訓等人排斥,左遷。唐武宗即位後,李德裕再度入相,執政期間外平回鶻、內定昭義、裁汰冗官、協助武宗滅佛,功績顯赫。會昌四年八月,進封太尉、趙國公。唐武宗與李德裕之間的君臣相知成為晚唐之絕唱。後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由於位高權重,五貶為崖州司戶。李德裕兩度為相,太和年間為相1年8個月,會昌年間為相5年7個月,兩次為相7年3個月。
李德裕功業顯赫﹐又善為文章﹐他在《文章論》中﹐援用曹丕文氣之說﹐反對雕琢與拘於聲律﹐重視語言的自然氣勢﹐以為文章當繼承《詩》﹑《騷》傳統﹐“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頗能重視文學特點﹐與當時古文家之宗尚以文貫道者不同。他的詩﹐以五言見長﹐“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句”(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五代孫光憲記時人言:“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北夢瑣言》)﹐可見其詩在當時流傳之廣。晚年貶崖州後﹐所作詩文情思淒婉﹐尤得後人同情。王士禛推崇他說:“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集》﹐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泉》五言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池北偶談》)他還著有筆記小說《次柳氏舊聞》一種﹐記玄宗遺事﹐為其父聞之於柳芳之子柳冕者。其中多詭異之詞﹐不盡實錄﹐然可備異聞。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李德裕《會昌一品集》20卷﹐又《姑臧集》5卷﹐《窮愁志》3卷﹐《雜賦》2卷。《會昌一品集》又名《李文饒文集》﹐今有《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計本集20卷﹐內皆武宗時制誥﹔別集10卷﹐則為詩賦雜文﹔外集4卷﹐即《窮愁志》﹐乃南遷後閒居論史之作。事跡見新﹑舊《唐書》本傳。傅璇琮《李德裕年譜》疑《窮愁志》非李德裕作﹐至少其中摻入偽作。
生平簡介
 李德裕
李德裕公元844年,輔佐武宗討伐擅襲澤潞節度使位的劉縝,平定澤、漣等五州。功成,加太尉賜封衛國公。
長期與李宗閔及牛僧儒為首的朋黨鬥爭,後人稱為"牛李黨爭",延續40年.牛李黨爭最早可上溯唐憲宗時文饒父吉甫與牛等的矛盾.縱觀史實,文饒執政功勳卓著,威震天下;牛黨執政,無所作為,國勢日弱.武宗即位,信用文饒,一掃朋黨,內平河北藩鎮,強藩觫手;外擊破回紇,威震土蕃南詔.唐室幾竟中興.宣宗即位,嫉文饒威名,初貶荊南,次貶潮州。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再貶崖州(治所在今瓊山區大林鄉附近)司戶,次年正月抵達。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正月卒於貶所,終年63歲,逝後被封太尉,贈衛國公。李德裕在瓊期間,著書立說,獎善嫉惡,備受海南人民敬仰,生前代表作有《會昌一品集》、 《左岸書城》、 《次柳氏舊聞》等。
人生事跡
 李德裕
李德裕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廕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闢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
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於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訁冋禁中語,關托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泄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
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訁木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己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
 李德裕
李德裕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朅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雕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朅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鹹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
又詔索盤絛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絛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為停。
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發,規影傜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
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群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 ,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遍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采。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 ,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為逢吉排笮,訖不內徙。齋
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後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跡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譎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
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逾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皋啟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盪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餫遠邇,曲折鹹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厄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台登,以奪蠻險。
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發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
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為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
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台乃聽。凡罷朝,由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捨。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
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凶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
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眾皆以宋申錫對。帝俯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為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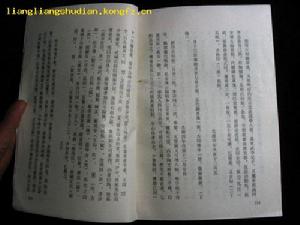 李德裕
李德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鷺,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鷺用其半。僧孺訴於帝,而諫官姚合、魏謨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
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諭,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系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浸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乾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帝嘗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爭,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
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 《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
回鶻自開成時為黠戛斯所破。會昌後, 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言。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為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
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峰,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峰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籓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
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
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托效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舍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脣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弇婀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為兵,猶五攻昌霸,三越漅,況其下哉?然贏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為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群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
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為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舍稹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
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挼穟哺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為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為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鮌、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硃博、陳鹹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奸偽見矣。”
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和後,風俗浸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乾。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
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鹹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為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共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
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
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乾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
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
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忲於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於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
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雲。
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為集賢校理,擢累司勛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
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歷刑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於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傅以罪。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為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鉶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為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愍傷之,為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
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哄於前,而以眾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詩詞鑑賞
 李德裕
李德裕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
李德裕是唐武宗會昌年間名相,為政六年,內制宦官,外平幽燕,定回鶻,平澤潞,有重大政治建樹,曾被李商隱譽為“萬古之良相”。在唐朝那個詩的時代,他同時又是一位詩人。這首《長安秋夜》頗具特色,它如同一則宰輔日記,反映著他日理萬機的從政生活中的一個片斷。
中晚唐時,強藩割據,天下紛擾。李德裕堅決主張討伐藩鎮,為武宗所信用,官拜太尉,總理戎機。“內官傳詔問戎機”,表面看不過從容敘事。但讀來卻感覺到一種非凡的襟抱、氣概。因為這經歷,這口氣,都不是普通人所能有的。大廈之將傾,全仗棟樑的扶持,關係非輕。一“傳”一“問”,反映出皇帝的殷切期望和高度信任,也間接透示出人物的身份。作為首輔大臣,肩負重任,不免特別操勞,忘食廢寢更是在所難免。“載筆金鑾夜始歸”,一個“始”字,感慨系之。句中特意提到的“筆”,那決不是一般的“管城子”,它草就的每一筆都將舉足輕重。“載筆”云云,口氣是親切的。寫到“金鑾”,這決非對顯達的誇耀,而是流露出一種“居廟堂之高”者重大的責任感。
在朝堂上,決策終於擬定,他如釋重負,退朝回馬。當來到首都的大道上,已夜深人定,偌大長安城,坊里寂然無聲,人們都沉入了夢鄉。月色撒在長安道上,更給一片和平靜謐的境界增添了詩意。面對“萬戶千門皆寂寂”,他也許感到一陣輕快;同時又未嘗不意識到這和平景象要靠政治統一、社會安定來維持。騎在馬上,心關“萬戶千門”。一方面是萬家“皆寂寂”(顯言);一方面則是一己之不眠(隱言),對照之中,間接表現出一種政治家的博大情懷。
秋夜,是下露的時候了。他若是從皇城回到宅邸所在的安邑坊,那是有一段路程的。他感到了涼意;不知什麼時候朝服上已經綴上亮晶晶的露珠了。這個“露點朝衣”的細節非常生動,大概這也是紀實吧,但寫來意境優美、境界高遠。李煜詞云:“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玉樓春》),多么善於享樂啊!雖然也寫月夜歸馬,也很美,但境界則較卑。這一方面是嚴肅作息,那一方面卻是風流逍遙,情操迥別,就造成彼此詩詞境界的差異。露就是露,偏寫作“月中清露”,這想像是浪漫的,理想化的。“月中清露”,特點在高潔,而這正是詩人情操的象徵。那一品“朝衣”,再一次提醒他隨時不忘自己的身份。他那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尊自豪感躍然紙上。此結可謂詞美、境美、情美,為詩中人物點上了一抹“高光”。
謫嶺南道中作
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愁沖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這首七言律詩,是李德裕在唐宣宗李忱即位後貶嶺南時所作。詩的首聯描寫在貶謫途中所見的嶺南風光,帶有鮮明的地方色彩。第一句寫山水,嶺南重巒疊嶂,山溪水流湍急,形成不少的支流岔道。再加上山路盤鏇,行人難辨東西而迷路。這裡用一“爭”字,不僅使動態景物描狀得更加生動,而且也點出了“路轉迷”的原因,似乎道路紆迴,使人迷失方向是“嶺水”故意“爭分”造成的。這是作者的主觀感受,但又是實感,所以詩句倍添情致。第二句緊接上句進一步描寫山間景色,桄榔、椰樹布滿千山萬壑,層林疊翠,鬱鬱蔥蔥。用一“暗”字,突出桄榔、椰樹等常綠喬木的茂密,遮天蔽日,連溪流都為之陰暗。這一聯選取嶺南最具特色的山水林木落筆,顯示出濃郁的南國風光。
頷聯宕開一筆,寫在謫貶途中處處提心弔膽的情況:害怕遇到毒霧,碰著蛇草;更擔心那能使中毒致死的沙蟲,連看見掉落的燕泥也要畏避。這樣細緻的心理狀態的刻畫,有力地襯託了嶺南地區的荒僻險惡。從藝術表現技巧來看,這種襯托的手法,比連續的鋪陳展敘、正面描繪顯得更有變化,也增強了藝術感染力。清人沈德潛認為這一聯“語雙關”,和柳宗元被貶柳州後所作的《嶺南江行》一詩中的“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一樣,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詩中的毒霧、蛇草、沙蟲等等都有所喻指。這樣理解也不無道理。
頸聯轉向南方風物的具體描寫,在寫景中透露出一種十分驚奇的異鄉之感。五月間嶺南已經在收穫稻米,潮汛到來的時候,三更時分雞就會叫,津吏也就把這訊息通知旅行的人,這一切和北方是多么不同啊!這兩句為尾聯抒發被謫貶瘴癘之地的思鄉之情作鋪墊。
尾聯是在作者驚嘆嶺南環境艱險,物產風俗大異於秦中之後,引起了身居異地的懷鄉之情,更加上聽到在鮮艷的紅槿花枝上越鳥啼叫,進而想到飛鳥都不忘本,依戀故土,何況有情之人!如今自己遷謫遠荒,前途茫茫,不知何日能返回故鄉,思念家園,情不能己,到了令人腸斷的地步。這當中也深含著被排擠打擊、非罪謫貶的憤懣。最後一句暗用《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越鳥巢南枝”句意,十分貼切而又意味深長。此聯為這首抒情詩的結穴之處,所表達的感情異常深摯動人。
全詩寫景抒情相互交替,景中寓情,情中有景,顯得靈活多變而不呆板滯澀。
登崖州城作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
李德裕是傑出的政治家,武宗李炎朝任宰相,在短短的六年執政生涯中,外攘回紇,內平澤潞,扭轉了長期以來唐王朝積弱不振的混亂局面。可惜宣宗李忱繼位之後,政局發生變化,白敏中、令狐綯當國,一反會昌時李德裕所推行的政令。他們排除異己,嫉賢害能,無所不用其極;而李德裕則更成為與他們勢不兩立的打擊、陷害的主要對象。其初外出為荊南節度使;不久,改為東都留守;接著左遷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最後,終於將他貶逐到海南,貶為崖州司戶參軍。這詩便是在崖州時所作。這首詩,同柳宗元的《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頗有相似之處:都是篇幅短小的七言絕句,作者都是被貶謫失意之人,同樣以山作為描寫的背景。然而,它們所反映的詩人的心情卻不同,表現手法及其意境、風格也迥然不同。
作為身系安危的重臣元老李德裕,即使處於炎海窮邊之地,他那眷戀故國之情,仍然鍥而不捨。王讜《唐語林》卷七云:“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哽。題詩云⋯⋯”他登臨北望,主要不是為了懷念鄉土,而是出於政治的嚮往與感傷。“獨上高樓望帝京”,詩一開頭,這種心情便昭然若揭;因而全詩所抒之情,和柳詩之“望故鄉”是有所區別的。“鳥飛猶是半年程”,極言去京遙遙。這種藝術上的誇張,其中含有濃厚的抒情因素。人哪能象鳥那樣自由地快速飛翔呢?然而即便是鳥,也要半年才能飛到。這裡,深深透露了依戀君國之情,和屈原在《哀郢》里說的“哀故都之日遠”,同一含意。
再說,雖然同在遷謫之中,李德裕的處境和柳宗元也是不相同的。
 李德裕
李德裕柳宗元被貶在柳州,畢竟還是一個地區的行政長官,只不過因為他曾經是王叔文的黨羽,不被朝廷重用而已。他思歸不得,但北歸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否則他就不會乞援於“京華親故”了。而李德裕在被遷崖州,則是白敏中、令狐綯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所採取的一個決定性的步驟。在殘酷無情的派系鬥爭中,他是失敗一方的首領。此時,他已落入政敵所布置的天羅地網之中。歷史的經驗,現實的遭遇,使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必然會貶死在這南荒之地,斷無生還之理。沉重的陰影壓在他的心頭,於是在登臨望山時,其著眼點便放在山的重疊阻深上。“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這“百匝千遭”的繞郡群山,不正成為四面環伺、重重包圍的敵對勢力的象徵嗎?人到極端困難、極端危險的時刻,由於一切希望已經斷絕,對可能發生的任何不幸,思想上都有了準備,心情往往反而會平靜下來。不詛咒這可惡的窮山僻嶺,不說人被山所阻隔,卻說“山欲留人”,正是“事到艱難意轉平”的變態心理的折射。
詩中只說“望帝京”,只說這“望帝京”的“高樓”遠在群山環繞的天涯海角,通篇到底,並沒有抒寫政治的憤慨,遷謫的哀愁,語氣顯得悠遊不迫,舒緩寧靜。然而正是在這悠遊不迫、舒緩寧靜的語氣中,包孕著深沉的憂慮與感傷。情調悲愴沉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