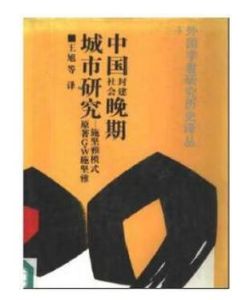研究內容
 施堅雅相關書籍
施堅雅相關書籍施堅雅以對中國市場體系的研究為基礎,結合德國學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理論,提出了中心邊緣理論。他將中國的地域分為中心地與地區系統兩個層面,提出以經濟職能作為中心地的基本職能。按照不同的中心地在經濟職能上的差異而劃分了不同的級別,以中心地的級別形成了相應的地區系統。在地區系統中施堅雅提出了核心-邊緣結構理論,在各個地區系統中地方政府所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責核心區域輕於邊緣區域(註:施堅雅:《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葉光庭等譯,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施堅雅認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於中心地,而地區系統則集中了非正式政治和亞文化群(註:施堅雅:《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葉光庭等譯,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施氏的貢獻在於將原屬地理學的空間概念引入歷史學的考察中,為歷史學開闢了廣闊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場體系理論與巨觀區域理論結合上,存在著重要缺陷。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從實證的角度重新構建符合中國實際的一個市場體系。
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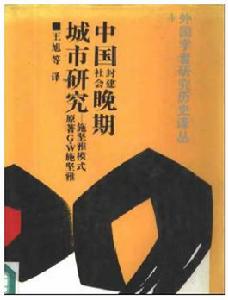 施堅雅相關書籍
施堅雅相關書籍西方學者可能不懂中國,更難以將中國國情窮形盡相。但是,施堅雅模式提醒人們,早應該對明清以來就有的認識框架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應該是多學科、多層面的,尤其是歷史學的反思必不可少,因為施堅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國人所稱的中國近代史。方法論的有效性需要用實證研究加以檢驗,但實證研究本身同樣存在各種局限和失誤,只有當實證研究達到科學實驗的階段,方法論層面的理論模式才能被推翻。歷史研究的實證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科學實驗的水平。因此,就其準確性而言,各種實證性的歷史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只能是相對的,而不可能是絕對的。從近代市場史、城市史、人口史角度對施堅雅模式提出的各種批評,只能證明施堅雅模式是一個有缺陷的分析模式,而不能將其推翻。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施堅雅模式仍是人們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鑑的有效資源。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國學者將對施堅雅模式不斷作出修正,並提出更科學的分析模式。
施堅雅對中國各歷史時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城市發展和地方市場結構所做的大量、細緻、別開生面的研究,使美國的中國史學者提高了在研究經濟社會史時的空間感,注意到了地理條件和空間關係。
理論
 施堅雅
施堅雅我以為,這些看法或多或少都誤解了施氏理論。施堅雅的這個六邊形社區包含18個村莊的模型,並不是根據中國的史料推理出來的,甚至不是根據歐洲的情況推理出來的。它是一個抽象的純粹數學模型。施堅雅實際上認為,理想的、標準的市場區域應該是圓形,但在一個地區布滿了市場區域後,它們彼此擠壓,既無重疊又無空隙時,就變成了蜂窩狀,每一個市場區域被擠成了六邊形。這樣的一個市場區域,其村莊分布按幾何學的原則,應該呈六角形排列,以集市為中心,第一個外環有6個村莊,第二環有12個村莊,以後每增加一個外環,都比前一個多6個村莊。從理論上講,一個市場區域可以有一個外環,6個村莊;兩個外環,18個村莊;三個外環,36個村莊;四個外環,60個村莊……而中國的經驗數據證明,中國的情況是兩環18個村莊。
施堅雅首先建立了一個幾何學意義上的模型,這個模型可以說是一個先驗的模型,施堅雅自己認為,它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地區,無論是幾何學還是經濟學都不特別具有中國性。(第21頁)以此類推,它們應該也不具有歐洲性或美國性。這個模型對一個市場區域內的村莊數字提供了多種可能性,施堅雅認為他所見到的中國的數據最符合於其中兩環18個村莊的這一種。
施堅雅所謂“村莊與基層的或較高層次的市場之比,在中國任何相當大的區域內,其平均值都接近於18”(第22-23頁),並不僅僅是指中國各地的市場區域下屬村莊數大都在15到20個之間,因而平均值接近於18(雖然施堅雅也確有這種意思),它還有一層進一步的意思,即,與一個市場區域包含6個或36個村莊的模型相比,這些平均值更接近於18個村莊的模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比率的變化可以通過從一種每市場18個村莊的均衡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發展的模型來得到滿意的解釋——但不能通過設定每市場6個或36個村莊的穩定均衡模型來解釋。”
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第二部分中,施堅雅描述了市場的密集循環過程:開始時村莊與市場之比比較低,逐漸增長到18,然後達到24-30之間,又發展到30-36之間,這時開始出現小市,隨著新的基層市場建立,村莊與市場之比下降,會降到18以下,然而隨著村莊的密集,再逐漸上升到均衡模型的平均值。如果假定新一輪基層市場中的第一個要在每個潛在區域都有了12個村莊時才會建立,那么,模型A(代表山區)的臨界點是54個村莊,模型B(代表平原)是42個。(第85頁及118頁注14)這裡,“新一輪基層市場中的第一個要在每個潛在區域都有了12個村莊時才會建立”,只是一種假設,如果村莊與市場之比在30左右時新的基層市場即開始建立,這一輪新市場開始時,每個新市場下屬的村莊就可能只有五六個甚至更少。
評價
對於施氏理論來說,一個市場區域包含四五個村莊到五六十個村莊的種種情形,都可以用一個市場含18個村莊的模型的密集循環過程來解釋,而無法用一個市場含6個村莊或36個村莊的模型來解釋。公正地說,村莊與市場之比
 施堅雅市場理論最受中國學者詬病的要數他的六邊形市場區域理論
施堅雅市場理論最受中國學者詬病的要數他的六邊形市場區域理論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說,這個模型看起來並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畢竟,中國很少能看到正六邊形的市場區域,而在村莊與市場之比問題上,施堅雅只知道一個村莊與市場之比超過50的實例(第118頁注14),王慶成先生的文章中,則舉出了數例包含90餘個村莊的集市和為數更多的一村集。其他地區說不定還會有更多有待發掘的史料,表現出與施氏理論差距甚大的情形。
然而,這裡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建立數學模型,利用抽象的模型方法研究歷史到底有沒有合理性。人們可以否認建立這類模型的必要性,畢竟,實證分析才是最可靠、最能說明問題的。也可以否認建立這類模型的可能性,因為中國現存史料中可供建立數學模型、進行數學分析的數據不夠多。但如果持這類觀點,與施堅雅之間就根本不存在對話的基礎,彼此的遊戲規則不同,完全沒有必要去進行任何爭論。如果承認數學模型、數理統計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數學方法作為分析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假定市場區域是圓形,無疑要比假定它是方形、三角形、菱形、平行四邊形或別的什麼形狀更為合理。事實上,有不少中國學者認為中國農村的市場區域基本上是圓形的。而當多個圓形擠在一起,互不重疊亦無空隙時,它們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正六邊形。既要建立數學模型,又糾纏於市場區域應該有幾條邊或幾個角,事實上並無多大意義。一個一個地描述具體的市場區域的形狀,對個案研究十分重要,但以此對施氏理論模型提出批評,沒有多大意義。
那么,這些工具到底有什麼用途呢,一般說來可以認為,研究現實經濟時使用的一切理論、方法和工具都可以用來研究經濟史,研究當代社會時使用的一切工具都可以用來研究社會史。其間的區別在於,為現實經濟建立數學模型,往往是利用大量的已知資料和數據模擬或預測一種經濟現象未來的發展趨勢,從而為經濟決策提供參考;而在歷史研究中建立模型,是為了解釋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有時是為了推算無法找到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