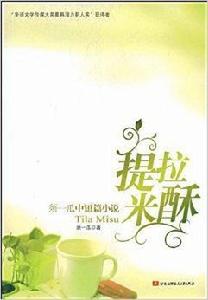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提拉米酥:須一瓜中短篇小說》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須一瓜,女,現居廈門。2001年起,陸續在《收穫》、《人民文學》、《十月》、《作家》、《上海文學》、《鐘山》《中國作家》、《小說界》等雜誌發表中短篇小說,作品多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作家文摘》、《新華文摘》等選載,獲2003年度“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著有《淡綠色月亮》、《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蛇宮》等小說集。
媒體推薦
我們以為我們終於碰到了一個小說家,她對人性中的光明抱有信念,但同時,我們發現,她目光銳利,她對死亡、對人的脆弱混亂有深入的興趣。她睜大眼睛注視著她的人物困惑、彷徨、絕望、受苦,她絕對不天真,偶爾,她也可以像法醫般超然無情。
在她看來,寫小說如同操刀——.她說的是手術刀,但我認為也是“庖丁解牛”的屠刀……她對人的複雜的具體境遇,對那些透露著人的紛亂、難以言表的內在生活的細節有驚人的敏感,她無疑比我們更聰明、更知道事情的真相和人的秘密。
對於這個時代的都市中的人性、人的感覺和經驗,對於這一切,我們其實還是所知甚少。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比須一瓜對此知道得更多。
須一瓜在“尾條新聞”和“頭條小說”之間的寫作是中國當代小說對於一個重要想像域的第一次自覺的勘探。
——李敬澤
她通過案件走進人們的心靈,而沒有糾纏於案件訴訟的破解.這是她小說成功的原因,也使她的寫作具有了獨特性。……在我看來,她是以一個“精神警察”的方式走進去的。
有時你會覺得她對道德追問得太苛刻,……這種推向極致的方式無疑使我們對人物的讀解更為豐富。另一方面,她也有她的道德原則。她以她的道德原則一遍遍地擦拭著她的小說世界,因此儘管她小說中的人物多半生活在惡濁的環境裡,但小說傳達出的精神卻像是擺在聖壇上的銀器錚亮明淨的。
——賀紹俊
圖書目錄
在水仙花心起舞
提拉米酥
穿過欲望的撒水車
淡綠色的月亮
老的人,黑的狗
第三棵樹是和平
雨把煙打濕了
有一種樹葉春天紅
城市親人
鴿子飛翔在眼睛深處
誠實的寫作都是霸道的——與須一瓜對話
文摘
在水仙花心起舞
一
阿丹是個輕度弱智。他哥哥說,政府檢測機構檢測報告單上,阿丹的智商指數是八十九分,就是說,差一分才跨進正常人智力指標。哥哥有時懷疑,有可能搞錯了,也許錯的還不止一分。你可以向過去的中山大道、現在的慧光大街打聽一下,一提起兄弟名剪城,不,不一定要提起名剪城,只要提說一個叫阿丹的,全城幾乎每個女人都知道那是個一流的美髮師。
其實阿丹已經四十多歲,但是,因為弱智,他的面貌一直都像三十左右。阿丹有著驚人的美貌,如果他低垂著眼帘專注地侍弄頭髮,或者戴著墨鏡,簡直找不出天下哪個男人比他更酷更有魅力。那些眼裡只有好萊塢男星的時尚女人,在阿丹面前,也難免手足無措。他的帥氣散發出金屬般的、女人難以躲避的光芒。只有你和他的眼眸對望的時候(阿丹幾乎不看人),你可能會因為它們過分的單純,感到無所適從而隱約失望。
但這並不妨礙阿丹、並不妨礙兄弟名剪城擁有一流的專業名望。慕名到那裡沒有預約的人,就像棲在兩大排沙發上的大鳥,一雙雙眼睛老跟著阿丹。阿丹是從來不理會店裡有多少客人的,他有可能在樓上睡覺,可能在剪髮廳那隻他專用的皮革舊沙發上。他可能在玩那把從小放在口袋裡的牙剪。那把鍍鎳脫落的牙剪,永不疲倦地在他手上飛速翻轉,每個指頭在兩個柄孔和剪口輾轉穿插;他也可能把那把牙剪藏在貼身口袋裡,而專心致志地看著美發廳一角糟糕的電視劇,有時笑得人仰馬翻,有時抽噎的動靜,電吹風都壓不掉;或者他只是安靜地在沙發上咬自己手指,他只咬右手虎口前段的食指側面,那裡的肉已經發紫隆起,因為從小到大,他都喜歡咬那塊肉。入睡的時候,他必須叼噙著那塊肉才能入睡。
十四歲之前,阿丹沒有得到那把牙剪之前,一直有傻瓜丹的外號。據說是3歲的時候,從窗台上摔裂了頭。阿丹也讀書,不愛說話,經常把同學名字叫錯,成績糟糕,但老師說他乖,就沒有讓他留級,反正那時候也無所謂讀書。
比阿丹大六歲的哥哥是通過一次次用針刺破手指,把微量的血擠到尿樣里,獲得腎病病歷證明而逃避農村插隊生活的。他躲在城裡,就學了理髮手藝。兩年後,廣交朋友的哥哥的美髮店小有名氣,但十四歲的阿丹偶然到哥哥店裡時,他哥哥的專業命運開始了徹底的改變。一開始,阿丹只是站在一邊,咬著自己的手指看。洗、吹、剪、燙、焗,什麼都看,看得很著迷,礙手礙腳的,碰來碰去的,正在操作的哥哥無數次地把他推開,但他一下子就忘了,又咬著手指靠近前來。他最喜歡看使用牙剪,也許那種剪了還有那么長,讓他感到驚奇有趣。哥哥就塞了一把牙剪給他,讓他走開。
從第一次走近哥哥店裡,阿丹再也不願意離開了。他感到沒有什麼地方比那裡更好玩了。阿丹還是什麼都看得眼珠子要掉下去,手裡還把玩那把牙剪;他也玩別的剪刀,或者蹲在地上剪掉在地上的頭髮。並不認識多少字,但是,阿丹能把髮型雜誌一看一整天。還有小工說他,一個上午,只看一個女人頭。一年後春節前的一天,因為太忙,哥哥對依然不識相的傻瓜丹氣急敗壞,狠狠把他湊近前來的頭打了一下。阿丹摸了摸頭,說,我做。
哥哥只想快點把這個二百五弟弟支開,掃了一眼等候的顧客,挑了一個看上去好說話的生客,說,把她頭髮吹吹乾。阿丹就過去了。忙得不可開交、又談笑風生的哥哥根本就把阿丹忘記了。一個多小時後,那個生客笑吟吟地過來交錢,做哥哥的大吃一驚。那女人完全換了一個人,一個刀法極其精緻的頭髮,剪制了一個非常少見的樣式,尤其是額前的層次清晰的斜發,處理得非常大膽別致。確實太合適那女人的臉型氣質了。女人一邊等找錢,一邊看著鏡子中的自己。那種滿足的、自己給自己的笑,哥哥太熟悉了,這是女人對髮型的最高褒評。留給你這樣一個笑臉的女人,一定就是你的回頭客了。
一個準確的髮型,能發掘一個女人百分之九十的美麗。哥哥突然悟出了書上這句話的經典意義。哥哥打量著又在咬手指的阿丹。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也許是憑著他的高大身材,也許憑著他的偶然發揮,贏得了意外的結果。但是,看來不只是哥哥的驚奇,哥哥手上正在做的女人,從圍裙下伸出食指說,我做她那個髮型合不合適呀?那些本來等候的客人,包括熟客,有兩個竟然起身悄悄過來對阿丹哥哥說,我時間比較緊,要不我的也讓你弟弟試試?
二
請阿丹做頭髮的女人都知道,阿丹不會馬上開剪,他經常是咬著自己的手指,上上下下地看,有時繞著被剪的人走,斜著眼睛環看理髮椅子上的女人。阿丹慢吞吞地走,女人們通常會忍俊不禁。阿丹哥哥會用手勢制止她們;然後,阿丹像陪女人照鏡子一樣,站在女人後面。一直盯著鏡子。然後,他會笑一笑,知道他習慣的人都會跟著笑笑;不知道而沒做出反應的,阿丹會再笑一笑。其他人就會提醒說,笑笑啊,他要看你合適的髮型呢。
一年後,也就是十六歲的阿丹,已經在美發界聲譽隆起。22歲的時候,他獲得了華東區第一屆的金剪刀獎,成為最年輕的獲獎者。這之後幾十年,只要是公平公正無需交納贊助費的美發大賽,阿丹總是赴賽必奪魁。八十年代後期起,這個海濱城市開始有模特大賽、精英大賽、選美大賽等區間賽什麼的,那時,兄弟名剪城幾乎被那些省內外慕名而來的佳麗們擠滿。
可是,二十七年前,也就是阿丹十六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這一件事,阿丹沒有和任何人說起,但他心裡永遠揣著它。阿丹哥哥直到阿丹死去,都沒明白怎么回事。阿丹臨死時,在他懷裡說,不種了。哥哥說,什麼不種了?阿丹說,水仙。不種了。
哥哥就點頭說好的。其實哥哥也不明白為什麼。他只知道,每年春節前種下五個精挑細選的水仙球,是弟弟從十七歲起就開始的習慣。有一年,有一球花蕾本來很多,不知為什麼患病,花蕾未放前全部蔫枯了。阿丹竟然有一周拒絕工作。後來母親發現他把那個早夭病死的水仙,連根帶葉地藏在枕頭底下。母親生氣地把那東西扔了。阿丹竟然蹲在空了的垃圾桶面前,孩子一樣哭泣了很久。大家知道傻瓜丹的智力底細,並沒有人見怪,也沒有人安慰他。
最後的遺言幾乎聽不見,阿丹哥哥把耳朵貼在弟弟流血的嘴邊。阿丹的聲音像風中的遊絲:不種了……
哥哥說,好。不種了。再也不種了。
三
距離當地六十公里有個大江南鋼鐵城。那裡完全是個獨立王國,六七萬人的大工廠里,工人上班、買菜、看電影、孩子上學——從幼稚園到高中,反正,那裡什麼都齊全。它就是一個功能完整的城市。在那個富饒的城中城裡,人們經常穿著統一的豆灰色咔嘰布工作服,有著比城外人更高的福利,比如分不停的凍豬腳豬排豬肚白糖綠豆水果,還有電影票、冰淇淋票、溜冰票。
阿丹的哥哥由於插隊結識了幾個幹部子弟,他們很快因為父母復官陸續上調,離開農村。阿丹哥哥只好通過小聰明,不斷地偽造腎出血證明,逃避農村。阿丹哥哥喜歡那些幹部子弟,儘管不在一個城市,他總會去找他們玩。在八十年代初,阿丹哥哥就算是憑手藝先富起來的人,人家一個月掙三四十元的時候,他有時半個月就掙一千多。但是,他把錢都慷慨地花在那個城市的幹部子弟們身上。他一出現在那個城市,就意味著免費的狂歡,所以,幹部子弟也真心和他成了好朋友。因為這樣的原因,他們帶他走進了那個鋼鐵城,走進了那些美麗動人的女演員間。
一個六七萬的大工廠,能進宣傳隊的都是頂尖的人物。如果不是容貌姿色過人,那必定有超群的技藝,最最不濟的要有後台。那批幾乎是半脫產的演員們,無論在鋼鐵城內城外,都是絕對的明星人物,尤其是女演員,分明就是城內外女人們的服飾髮型時尚指向標。只要是她們上身的,很快就會在鋼鐵城女工內流行起來,城外的女人就會學習,很快的城外的女人也就都流行開了。
阿丹哥哥基本是個風流倜儻好色之徒,手藝精,為人機靈慷慨。鋼鐵城女演員們很快就都把他定為自己的髮型師。女演員們本來和那些幹部弟子就是權勢與美貌相得益彰互相欣賞的關係,阿丹哥哥很自然就成了其中一員。他有時會買兩張火車票帶上阿丹,後來那邊的女人發現阿丹的手藝並不差,就會主動要求帶上阿丹。阿丹哥哥也樂意有個幫手,有時他在那裡和眾朋友通宵歌舞狂歡,阿丹在毫無怨言地勤奮工作,娛樂和賺錢都沒耽誤。
阿丹是討人喜歡的。那些生性浪漫輕狂的女演員們,一高興就摸拍少年阿丹漂亮的臉,髮型滿意了撲上來就死抱。阿丹的臉經常被她們弄得都是口紅。阿丹是羞怯的,漲紅著臉,假裝沒感覺地不斷玩手上的牙剪。有的女演員見狀,就刻意過來用肩頭撞他,一臉壞笑的猛烈撞他,阿丹被撞倒了,但坐在地上他也不停地翻轉手上的牙剪,目不斜視若無其事。人們就哄堂大笑。這個時候,總是阿丹哥哥哭笑不得又愛憐地把阿丹拉起來。
說不上是什麼複雜情感,未必是吃弟弟的醋,阿丹哥哥有時候就是覺得那些潑辣放浪的女演員會把阿丹給吃了。那時候,兄弟名剪城在當地已經是聲譽日隆,兄弟倆雙雙離開去鄰城工作嬉戲,已經不被本城女人們答應。慢慢的,阿丹哥哥把阿丹留在家裡的時候多了,由母親負責看店收費,加上僱傭的師傅配合阿丹,倒也撐得住幾日;再後來,那些幹部子弟下海的、出國的、發財的,那個固定團伙漸漸也散了,女演員們也在日益繁忙的個人生活中,黯淡了姿色,黯淡了扎堆的激情。不過,阿丹哥哥時不時還會過去,有時是某子弟結婚了,某女子小孩滿月了,某子弟回國了,某子弟出獄了。反正一年年友情還絲連著。阿丹是早就不再去了。
四
從十七歲的那個春節前,阿丹開始養五個水仙球。開始家人以為他是一時玩興,就按他的要求,買了五個荷葉造型的薄瓷白盆。阿丹哥哥還送了他一把雨花石。阿丹每天給五個水仙球澆水、曬太陽。那年冬天陰雨綿綿,天氣陰冷。人家說,你要是不澆熱水,春節開不了花呢。阿丹就小心翼翼地每天澆熱水,水溫都必須用溫度計試過溫,正好三十三度然後才澆;一聽說出太陽,扔下做了一半的顧客的頭,狂奔回家,把花盆一一抱到陽台太陽底下曬。
春節的時候,五盆水仙花都開始開了。家人以為可以每個房間分享一盆,客廳可以安排兩盆。不料,阿丹回來勃然大怒,把水仙花一盆盆都搶進自己臥房,還把門反鎖了。後來家人就看到,阿丹的桌上有兩盆,茶几上有一盆,還有兩盆竟然放在枕頭邊。母親趁他上班,趕緊把枕頭上一左一右的花盆移到桌上,但是,阿丹一回家,就怒不可遏地放回原處,而且因為憤怒手重,把花盆裡的水都振盪出來,結果,枕巾床單濕了一大片。母親只好在阿丹不在的時候,把花盆裡的水偷偷倒掉一些,以減少危險程度。而且倒水的時候千萬要注意,每一盆花每一天所處的位置不同,一旦放錯,阿丹一眼就看出。天知道,他是怎么區別那些幾乎一模一樣的水仙花。有年春節,因為家人不慎錯誤放置了水仙花盆,他打開煤氣灶,幾乎要放火燒掉自己的手。
事實上,家人的擔心是多餘的,二十多年來,和他同床共眠的水仙花,從來沒有灑出來過水。枕巾和床單總是潔白乾淨的,枕邊,水仙花總是鬱鬱蔥蔥,美麗的黃花清香陣陣。一年一季的水仙花花開花謝,阿丹都是安安靜靜地躺在它們中間,而且容易微笑,就是說,在每一個水仙花睜開眼睛的冬季,他總是在花叢中純潔地睡去,恬靜地醒來。每一個冬天,阿丹的頭髮和眼睛都充滿著水仙的芬芳。
雖說弱智,但阿丹有錢有貌,舉止又從不討人嫌棄,所以,看上阿丹的人家還不太少。家人怕阿丹被欺負,還挑了又挑,力圖找個智力正常的厚道人,好把阿丹一輩子託付給她。親戚所在的一個外省女孩,符合這個條件,眉眼也周正。人家只是家境太窮,才這樣選擇。沒想到,一到冬季,阿丹的枕頭邊雷打不動的水仙花,還是嚇跑了那個富有犧牲精神的厚道女孩。
序言
作為小說家的須一瓜是一個“好人”。“好人”的標誌是,她在總體上能夠與我們達成一致意見,這種一致意見涉及我們想像世界、認識生活的一系列基本範疇,比如:善、美、正義、忠誠、英勇、憐憫,等等。
也就是說,須一瓜無意冒犯我們,善、美、正義、忠誠、英勇、憐憫等等,也許我們做不到,也許我們其實並不十分清楚它們究竟意味著什麼,但是,對這些詞以及它們所指涉的價值我們懷有天然的、先驗的尊重,我們認為它們理應普照大地,就像我們知道有人逍遙法外,但我們的憤怒依然是出於對正義的信念。
須一瓜和我們分享著這些共同的基本信念。她是個有信念的小說家,她和我們達成一致並非出於策略、習慣,不是因為她要討好我們,而是她真的相信,實際上,她比我們更信,她幾乎是天真地信著,她的熱情感染著我們。
這是須一瓜和她同時代的很多小說家的重要區別。對人類生活中正面的、肯定性價值的發自內心的信奉,這是一種此時極為稀缺的品質。小說家們樂於表現得桀驁不馴、玩世不恭或者老奸巨猾,他們認為,和讀者一樣對生活存有樸素的信念是一件令人羞慚的事,這幾乎就等於愚蠢,而愚蠢不可饒恕,小說家們決心比我們更明察、更賊或者更無信念。
但須一瓜恰好又是一個明察的小說家。她的信念從未使她在想像人類事務時失去現實感,她說過,在她看來,寫小說如同操刀——她說的是手術刀,但我認為也是“庖丁解牛”的屠刀,堅定、冷靜、流暢,譁然響然,奏刀霍然,準確抵達一切部位,分開筋肉牽連的含混夾纏,她對人的複雜的具體境遇,對那些透露著人的紛亂、難以言表的內在生活的細節有驚人的敏感,她無疑比我們更聰明、更知道事情的真相和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