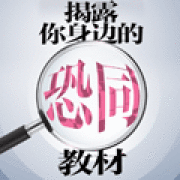由來
 淡藍開展“揭露你身邊的恐同教材”發布活動
淡藍開展“揭露你身邊的恐同教材”發布活動內容爭議
在一本名為《生命教育》的讀物中,同性戀被定義為“不正常的性傾向”,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教育部下屬的專業基礎教材出版機構。這本在遼寧省多所高中使用的教材中說,“我國仍將同性戀列入‘中國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CCMD-2-R·1995)’的規定之中”,但事實上,中國早在2001年就從上述標準中刪除了“同性戀”詞條。
淡藍網負責人耿樂認為“中學是青少年形成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時期,此類觀念只會帶來誤導作用。”
浙江杭州的LGBT權益人士姚煌(YaoHuang,音譯)指出,教材里的這些觀點會阻礙青少年了解自己的身份,對他們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不健康影響。同時,這些觀念在年輕的學生們之間傳播,可能會導致校園內出現欺凌行為。
總部位於北京的LGBT非政府組織“愛白文化教育中心”2014年對420多名青少年展開調查,80%受訪者是同性戀或雙性戀人士。調查報告顯示,約77%的受訪者曾遭到基於性別和性傾向的欺凌,最常見的形式是言語攻擊,有些人甚至遭到人身攻擊。
權益人士普遍認為,書籍作者們極少更新相關知識是導致教科書充斥偏見的主要原因。“這是事實,許多教材的出版只是為了敷衍上級教育部門的指標,並不會認真對待。”被人們稱為“同志哥”的姚煌說。
這種現象也是現實的寫照,許多學術成果都基於相互“引用”,有時甚至直接抄襲。
引起爭議的《青少年心理學》的主編之一李力紅承認該書相對比較過時,但這位心理學家強調,關於同性戀的那部分內容並不是她撰寫的。“所有知識都應該按照國家發展的需求進行更新。教育工作者必須不斷地在教學過程中吸收新的觀點。”李力紅說,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同性戀不應該被視為性變態。
呼籲行動
 5月17日,活動家們在長沙參加同性戀者反歧視活動
5月17日,活動家們在長沙參加同性戀者反歧視活動2014年8月,杭州權益人士在這方面的努力獲得廣泛關注。一本由杭州教育部門編寫的性教育讀物被指污名化同性戀者,引起許多家長和權益人士的強烈不滿。這本面向學生和家長免費發放的讀物中說,同性戀與社會風俗道德相悖逆,屬於性偏離中的一種。該書還宣稱青春期應該禁慾及避免自慰。
閱讀了這些內容後,大約20名同性戀青少年的家長聯署發表反歧視公開信,要求出版方更正這本書的相關內容。姚煌與當地的另一名權益人士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他們一起面見了負責編撰這本書的杭州知名教育家韓似萍女士。
姚煌明確表達自己的看法並指出書中不恰當的性學觀念。經過兩個多小時的交流,韓女士承認書中部分內容存在爭議,並承諾再版時會作出相應修訂。他們的交流似乎很順利,此前在雲南出席性教育工作會議的一些性學專家也對這本教材表示質疑。姚煌說:“在溝通方式上,我們希望以理服人,而不是‘對抗’。”在他們的交流過程中,姚煌出示了大量資料,包括來自國外的有關LGBT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論。雖然這表明人們正在爭取用更多樣化的方式來消除針對LGBT群體的歧視,但他們仍面臨無法預料的挑戰。
2015年5月17日,大陸同性戀者反歧視活動在湖南長沙舉行,事後負責組織活動的19歲男同性戀者被長沙警方逮捕並拘留12天,此事引發大量爭議。
事實上,儘管公眾要求改善性教育的呼聲越來越多,但性教育在中國仍處於尷尬境地。主管教育工作的上級機構既沒有出台強制性規定,也沒有通過統一的教材來解決這個問題。此類性質的教育內容似乎都處於實驗階段,沒有統一的標準,但大部分都偏向於“壓制”同性戀傾向。事實上,教育工作者中很少有人意識到傳授多元性別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他們往往發現這方面的討論和研究面臨各種形式的阻力,仍處於在夾縫中生存的狀態。
負責講授性別人類學的廈門大學副教授林紅曾於2014年申請性別多樣性研究項目資金,卻被教育部拒絕。據《南方都市報》報導,她於2008年和2009年兩次嘗試將性別平等教育納入大學通識課程,但相關申報都沒有成功。
相關事件
2015年8月27日,據媒體報導,化名秋白的大學女生參與反“恐同教材”維權後,8月18日,學院將“某高校一女同性戀者起訴教育部”的新聞轉發給了她的父母,導致其被迫出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