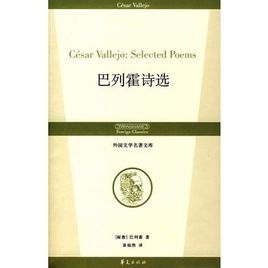簡介
巴列霍的詩是不折不扣的痛苦的詩篇,詩歌史上恐怕極少有詩人像他這樣在詩中如此高密度地使用“痛苦”這個詞。他的少作詩集《黑色騎手》的標題詩首句便是:“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擊——我不知道緣由!”這句話如同讖語高掛在他人生之途的起點。而後“痛苦”在他的詩中隨處可見:“這個旅行者給了我多么奇怪的痛苦!”(《蜘蛛》)“痛苦的穿越,它背後好像拉著/一車被束縛的禁慾的感覺!”(《我們每天的麵包》)“如果他身上有多么痛苦,我肯定就是那痛苦。”(《遙遠的腳步》)“廚房就是黑暗,愛就是痛苦。”(《我剛獨自吃過午餐》)登峰造極的是那首談希望的詩《我要談談希望》,可謂滿篇皆痛苦,起首即是:“我不是以塞薩爾·巴列霍遭受這痛苦。”結尾還是:“今天我只是痛苦。”痛苦的詩人不在少數,但在詩篇中如此直接書寫痛苦則是異乎尋常的。
巴列霍所遵循的創作原則是精神和感官的強度。不用說這是一種古老的詩觀,可是許多時候所謂“創新”不正是復甦某種被淡忘的重要原則嗎?淡忘的原因則是因為小詩人們太容易迷失在詩歌技術的小道了,往往被細枝末節一再遮蔽視野。只有強力詩人才能抓住詩藝的關鍵所在,在巴列霍看來情感強度決定著一首詩的成色,而不是精明的批評家們開出的一副副靈丹妙藥。強烈的情感猶如耀眼的光束投射在尋常的物件上,讓它們自動產生濃烈的詩意,而不是像許多次要詩人那樣去搜腸刮肚地攫取。同時這也是巴列霍敢於在詩中粗率地使用語言的內在原因,他不僅毫無顧及地書寫許多“訓練有素”的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痛苦”、“失望”、“悲傷”等辭彙,而且還大量使用直接的口語、排比、反覆等貌似“老土”的手段。
就像無數次寫到痛苦一樣,巴列霍也無數次寫到了死亡,在這些詩篇中有兩首我以為是感人至深的。一首是他早期作品,第一本詩集《黑色騎手》里的《給我的兄弟米格爾》,一首是他逝世前一年寫的《民眾》。前者寫他早逝的哥哥米格爾,寫法樸實而巧妙,先是寫實地敘述少年時代和哥哥玩捉迷藏的遊戲,“後來,你藏起來,而我找不到你。”“我們都嚇哭了。”最後則是:“聽著,兄弟,不要遲遲不出來。好嗎?媽媽會擔心。”這樣的結尾讓人心碎。《民眾》更簡單,寫的是西班牙內戰中戰死的共和派士兵,許多人走過來對他說:“不要死,活過來。”最後奇蹟發生,“那個屍體悲哀地望著他們,/深受感動,/他慢慢坐起來,/擁抱那第一個人,開始走路……”在這裡巴列霍行使了詩人的特權——起死回生之術。這種復活蘊含著巨大的情感力量,妄想第一次具備了正面的催人淚下的含義。三十年代正是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巴列霍在巴黎結識了不少超現實主義詩人和畫家,但是和超現實詩人們通常從抽象的美的角度,扭曲現實意象不同,在《民眾》中,巴列霍的“回生術”簡單樸實充滿人性的力量,和當時不少超現實主義詩人華麗而空洞的詩作毫不相干。
巴列霍總體而言是囈語式的詩人,他在詩歌寫作中期的語言實驗充分表明了這一點,那些大膽的別出心裁的語言組合(老實說,有些地方的確顯得生硬不自然),說明巴列霍的主要精力放在探索詩歌可能達到的深度上,而對和讀者的交流巴列霍並不在意。可是當他順應三十年代社會思潮,轉入左翼陣營(兩次訪問莫斯科,並在1931年正式加入共產黨,實事求是地說,他的左傾非常自然,首先他是真正的無產者,而且早期左派的確具有極高的道德抱負),他如何用詩歌去完成共產主義的主張,就變得格外讓人好奇。他給出的答案是像《憤怒把一個男人搗碎成很多男孩》、《讓百萬富翁赤裸裸走路,一絲不掛!》、《有些日子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政治需要》、《西班牙,我喝不下這杯苦酒》等一系列優秀的詩篇。他沒有為了政治目的降低詩歌的要求,相反他的政治態度強化了他的詩歌人性的廣度和深度,和早期詩作相比,巴列霍晚期詩作自有一種無可替代的悲憫,而且這悲憫隱藏在詩歌的律法下,從而避免墮落為某種令人生厭的姿態,這姿態曾經污染過多少優秀的左派詩人呵,從馬雅可夫斯基到阿拉貢到聶魯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