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威廉·燕卜遜
威廉·燕卜遜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年9月27日生於英格蘭約克郡,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詩人。他的成名作為《朦朧的七種類型》。他是20世紀40年代以後中國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國現代派詩歌的一代宗師。曾任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英國文學教授,北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編輯,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英國文學教授。1984年4月15日去世,享年77歲。
生平
學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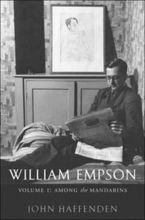 威廉·燕卜遜
威廉·燕卜遜1925年,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入劍橋大學的瑪德琳學院念數學,並開始以劇作家和詩人揚名。1926年,在當時劍橋的學生文學期刊上發表評論,他認為其關於著作、戲劇與電影“草率而尖刻”的評論成為了他批評思想快速成熟的一個重要階段。
1928年,與他人共同創辦《實驗》雜誌,力圖將藝術實驗、哲學實驗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結果被斥為“聰明的年輕人可悲地盡講廢話”。在本科期間,燕卜蓀用自己的話說,沉湎於“讓人頭暈的誇誇其談”,其詩歌創作是“孤獨與受難”的產物。
1930年,燕卜蓀在劍橋大學由數學專業轉讀文學專業時,曾師從大名鼎鼎的文學理論家I.A.瑞恰慈。作為學生的燕卜蓀,在瑞恰慈給他批改的一份作業中得到啟示,寫出了震驚現代西方文學界影響久遠的著作《朦朧的七種類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該書改變了整個現代詩的歷史,也開創了“細讀”批評範例。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學的文學系,依然鼓勵學生作細讀分析。美國文學批評家蘭色姆認為:“沒有一個批評家讀此書後還能依然故我。”有人甚至說,西方文學應分成“前燕卜蓀(Pre-Empsonian)時期”和“後燕卜蓀(Post-Empsonian)時期”。
後來,劍橋校方因為在燕卜蓀抽屜里發現了保險套,取消燕卜蓀教席。此事使他的導師瑞恰慈極為震怒,只能勸燕卜蓀離開英國到遠東去。
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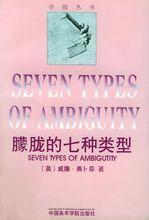 威廉·燕卜遜著作
威廉·燕卜遜著作1934年契約期滿不再續約,他回到故地布魯斯伯里,過著清貧、散逸的生活。
1937年,燕卜蓀乘坐跨西伯利亞列車來到中國,此時北京大學已南遷。他隨當時在中國推廣“基本英語”的瑞恰慈夫婦乘船去了香港,隨後到中國內地邊走邊聊。當時三校在長沙、衡山建立臨時大學,燕卜蓀來到這裡報到,並著有長詩《南嶽之秋》。他關於中國的詩還有《中國》、《中國謠曲》等四首。1938年,他隨學校繼續南遷到昆明,並開講英國現代詩——奧登的《西班牙》。1937年-1939年,燕卜蓀先後在北京大學西語系和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授,講授英國文學。 “燕卜蓀”是他為自己取的一個中國名字。在這期間,燕卜蓀開始寫作後來成為他最偉大著作的論文集《複雜詞的結構》,他講授的英國當代詩歌對中國20世紀四十年代現代主義在昆明的興起影響巨大。
往返中英
1939年1月,燕卜蓀從中國返回英國,正趕上一場戰爭。由於近視,他未能入伍。很快,燕卜蓀就在英國廣播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任該公司中文部編輯。但他其實並不喜歡這個工作。戰後,他舉家(已有妻兒)來到北京大學教書。1952年回英後進入“外省”的一個較國小校謝菲爾德大學擔任英文系主任,直至退休。
1983年9月,巫寧坤教授有機會到英國訪問77歲高齡已經退休的燕卜蓀,細數聯大北大同事別後的坎坷生平,感慨萬端。巫寧坤邀請燕卜蓀重訪北京,而且‘不必演講’。不料燕卜蓀回答說:“我喜歡演講!”可惜,這個在中國演講了半輩子的20世紀大學者,第二年就去世了。”
大事年表
1906年9月27日生於約克郡。
1920年入溫徹斯特學院學習。
 威廉·燕卜遜
威廉·燕卜遜1925年進劍橋大學攻讀數學,後改讀英國文學。
1930年出版《朦朧的七種類型》。這是他的成名之作。
1931年至1934年任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英國文學教授。
1937年來中國,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平津淪陷後,燕卜蓀隨北大、清華、南開師生向南方撤退,先到長沙,後又遷到昆明。
1940年返回英國。
1941-1946年任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編輯。
1953年起任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英國文學教授。
1971年退休。
1984年4月15日去世,享年77歲。
主要著作
| 《朦朧的七種類型》(1930) | 《田園詩的幾種形式》(1935) |
| 《複合詞的結構》(1951) | 《詩集》(1955 ) |
| 《密爾頓的上帝》(1961) | 《柯勒律治詩選》(1972,與皮利合編) |
| 《使用傳記》(1984) |
潛心教學
教學方式
燕卜蓀先生在北大教書期間開過許多門課程,其中有十七世紀英詩、英詩概觀、現代英詩、英國散文演變等選修課。理論文寫作則是西語系大四學生的一門必修課,由教師指定閱讀的文章,讓學生寫出評論。燕卜蓀先生對學生的每篇文章都詳細批改,批語有的寫在行間空地,有的寫在頁邊。其中既有觀點上的辨析商榷,也有語言上的錯誤改正。不過最精彩的還是他給每篇作文所下的總評語。往往是三兩句話,切中要害,文章的優缺點赫然在目,讓你折服。其精到處為一般教授所不及。他在批改時當然也不忘記鼓勵學生,如發現好的句子便寫上“This is good English ”,“This is vigrous writing ”和“very graceful English ”等等鼓勵的話。
教學特點
燕卜蓀先生每次上課只帶要講的原文文本,至於他的講課內容,即要在黑板上寫的東西,卻隻字不帶,而是即時在黑板上奮筆疾書寫下的。等到寫滿黑板後,他稍事停頓,只輕輕念一遍,便擦掉再繼續寫下去。中間從未有間斷停頓的時候。看上去他講課像是完全憑著才氣,即時發揮,其實是事先早有充分準備。他在授課時所表現的思路之敏捷、清晰和記憶力之強,堪稱一絕。
燕卜蓀先生在講課中從不重複權威的看法,很少援引旁人的觀點,講的話往往都是自己的真知灼見,難得從一般的書本中找到。舉例說,他認為T.S.愛略特對龐德的推崇超過了正當的評價,實屬過譽。他對於T.S.受略特的後期詩作《四個四重奏》評價不高,認為失之於空洞。這與一般美國批評家將該詩捧到天上的作法大不相同。他也鼓勵學生對詩歌要有自己的感受和見解,不要人云亦云,甚至有時要提出與教師不同的看法。
名作流派評價
1930年,燕卜蓀早年的成名之作《七種歧義類型》將他的導師李恰慈倡導的文學批評中的語義分析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推動了美國新批評運動的興起。他的這部早年著作被新批評派視為經典,競相效法。美國新批評家克林思·布魯克斯?Clean Brooks?隨後便標榜出“悖論”和“反諷”的說法。他在《精製的瓮》一書中根據這一理論細緻分析了華茲華斯、濟慈、丁尼生等人的詩歌,從而證實語義分析的方法不僅適用於玄學派詩人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如燕卜蓀所做的工作?,而且適用於一般認為比較易讀的詩歌作品。此外蘭色姆John Crow Ransom還提出了“結構與肌理”說。維姆扎特?Willam K.Wimsatt Jr.?,則倡導“具體的共相”的理論。這些說法都是想標明詩歌語言的特性,不過各有其不同的側重方面,在四十年代顯得異彩紛呈,蔚為大觀,形成新批評派的極盛時期。這些新批評派人物對詩歌語言的細緻分析與燕卜蓀走的路子基本上是一致的。不過他對美國新批評派代表人物的評價一般並不很高,認為他們沒有做出真正有創造性的成就。在美國當代批評家當中,肯尼思·博克Kenneth Brurke算是他最讚賞的一位。維姆扎特和比爾茲利Monrot Beardsley提出“意圖的謬誤”itentional fallacy的觀點,將作者的意圖與作品的意義完全分離開來,目的是強調作品文本的獨立性。這一觀點是燕卜蓀所極力反對的。無怪乎當代英國批評家科默德F.Kermode稱燕卜蓀是一個意圖主義者。另外,由於新批評派將詩歌作品當作獨立自足的實體,所以只注重文本上的細讀,而忽視作家個人經歷與社會背景對作品的關係。燕卜蓀的作法卻與此迥然不同。例如他在講莎士比亞時就詳細闡述了伊莉莎白時代的歷史背景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神視野或世界圖像。4、偏好作品: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 他特別推薦中國學生去讀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而不鼓勵閱讀霍桑和所謂高雅的亨利·詹姆士的作品。這也可以看出他的趣味標準與當時流行的學院派風尚的不同。
燕卜蓀先生在1950-1951年講授現代英詩,當時選修這門課程的只有金髮燊學長、李修國和我三個人。燕師?這是發燊學長和我對他的尊稱?本人就是一位重要的英國現代詩人,自然也要選讀兩三首。他說自己的詩常常被人認為晦奧難懂,實則一旦理解了其關鍵寓意,並非深不可測云云。這門課程講了一年,從哈代、葉芝、愛略特一直講到迪蘭·托馬斯Dylan Thomas,其中自然也包括與他同時期的奧登、斯本德等詩人,講起來更是如數家珍。課程內容非常豐富,囊括了英詩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演變概況。
燕卜蓀先生雖然早在二十四歲時,1930年就在英美批評界有了很高的聲譽,但他對自己的成就仍然抱著很謙虛的態度,曾說自己的文學批評範圍過於狹窄,遠遠不及他最欽佩的英國莎士比亞批評家A .C布拉德雷。他認為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亞悲劇》一書在卷帙浩繁的莎士比亞評論中是惟一值得一讀的著作。他也從不囿於一家之言,而是樂於介紹別人的觀點,舉例說他就曾將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udwell的《幻象與實在》介紹給中國學生。
教育風格
燕師對待中國學生總是循循善誘,充滿友愛之情。學生一到他家,他都是熱情接待,讓你坐下喝茶交談。有的學生準備寫論文,他便親自去圖書館替學生找出有關書籍,給予指導。有一年暑期他去美國講學,回來時帶來一些新書,往往自己還未看完,便很大方地借給來訪的朋友或學生先看。凡是認識他的人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般大學教授常有的學者架子。他待人的態度竟是出乎尋常的平易和親切。最可貴的是,這種待人的熱忱看來並不是修養的結果,而是他純樸真誠性格的自然流露。可以說,在他身上辨析入微的思考能力與率真的赤子之心奇妙地結合成了他獨一無二的人格風采,這正是每個認識他的人所無法忘記的生活中的燕卜蓀。
文學影響
燕卜蓀是“超前式”的詩人和新銳的批評家。他來中國的時候剛過三十歲,風華正茂,跟著臨時大學(後來的西南聯合大學)到長沙、南嶽、蒙自、昆明,同中國師生打成一片,·彼此極為相得,當時寫了一首題名《南嶽之秋》的長詩,其中說:“我交了一批好朋友。”
中國新詩也恰好到了一個轉折點。西南聯大的青年詩人們不滿足於“新月派”那樣的缺乏靈魂上大起大落的後浪漫主義;他們跟著燕卜蓀讀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讀奧登的《西班牙》和寫於中國戰場的十四行,又讀狄侖 ·托瑪斯的“神啟式”詩,他們的眼睛打開了一一原來可以有這樣的新題材和新寫法!
其結果是,他們開始有了“當代的敏感”,只不過它是結合著強烈的中國現實感而來,因為戰局在逆轉,物價在飛漲,生活是越來越困難了。他們寫的,離不開這些—儘管是用了新寫法。與中國現實的密切結合,正是四十年代昆明現代派的一大特色。在燕卜蓀的影響下,一群詩人和一整代英國文學學者成長起來了。
人物評論
燕卜蓀一生詩作不多,1955年出版的詩作合集僅收詩50餘首。這些詩受玄學派和T.S.艾略特的影響,以嚴謹的古典形式反映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困惑和內心痛苦。
燕卜蓀天分和才情極高,1930年就發表了文藝理論專著《朦朧的七種類型》。他在劍橋曾拿下數學和英文兩個第一,他是從數學後轉到文學上來的,是劍橋著名文學理論家瑞恰慈的高足。
其詩歌創作是“孤獨與受難”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