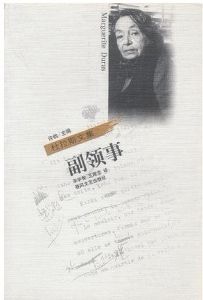內容簡介
 副領事
副領事故事發生在恆河岸邊:法國駐拉合爾的副領事深更夜朝鄰家花園開槍殺了人,他站在寓所的陽台上,向著拉合爾吼叫;在恆河岸邊,遊蕩著一個禿頭瘋姑,她常常夜半歌唱;大使夫人是加爾各答最優秀的女人,然而,她卻和幾個英國男人出沒藍月亮妓院。孤獨的副領事卻瘋狂地愛上了大使夫人。愛情聖手杜拉斯以悽美的文字寫出了又一段不可能的絕望愛情。
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法國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出生於印度支那,十八歲後回法國定居。她以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贏得國際聲譽,以小說《情人》(1984年)獲得當年龔古爾文學獎。
書摘
她走著,彼得•摩根寫道。
怎樣才能回不去呢?應該讓自己迷失。我不明白。你會明白的。我需要一個指示,好讓自己迷失。應該義無反顧,想辦法讓自己辨認不出任何熟悉的東西,邁步走向那最為險惡的天際,那種遼闊無邊的沼澤地里,數不盡的斜坡莫名其妙地縱橫交錯。
她正在這么做。她一連走了很多天,沿著斜坡走,又背向而去,涉水過河,徑直向前,轉向更遠的沼澤,又邁步走向更為遙遠的其他沼澤。
腳下還是洞里薩平原,她還認得出。
要知道,吸引你前行的天際或許不是最為險惡的,儘管會讓人產生這樣的想法;讓人根本意想不到的天際,才是最為險惡的所在。
低著頭,她向著險惡的天際走去,低著頭:她認出了泥沙里的貝殼,它們還是洞里薩湖的貝殼。
應該堅持下去,直到排斥你的東西最後轉過來吸引你,這是她所理解的母親將她逐出家門時說的那番話。她堅持著,她相信那番話,她走起來,她泄氣了:我還太小,我還是要回來的。如果你回來,母親說,我就在你的米飯里放上毒藥,毒死你。
她低著頭走著,走著。她很有力量,飢餓也同樣有力量。她徘徊在洞里薩平原,那裡天地相連形成一條直線,她漫無目的地走著。她停下來,又走起來,頭上頂著碗,又走起來。
飢餓和行走在洞里薩的大地上生根,播種,繁衍出更為遼遠的飢餓和行走。向前走已經不再有什麼意義。睡夢中,母親手中拿著一根棍子,看著她:明天一早太陽一出來,就給我滾,你這個大了肚子一輩子也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我還要照顧那些剩下的孩子,他們有朝一日也要離開家門……給我滾得遠遠的……無論有什麼情況都不要回來……無論什麼情況……滾得遠遠的,遠到我完全想像不出你所到達的地方……給你的母親下跪,然後滾開。
父親對她說過:如果我沒有記錯,我還有個堂兄在九龍江平原,他家孩子不太多,他也許能收留你做個丫鬟。她還沒有問九龍江平原在什麼方向。雨天天在下。天空布滿烏雲,不停地向北方翻滾著。洞里薩湖在漲水,帆船在大湖中前行。只有在雨後轉晴的間隙,才能從湖的這一岸看到對岸:水天相連之際,有一排藍色的棕櫚樹。
離開家這一路上,她一直都看得見湖的對岸。她從來沒有到過那裡。如果到了對岸,她是不是就開始迷失?不會的,因為從對岸她還能看到此岸,她出生的地方。洞里薩湖水面平靜,暗流潛涌,水色凝重昏暗,令人望而生畏。
她不再看湖了。她又來到一片斜坡縱橫交錯空曠奇異的沼澤地。此刻那裡空無一人。一切都沉寂不動。她走到空曠的沼澤地的另一邊,身後是一條鐵軌,暴雨過後閃出熠熠的光輝。她看見似乎有活物穿過。
某天早晨,一條河流橫在她的面前。河道有種令人心安的走勢,徐緩沉靜。她父親有一次說過,如果沿著洞里薩湖走,就永遠不會迷路,遲早會看到岸邊洗澡的人;他還說洞里薩湖就像個淡水的海洋,這個國家的孩子們之所以能活下來,多虧了湖水裡有那么多的魚類。她走著。她逆流而上走了三天,來到了大河面前,心想到了河的盡頭她就到了北方,大湖的北方。她會面對著大湖停下來,留在那裡。歇息的時候,她打量著自己的一雙大腳,腳底已經感覺不到橡膠鞋底的存在,她不由得揉搓起來。鞋裡有青青的稻粒,還有一束束芒果樹和香蕉樹的枝葉。她一連走了六天。
她停下來。在大河擋住去路之前,她為了尋找北方一直沿著河走,她是不是走過了頭昵?她繼續沿著河走,緊貼著蜿蜒的河流,晚問有時也在河中游上一程。她又走起來,她在看:對岸的水牛是不是比其他地方的水牛更矮壯些?她停下來。孩子在她的肚子裡攪動不停:就像魚兒在她肚子裡打架,那惱人的孩子自顧自悶聲快活地玩耍著。
她問昭:九龍江平原在哪個方向?她想,如果她知道是在哪個方向,她會走向相反的方向。她尋求著讓自己迷失的另一種方式:往北而行,越過她的村莊,然後就是暹羅山,在到達暹羅山之前停下來。到了北方不再有河流,我就可以擺脫沿河而行的習慣,在還沒到達暹羅山之前,我就選定一個地方留下來。她看見南方消融在大海里,而北方則安然不動。
沒有人知道九龍江平原在什麼方向。她走著。洞里薩湖發源於北方,所有注入湖中的河流也是如此。這些河流聚攏一處,看起來像一頭長髮,披著長發的頭頂朝向南方。應該順勢來到頭頂,直到盡頭,從那裡向南看,包括家鄉的村莊在內,眼前一望無際。那些矮壯的水牛,那些粉紅色的石頭,有時大塊大塊地堆在稻田裡,這些不同之處意味著方向沒有錯。她覺得,先前圍著她的村莊打轉已經結束了,最初的方向是錯的,第一步就錯了。她心想:這回我走對了,我選擇去北方。
實際上她走錯了。她選擇了沿菩薩河逆流而上,可菩薩河起源於豆蔻山脈,在南方。她望著天邊的群山,問人那是不是暹羅山。人們告訴她那是相反的方向,這是高棉。她大白天在一個香蕉園裡睡著了。
飢餓難耐,大山的陌生並不要緊,它催人慾睡。飢餓比大山更有作用,她開始睡覺。她睡著了。她睡醒起身。她上路,有時朝著群山走去,如同向著北方走去。她又
睡了。
她找吃的。她睡。她不再像在洞里薩的時候那樣走路了,她步履艱難,忽左忽右。她繞過一個小城,人們告訴她說那是菩薩城。過了菩薩城的那個地方,她往前又走了一段,踉蹌而行,差不多是直行著,朝群山走去。她從來不問洞里薩湖在哪裡,哪個方向。她認為,關於這個方向,洞里薩的方向,人們不會跟她說實話。
她路過一個廢棄的採石洞,她走進去,睡下。這是菩薩城的周邊地區。走進採石洞,她看到一些棚頂。有一次,她大概走了兩個月,這一次她不清楚了。在菩薩城一帶,被趕出家門的婦女、老人、瘋瘋傻傻的人數以千計。他們彼此擦肩而過,尋找吃食,互不搭話。大自然啊,給我一點吃的吧。有水果,泥巴,彩色的石頭。她還沒有掌握去捕捉靠著水岸打盹的魚兒的竅門。她母親曾對她說:吃吧,吃吧,到時候不用惦記你母親,吃吧,吃吧。午休的時辰,她一直在找吃食。平原啊,給我點兒東西嚼嚼吧。她去採集果子,野香蕉,稻穀,芒果,她將這些東西帶回採石洞吃。她咀嚼著稻穀,吞咽著溫熱香甜的果漿。她睡了。稻穀,芒果,是需要的。她睡了。她醒轉過來,看著四周。除了採石洞右側高聳的菩薩城,就是天地之間她那青春的直線。其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都沒有可是一切都蠢蠢欲動。在洞里薩也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在來到這裡之前,她對此卻很茫然。採石洞左側是豆蔻山,上面是參天大樹,地上是紅白相間的大坑,聲音就是從那裡傳來的,有帶鏈條的機器的聲響,有重物墜落的悶響,也有大坑周圍的男人們的叫喊。有多長時間了?
這豆蔻山,身前身後的山,有多長時間了?這條河,雨後溢滿泥水的河,有多長時問了?是這條河,又一條河,一直把她帶到這裡的。
肚子愈來愈鼓。撐起了她要一天天往上提的裙子,她現在走路時雙膝外露。在陌生的國度,她的肚子就像細小的穀粒,長在石頭問溫熱輕柔,令人想到某種要放到口中的食物。天經常下雨。雨後飢餓愈加強烈。肚子裡的孩子什麼都吃,稻穀,芒果。真正陌生的,是食物愈見缺乏。
她醒了,來到外面,開始在採石洞周圍徘徊,就像此前在洞里薩北面徘徊一樣。路上,她遇到一個人,打聽九龍江平原的方向。那人不清楚,人家不想回答。她繼續打聽。每被人回絕一次,那個方向就更擁堵一些,凝固下來。但有一次,一位老者回答了她。九龍江平原嗎?應該順著湄公河往下走,大概是這樣。可是,湄公河在哪裡呢?應該沿著菩薩河順流而下,一直到洞里薩湖,到了洞里薩湖繼續順流而下,應該是這樣的。河水都是流向大海的,從來如此,到處都是這樣,水鄉澤國的九龍江平原就在大海那邊。那么,在您看來,如果沿著菩薩河逆流而上呢?恐怕就要碰到難以逾越的高山了。高山後面呢?聽說是暹羅灣。我要是你的話,孩子,我就往南去,在那邊據說上帝也更和善。
她現在清楚了洞里薩湖的方向,也知道了自己處在它的什麼方位。
她在離菩薩城不遠的那個採石洞又停留一陣。
她走出採石洞。當她停步在單獨的茅舍而不是村里那種成排的茅舍前時,她就會被人趕走。當她與單獨的茅舍保持一段距離等待在門外時,過一會兒也會被趕走,進了村子情況也是這樣。她在河邊的竹林里等待,她悄然無蹤地穿過村莊,與別的女乞丐沒什麼兩樣。她們混進集市里,與賣魚湯的小販擦肩而過,她們打量著肉案上油光發亮的豬肉,成群的綠頭蒼蠅也和她們一樣打量著豬肉,但它們離得更近。碰到老太太或者賣魚湯的,她每次都要一碗米飯。她什麼都要,米飯,豬骨頭,魚,那種死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