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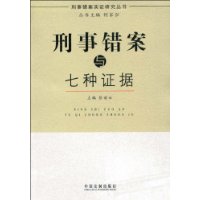 刑事錯案與七種證據
刑事錯案與七種證據《刑事錯案與七種證據》中從語詞含義的角度來說,刑事錯案應該包括兩種基本類型,其一是把無罪者判為有罪,可以簡稱為“錯判”;其二是把有罪者判為無罪,可以簡稱為“錯放”。它們都是刑事訴訟過程中就案件事實問題做出的錯誤裁判,但本課題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第一種類型的錯案,即錯判。這類刑事錯案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它不僅損害個人利益,使當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損害公共利益,破壞司法公正和社會秩序,甚至會使公眾喪失對司法的信念乃至國家政府的信念!在當下中國,刑事錯案的發現和糾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例如,杜培武的錯案得以糾正是因為偶然地發現了真正的兇手;佘祥林的冤案得以平反是因為當年的“被害人”意外的生還。刑事司法出現錯案在所難免,但關鍵是我們能否建立發現錯案和糾正錯案的有效機制。雖然我們有上訪制度,有控告申訴部門,但是錯案的發現和糾正依舊非常困難。這裡有來自很多方面的阻力,例如地方政府阻力和原司法偵查機關的阻力。其實,有些錯案辦案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或結案之後就已經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了,但是卻不願意改正,似乎有騎虎難下之苦,只好掩蓋錯誤甚至堅持錯誤,結果是錯上加錯。
圖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刑事錯案的基本問題
第二節 刑事錯案產生的原因
第三節 證據與刑事錯案的關係
第四節 “證據與刑事錯案的關係”問卷調查
第二章 物證與刑事錯案
第一節 從“李化偉案”談起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第三節 物證運用中導致刑事錯案的因素
第四節 物證運用中刑事錯案的預防
第三章 證人證言與刑事錯案
第一節 從“張海生案”談起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第三節 證人證言運用中導致刑事錯案的因素
第四節 證人證言運用中刑事錯案的預防
第四章 被害人陳述與刑事錯案
第一節 從“張金波案”談起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第三節 被害人陳述運用中導致刑事錯案的因素
第四節 被害人陳述運用中刑事錯案的預防
第五章 被告人口供與刑事錯案
第一節 從“佘祥林案”等說起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第三節 被告人口供運用中導致刑事錯案的因素
第四節 被告人口供運用中刑事錯案的預防
第六章 鑑定結論與刑事錯案
第一節 從“李逢春案”談起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第三節 鑑定結論運用中導致刑事錯案的因素
第四節 鑑定結論運用中刑事錯案的預防
第七章 勘驗、檢查筆錄與刑事錯案
第一節 從三個典型刑事錯案談起
第二節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第三節 勘驗、檢查筆錄運用中導致刑事錯案的因素
第四節 勘驗、檢查筆錄運用中刑事錯案的預防
第八章 視聽資料與刑事錯案
第一節 從三起刑事案件談起
第二節 視聽資料與刑事錯案的調查問卷分析
第三節 視聽資料運用中導致刑事錯案的因素
第四節 視聽資料運用中刑事錯案的預防
參考文獻
後記
……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從中國古代的“竇娥冤”到今天的“佘祥林案”,刑事錯案伴隨著刑事司法制度的始終。刑事錯案就像幽靈和影子一樣,不管司法制度如何健全和發達,只要有審判,就可能出現刑事錯案。在人類主導司法的歷史上,即使在良性運轉的司法體制中刑事錯案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司法審判的目的就是要還原和再現已經發生的事實真相,而這一目的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刑事錯案的發生不僅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甚至生命權,更破壞民眾的安全感和對司法的信任,進而撼動司法的尊嚴和權威。正如弗蘭西斯?培根所言:“一次錯誤的判決,有甚於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錯誤的判決污染的卻是水源。”從這個意義上說,刑事錯案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和損失是無法估算和衡量的。
刑事錯案的發生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過對其產生的原因進行探究,通過對其預防機制進行構建,通過對相關法律和制度加以完善與改進,可以最大限度的減少甚至避免刑事錯案的發生,以期維護司法的尊嚴,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依法治國和構建和諧穩定社會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包括司法工作者在內的全社會的共同願望。
第一節 刑事錯案的基本問題
人類是世界上唯一能夠自覺地利用大腦機制,對客觀現實進行認識、分析、判斷的。正因為人類能夠認識客觀現實,進行自主的分析並調整自己的行為,才出現了對認識或行為的所謂正確或錯誤的判斷。意識使人能夠從客觀現實中引出概念、思想、結論,並以此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使行為具有方向性、目的性和可預見性。當人的意識行為違背了自然規律或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意識和由它引導的行為就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和錯誤的行為。從認識論和實踐論的角度講,人類發展和進步的過程就是在不斷地修正錯誤、認識錯誤行為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種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科學與現代貧困、衰頹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①因為“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②這種對抗中就包含了人們對錯誤的實踐和對錯誤的矯正。
自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私有制產生後,有了階級和國家,便有了法律和犯罪,從而也有了刑事司法活動。隨著人類法律以及法律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法律體系日趨完善,刑事司法活動日益規範,人類對自身的生命、財產、人身自由等權益日益重視,刑事錯案也就隨之發生,並日益受到法學家們的重視。刑事司法活動中的錯案是人們在刑事司法活動中認識錯誤和行為錯誤的結果,這種錯誤既可以是有關司法人員或其他人員故意所為,也可以是無意所導致的。前者如司法人員貪贓枉法、徇私枉法、徇私舞弊,後者如司法人員素質低下,對事實認定及對法律把握不準而導致對刑事案件的法律適用錯誤或事實認定錯誤。刑事錯案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危害,有的甚至是無可挽回的災難性後果。因此如何預防和減少刑事錯案,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對刑事錯案的研究,其目的是減少和避免其發生,消除其消極的、不良影響,至少減少到最低程度。
一、刑事錯案的概念
就概念而言,在我國,一直都沿用冤假錯案的說法。從字面上說,“冤”案指發生了犯罪事實,但未查明事實真相,導致無辜者被定罪,而真正的罪犯可能逍遙法外的案件。“假”案指沒有犯罪事實發生,但辦案人員出於某種目的製造案件事實,並最終導致無辜者被審判定罪的案件。法律對於這兩個概念沒有明確的界定。但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的第2條明確了“錯案”的概念,即“檢察官在行使職權、辦理案件中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案件,或者在辦理案件中違反法定訴訟程式而造成處理錯誤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雖然沒有明確界定錯案的概念,但是在《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第2條中規定:“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在審判、執行工作中,故意違反與審判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或者因過失違反與審判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承擔違法審判責任。”這一規定從側面提出了“錯判”的追究問題,而“錯判”的案件就是錯案的一種。在司法實踐中,傾向於認為冤案、假案是因辦案人員有主觀惡意而造成,因此性質更惡劣,必須追究辦案人員的刑事責任;而錯案則一般是由於辦案人員對法律、法規、政策的錯誤理解或不當適用並非主觀惡意而造成,故而一般不追究辦案人員的刑事責任,即使追究也只是行政責任。這種區分有公權力機關推卸責任的嫌疑。
事實上,從嚴格意義上講,冤案和假案都屬於錯案,因為“冤”和“假”也是“錯”,歸根到底都會導致事實真相被掩蓋,無辜者被定罪,而真正的犯罪分子則逍遙法外。而既然有錯,就應該涉及到糾正錯誤和追究責任。因此,刻意區分“冤”、“假”、“錯”並無實際意義,其效果往往會沖淡主題,轉移人們對於刑事錯案本身的關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文中,“錯案”和“冤案”甚至“假案”均使用同一個辭彙,?即“刑事錯案”一詞(wrongfulconviction),①沒有“冤案”和。“假案”的提法。因此,使用“錯案”這一概念也便於與國外語境相統一。綜合以上分析,本書統一使用“刑事錯案”這一概念。
就概念界定而言,與刑事錯案的概念相關的一個問題是錯案的標準問題。如前所述,現行法律制度關於錯案的標準不夠明確和科學。如何確定錯案的標準,理論界近年來提出了諸多不同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為客觀說。此觀點強調的是,判斷錯案的標準是案件最終的處理結果是否與客觀事實不符,是否存在錯誤;此觀點的理論根據是:任何案件正確的裁判結果只有一個,而且司法人員可以並且應當發現案件的客觀真實並據此做出唯一正確的裁判。第二種為主觀說。此觀點強調判斷案件是否是錯案不是根據案件最終的處理結果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而是司法人員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持此觀點的學者的理論根據主要是:法律條文的不確定性、事實認定的不確定性和法律以外的其他社會和個人因素的不確定性決定了案件最終正確處理結果的不確定性,只要司法人員主觀上存在過錯,即使案件處理結果與客觀事實相符,也應當認定為錯案。第三種為主客觀統一說。認為確定錯案的標準應把主觀過錯與客觀結果結合起來。根據這一觀點,可以將刑事錯案定義為:刑事訴訟中發生了犯罪事實,公安機關(包括國家安全機關、監管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等在刑事司法活動中故意或者過失違反法定的程式,或者嚴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調查收集和使用證據,或者由於對案件的事實認定、證據認定和適用法律上的錯誤,最終導致無辜的人被錯誤地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
另外,在把握刑事錯案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時,應將其與適用國家賠償法的刑事錯案的外延和內涵加以區分。兩者相比,刑事錯案的定義範圍要明顯大於適用國家賠償法的刑事錯案。此外,還要將刑事錯案與刑事違法嚴加區別,刑事錯案肯定是刑事違法所造成的,但刑事違法本身卻不一定是刑事錯案,也不一定必然就導致刑事錯案的結果,只有那些在本質上和後果上導致刑事案件處理結果錯誤或嚴重侵犯有關人員合法權益的嚴重的刑事違法,才可能導致刑事錯案。
二、刑事錯案的危害
如本章開篇所述,在刑事司法活動中,錯案的發生會對當事人、對社會、對司法本身造成巨大的損害和無法估量的惡果。這是因為,司法是正義的最後防線,而刑事司法更是關乎人身、自由、財產等基本權利,對於含冤死去的人來說,甚至人最寶貴的生命權也可能面臨著威脅。審視聶、佘兩案,人們會發現聶樹斌、余祥林雖不幸但也是萬幸的,畢竟他們的冤情得以大白天下,事實真相也還他們以清白之身。但是,如果僅靠真兇落網、死者復活來期待冤案得以昭雪,那么肯定更多冤獄的受害人可能就沒有如此幸運的機遇來洗刷冤屈。“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在刑事司法各個環節的環環相扣之中,法制的陣地徐徐展開,人性的力量得以彰顯,社會的和諧圖景漸漸成就,而一旦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讓某個環節脫離法律的規制,受傷的將不僅是人的尊嚴和權利,更會使得法律的威嚴處於尷尬的境地”。①畢竟人們期待一種司法制度能夠以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方式來保障人的權利、安全感以及對司法和正義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