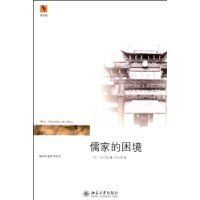內容簡介
《儒家的困境》作者用舊約傳統中的先知同中國儒家傳統中的君子進行比較,認為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對朝廷的不義進行譴責和矯枉。君子和帝王之間的張力是中國政治中重要的主題。隨著東亞的復興,儒家思想重新成為全世界學術領域的重要話題,東亞的崛起與儒家思想有什麼關係?儒家的人格在現代社會中能起到何種作用?君子的力量源於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會角色,但是君子卻沒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託付,也沒有從上天那裡獲得宗教性的支撐,而是一直陷入黎民蒼生和專制皇權的裂縫之中,這成了歷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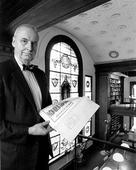 儒家的困境
儒家的困境狄百瑞(Wm.TheodoredeBary,1919—),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系教授,是海外研究中國思想的
著名學者。主要著作有:《高貴與文明》(NobilityandCivility:AsianIdealsofLeadershipandtheCommonGood,2004),《亞洲價值與人權》(AsianValuesandHumanRights,1998),《為己之學》(LearningforOne'sSelf,1991),《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EastAsianCivilizations:aDialogueinFiveStages,1988),《中國的自由傳統》(TheLiberalTraditioninChina,1983),編寫了影響廣泛的《中國傳統資料選編》(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
編輯推薦
《儒家的困境》翻譯的著作能使此前已結碩果的研究增添一個層面:面對當代西方對中國傳統進行的豐富闡釋(有時也是誤釋),我們去追溯西方的中國思想研究歷程中澤被最為深遠的學術經典。
目錄
總序
前言
第一章 聖王與先知
第二章 《論語》中的君子
第三章 帝國聖人與儒家君子
第四章專制背景下正統理學中的先知思想
第五章 方東樹:近代早期的一位先知
第六章 先知與民眾
參考文獻
索引
……
文摘
第一章 聖王與先知
從一開始,儒學的困境就來自於奠定了仁治理想的傳統神話。以及儒學後來取得過的短暫和表面的成功。這種世俗的成功恰恰顯示出帝國統治的失控。因此,儒學的困境變成了一個永久的挑戰,進退維谷的窘境讓儒學在歷史的長河中飽受煎熬。當我們在《尚書?堯典》中第一次接觸到儒學的困境時,發現了一個理想化的聖王形象。
日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人們無須深刻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堯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一個好的有教養的儒家統治者應當具備的種種美德。堯才智出眾,歷經磨練後成為多才多藝的人;堯為人恭敬、克己、謙虛、尊敬關愛他人。這些品質顯露在他對百姓慈愛如父的關懷中,在對百姓進行道德感化的過程中發揮了神奇的作用。堯的美德光芒四射,恩澤九族天下。天下百姓和睦相處,親如一家,與天地合一。但是,請注意,古人在展現這一英雄理想時,簡單地認為英雄身後的背景理所當然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人的世界,一種家族的秩序。其中,男性首領不僅已經處於統治地位,而且他的統治地位已經位於家族的中心。這裡沒有關於開天闢地的神話,沒有《創世記》。作為一個奠基性神話,《堯典》里甚至沒有展現征服或者爭鬥的場面,沒有要戰勝的敵手或競爭對手,也沒有即將面臨的抗衡力量。聖王孤身一人。除了自我約束,聖王既不會受到挑戰也不會受到制約。在描述了堯身上那些令人景仰的美德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只是尋找賢明的繼任者。這一過程里不存在角逐或者爭辯。人們的當務之急是再找一個像堯那樣具備謙恭美德、可以被委以統治重任的人。
不論儒家這一奠基性神話是否起到了含蓄批判既定秩序、祛除其神性的作用,由於它包含著依賴個體美德而非繼承權進行統治的理想,所以這個神話看起來很容易被家長制的王朝政權盜用。人們很久以後才發現,《堯典》不過是被塞進《尚書》里的一篇偽作。然而,這一。事實既不會削弱《堯典》在儒家聖王傳統中的神話功能,而且,在中央集權統治下,也不會妨礙人們對《堯典》做一番變通以適應帝國聖人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需要。畢竟,不論是神話內容還是中央集權統治,它們都不只屬於儒家。早在孔子在神話和中央集權上留下自己的烙印之前,二者就已經在中國的原始記載中恭候他的出現了。不僅大多數古典典籍早於孔子,而且,孔子之前的一些文本里也已經出現了對理想化聖王的讚美。例如,《詩經·大雅·文王》中就把周朝創始人周文王比作承載天命的人。
序言
不久以前,人們應該還無法想像會提出“儒學對於今日世界有何意義?”這樣一種問題。在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的東亞,除了少數幾個很可能被視為尚久好古的學者之外,儒學是一個沒有前途的課題。人們常說,儒學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經變成了一件博物館的展覽品。在“文革”之前,孔子在中國如此受到忽視,他的形象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至於“四人幫”在開展“批林批孔”時才發現,孔子實在是不堪一擊。因此,他們必須首先讓孔子復活,然後才能給他套上頸手枷,再把他釘到十字架上。可是,從此以後,孔子便陰魂不散。就像希區柯克的電影《怪屍案》(The Trouble with Harry)中的哈里一樣,孔子拒絕被埋葬。
時至今日,儘管人們重新開始並且更加謹慎地關注孔子,卻依然無法確定他的位置和地位。對於更年輕一些的人來說,他們在“文革”之後經歷了痛苦的幻滅。至於說其他人,儘管從來也沒有受過儒家經典的薰陶,然而,作為五四運動的繼承人,他們卻深受魯迅的反儒學諷刺文學的影響。